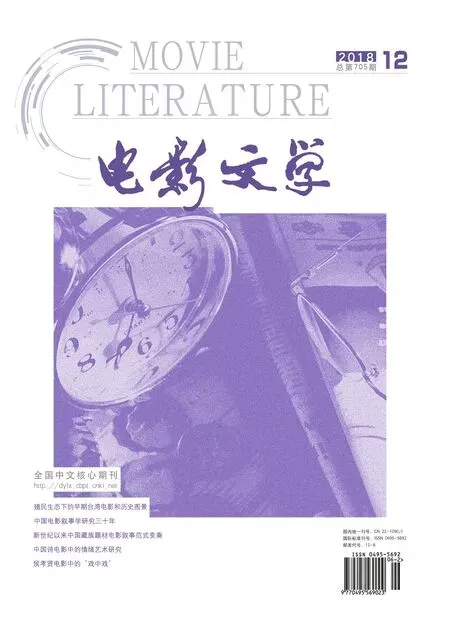《黃海》與韓國電影的流散主題
王 妍
(大連民族大學,遼寧 大連 116600)
在《追擊者》之后,羅泓軫、河正宇和金允石又聯(lián)手打造了同樣獲得如潮好評的《黃海》,相對于《追擊者》,《黃海》擁有著一個充斥著更多暴力、癲狂和陰謀的語境,在分鏡和剪輯上,《黃海》也顯得更為成熟。而更令人感到驚喜的是,不同于《追擊者》還停留在傳統(tǒng)的,立足于本土的韓國罪案片的范疇中,《黃海》已經超越了國家界限,以一種冷峻的敘事口吻讓觀眾看到了一幕黃海兩岸的悲劇。在《黃海》中,韓國電影一貫熱衷于表現(xiàn)的流散主題,也在諜戰(zhàn)片之外的類型片中與觀眾見面。
一、“流散”釋說與韓國電影的“流散”類型
流散(diaspora)一詞來源于古希臘語,原用以指因為兩次猶太戰(zhàn)爭,部分猶太人不得不離開巴勒斯坦地區(qū)而流落到世界各地。除了猶太人以外,非洲裔、華裔等各民族也有著流散歷史,流散已經成為一種世界性的、普遍性的現(xiàn)象。尤其是在后殖民主義的思想高漲和全球化時代到來之際,人們更是關注,并承認流散這一廣泛存在的社會現(xiàn)象,并注目與之有關的藝術創(chuàng)作。
而韓國因為其特殊的歷史和地理原因,其電影中的流散現(xiàn)象又與猶太人的流離散居或少數(shù)族裔的移民歷程有所區(qū)別。一般而言,韓國電影中表現(xiàn)的流散主要有以下三類:
第一,二戰(zhàn)背景下的流散。20世紀的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對于東亞諸國的影響是巨大的,韓國電影也高度重視二戰(zhàn)題材,用以迎合觀眾的愛國情愫和民族情懷。二戰(zhàn)在帶來傷亡的同時也造就了朝韓不甘投降的流亡政府和受盡苦難,難以把握自身命運的半島人民。例如,在崔東勛的以1933年為背景的《暗殺》(2015)中,歷史上在中國建立條件簡陋的臨時政府的金九,以及為抗日而不斷開展暗殺活動的韓人愛國團等各獨立運動團體進入觀眾的視野,電影中安沃允、皮斯托等韓國人身在中國卻心系祖國,歷史上的烈士李奉昌、尹奉吉就是其原型。而柳承莞的《軍艦島》(2017)則將目光對準了被日本人強行擄到軍艦島上進行采礦作業(yè),被殘酷剝削的朝鮮人,電影也表現(xiàn)了獨立運動人士并非都是高尚、磊落者。在這一類電影中,流散者的痛苦體驗以及對祖國、故鄉(xiāng)的眷戀之情,以及愿意為同胞而犧牲赴死的悲壯被展現(xiàn)得淋漓盡致。
第二,朝鮮戰(zhàn)爭與冷戰(zhàn)背景下的流散。1950年—1953年的朝鮮戰(zhàn)爭被認為是冷戰(zhàn)的開端。而朝鮮半島中的南北政權此后也一再用各種方式強化自身國家身份的合法與正當,這種分裂狀態(tài)也影響了人們的日常生活方式與思維方式。盡管1991年冷戰(zhàn)宣告結束,然而對于半島人民而言,冷戰(zhàn)的陰影依然揮之不去。在朝韓的對抗中,互派間諜進行滲透潛伏也成為斗爭方式之一。韓國電影中不乏表現(xiàn)這類“南派間諜”的作品,而出于意識形態(tài)等原因,韓國電影往往將其塑造為朝鮮的棄子。他們既是韓國社會的觀察者、異邦人,也是自己祖國的流散者。例如,在張勛的《義兄弟》(2010)中,在一次行動后,朝鮮間諜宋志元被上級拋棄,而韓國一方的行動隊長李仁奎也被革職,兩個落魄的人巧遇后從都想抓住對方洗清自己,到最后感情越來越深,兩人的“義兄弟”身份其實也是電影對于血濃于水的朝韓實現(xiàn)關系緩和的渴盼。在禹民鎬的《間諜》(2012)中,南派間諜的眾生相則被展現(xiàn)得更為殘酷。如金科長為了生存而不得不在長達22年的潛伏生涯中非法販賣偉哥等。在這類電影中,作為流散者的朝鮮間諜們往往要維持自身的生存已經相當吃力,難以發(fā)揮諜報力量,而韓國社會自身的如物價飛漲等問題,也在他們奇特的經歷中被暴露出來。
第三,當代全球化背景下的流散。朝韓之間因種種原因而被筑起了高墻,對于改革開放、中韓建交后的中國朝鮮族人而言,進入韓國則并無這樣顯著的阻礙。由于韓國一度在經濟上的優(yōu)勢地位,加上語言、生活習慣等方面限制較少,大量生活在延邊等地的朝鮮族人通過合法或非法的方式進入韓國務工,甚至成立幫派,給韓國社會的穩(wěn)定帶來影響。“他們生活在被隔離的少數(shù)異文化集團的居住地……喪失了自己的文化,墜落為社會底層。”這群作為流動的勞動力的人也為韓國電影所刻畫。如在沈成寶的《海霧》(2014)中,韓國自身因金融危機而陷入經濟下滑中,船長哲洙就為保住自己的漁船而每日憂心忡忡。而即使如此,依然有中國朝鮮族人冒著生命危險和忍受惡劣的船上空間偷渡韓國,最終一船人在漫天海霧中幾乎全部死去。又如在金周煥的《青年警察》(2017)、樸勛政的《新世界》(2013)、鄭炳吉的《惡女》(2017)等電影中,中國朝鮮族人甚至成為一系列兇險非常罪案的罪魁禍首,以至于電影引發(fā)了在韓中國人的不滿。而誕生于《海霧》之前的《黃海》也是一部涉及了中國朝鮮族人偷渡韓國的電影,可以說,《黃海》的一大價值,就是以一種不乏溫度的、人文關懷高于獵奇的方式將這一類流散者帶到了觀眾的面前。
二、《黃海》的流散主題書寫
《黃海》以兩撥人對金教授金承賢的謀殺展開。金承賢的妻子因與銀行科長金正煥勾搭成奸而雇兇殺人,通過中介找到了中國朝鮮族的綿正鶴,綿正鶴則以六萬塊的傭金找到了在延邊做出租車司機的金九南。而另一邊,黑幫老大金泰元的情人則與金承賢有染,金泰元找到崔理事欲殺死金承賢泄憤,崔理事買通了金承賢的司機,司機卻又雇傭了兩個極為業(yè)余的殺手。在金承賢被兩個殺手殺害后,金九南急匆匆地割下金承賢的手指,不料自己卻已經被綿正鶴拋棄,面臨著黑白兩道的尋找。綿正鶴和金泰元聯(lián)手追殺金九南,二者又在追殺過程中自相殘殺。在《黃海》中,電影在前半部分表現(xiàn)出了懸疑電影的特質,而后半部分則更加接近于動作片,但在拋開激烈、緊張的追逐、殺戮情節(jié)后,電影讓人深思的卻是中國朝鮮族作為流散者的悲哀境遇。
(一)身份與生存窘境
電影的第一章“出租車司機”幾乎全部在中國延邊取景,羅泓軫有意使用手持攝影讓觀眾看到了一個原生態(tài)的朝鮮族生存境遇。金九南家湊了六萬塊錢給妻子花子去韓國打工,而作為留守者的丈夫則或是如九南一樣,尚且有一個開出租的工作,或是打牌喝酒度日,等候妻子寄錢回家。電影有意在麻將館展開敘事,就是選擇了一個較具代表性,且較易爆發(fā)沖突的切入點。由于妻子已經六個月杳無音信,九南將女兒托付給母親,自己也沉迷賭博,并欠下債務。在債主追上門后,九南接受了當?shù)睾诶洗缶d正鶴的雇傭,踏上了偷渡去韓國殺人以賺錢還債的路,九南也希望能借這個機會,去首爾找回自己的妻子花子。電影中的延邊破敗、混亂,而首爾則極為寒冷。為了在偷渡船只到來之前完成殺人任務,九南不得不每天冒著嚴寒踩點,而金承賢在看到九南后,卻認出他是中國朝鮮族人,給他一點錢讓他去洗浴中心過夜。金承賢的態(tài)度無疑表明了對同胞的同情。九南也迅速在首爾感受到了朝鮮族在這里生存的艱難,電視新聞中常常報道與非法居留的朝鮮族有關的犯罪事件,而最令九南感到焦慮的是,在一則海鮮鋪老板殺死同居的朝鮮族女人的新聞中,九南敏感地感覺到女死者就是花子。
毫無疑問,在韓國,中國朝鮮族是外來者,尤其是非法打工者,更是居于社會的邊緣。“隨著中韓互動與交往接觸越來越頻繁,朝鮮族向韓國的勞務輸出規(guī)模不斷增大……但是,朝鮮族越是與韓國人的聯(lián)系密切,他們越感到自身與韓國人的差異性,影響著互相之間的認同意識。”但在自己的祖國,朝鮮族又非主體民族,電影中有意以麻將館的人罵九南來體現(xiàn)朝鮮族在自己國家的受歧視狀態(tài)。這樣一來,朝鮮族處于一種難以找到歸屬感的窘境中,與漢族人有著語言、審美等方面的鴻溝,而自己雖然與韓國人能流暢溝通,但韓國顯然并非自己的國家。在精神層面陷于漂泊狀態(tài)的同時,朝鮮族又并不在物質層面占優(yōu)。從表面上看,九南原本可以不必陷入這種流散他鄉(xiāng)的困境,但從他妻子在改善經濟條件的誘惑下離開家園,與其他朝鮮族一起加入去異國打工的大潮中去時,九南就已經接近了被放逐的命運,最終失去尊嚴和生命。
(二)流散中的追尋
《黃海》并沒有將敘事重點置于身在陌生異國空間中,朝鮮族人是如何徘徊于母國文化,同時努力建立開放心態(tài),以融入當?shù)厝说纳钪小T陔娪爸校拍虾突ㄗ佣加兄鞔_的回國目標。九南無時無刻不在想著找到妻子,完成殺人任務就回國重新開始生活,而花子之所以招來殺身之禍,也是因為她跟同居的海鮮鋪老板表示自己要回去找丈夫。在電影的最后,九南和花子的骨灰一起葬身于茫茫黃海。而羅泓軫有意安排了一個富有爭議的鏡頭:在闐靜的延邊火車站,花子微笑走下車回到故鄉(xiāng)。這實際上是九南臨死前的幻想,卻讓許多觀眾誤以為花子成為電影中唯一一個實現(xiàn)“回家”夢想的人。在電影中,花子等人遠赴韓國,是對一種更好生活狀態(tài)的追尋,但他們對自己的國族屬性依然持本質主義立場,即自己是中國人,根在中國。而電影也正因為強調了這種在流散狀態(tài)中對家的追尋,使主人公獲得了一種不可克服的悲劇沖突,讓觀眾在看到九南一次次接近故鄉(xiāng)而不可得,在每次無處容身時就躲在妻子曾經住過的小屋時,感到其被命運捉弄,不得不走向毀滅結局的悲哀,電影的感人之處也正在于此。
(三)意象的運用
在以流散主題來打動觀眾時,《黃海》并沒有只是膚淺地呈現(xiàn)不幸、死亡,在電影中有著極能體現(xiàn)羅泓軫用心的意象。首先是片名黃海。黃海在電影中象征的就是部分朝鮮族的尷尬境遇,在中國作為少數(shù)民族與主體民族常常格格不入,而韓國人也對自己充滿歧視。九南在偷渡前往韓國時曾目睹偷渡客被扔下海,這里呼應了最后九南自己也被拋下黃海,葬身于汪洋之上,中韓之間,至死也是一個無家可歸的流散者。其次是帶有顯著隱喻意味的“狗咬狗”象征。狗肉本身是朝鮮族人喜愛的食物,“狗東西”也是朝鮮語中語氣強烈的罵人話,在綿正鶴找到九南時,環(huán)境就是延邊嘈雜的、狗咬狗的狗市。電影的開頭也借九南的旁白講述了一個人們因為吃了有狂犬病的狗肉而致死的故事。而其后的故事,則反復印證著“狗咬狗”。電影中人的彼此殺害,正如一幕狗咬狗的鬧劇。而電影在表現(xiàn)朝鮮族時,有意體現(xiàn)其土氣、粗魯?shù)囊幻妫ㄗ印⒕d正鶴等人也生活在灰色地帶,似乎是韓國社會治安混亂的因素之一。而反觀韓國首爾人則普遍衣著光鮮,有豪車別墅,帶有被“文明教化”過的優(yōu)越。然而羅泓軫所想諷刺的正是后者。金氏兄弟無恥而殘酷,是典型的衣冠禽獸,銀行科長、司機等人貪婪無情,金氏兄弟的伴侶則紅杏出墻,代表正義的警察也庸懦無能,海鮮鋪老板甚至喝酒之后就虐殺了花子。正是這些韓國的“文明人”導致了罪惡,然而他們卻視朝鮮族為危險、野蠻的化身,這是十分可笑的。在電影中,幾乎所有人都暴露出了和狗一樣的原始欲望。
韓國電影中的流散主題是一個值得開掘的對象,種種原因造就了韓國社會各類身份、遭際不同的流離失所者,其在現(xiàn)實世界中的生存斗爭,成為韓國電影熱衷表現(xiàn)的內容。盡管羅泓軫對于中國朝鮮族的境遇存在一定的偏見,但這不影響《黃海》依然是一部進行流散書寫的佳作。在其表面的謀殺、追殺情節(jié)后,電影最大的價值來自于具有社會意義和審美意義的對朝鮮族個體悲劇的演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