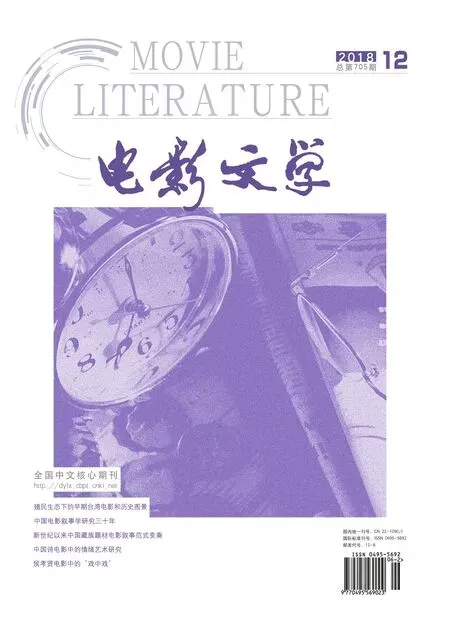《三塊廣告牌》的現實主義底色
朱 芬
(洛陽理工學院 外國語學院,河南 洛陽 471000)
走現實主義的道路,被認為是國產電影對抗好萊塢影響的重要方式:“好萊塢電影美學的文化霸權是導致世界各國電影持續衰退的原因,世界各國尤其是中國要想走出困境,一個至為重要、關鍵的策略就在于堅持現實主義電影美學。”而現實主義同樣也是非好萊塢體系的美國本土電影(即獨立電影或大制片公司下的非商業片)不曾放棄的,用以標示自身處于好萊塢之外的美學經驗,這一點在奧斯卡這一在美國電影界,尤其是文藝片中具有風向標意味的獎項的頒發上體現得尤為明顯。只要從近數十年來奧斯卡的提名與授獎傾向上來看,就不難發現其對具有現實主義底色影片的青睞,如20世紀80年代的《布拉格之戀》(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1988),20世紀90年代的《阿甘正傳》(Forrest
Gump
,1994),以及新世紀的《海邊的曼徹斯特》(Manchester
by
the
Sea
,2016)等。而在2017年的奧斯卡“大年”中脫穎而出的,由馬丁·麥克唐納自編自導的《三塊廣告牌》(Three
Billboards
Outside
Ebbing
,Missouri
,2017)便是其中之一。一、《三塊廣告牌》的創作原則
現實主義是傳統文藝理論中的一個重要美學范疇,與浪漫主義、象征主義、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等并峙。從本體論的層面來看,現實主義意味著一套與前述主義不同的意識形態,而從創作論的層面來看,現實主義有著在創作原則和創作方法上的獨特性。
從創作原則上來看,現實主義原則強調直面現實,關注社會與時代的精神狀況,以現實生活中存在的各種矛盾,以及人們的社會心理為表現對象,并且試圖總結、揭露對象背后的原因與邏輯。主體對于現實的認識和評價,往往通過一種較為含蓄的方式表達出來,現實主義通常對現實采取批判、否定態度,批判性被認為是現實主義區別與其他美學范疇的一個重要標志。
在《三塊廣告牌》中,對“正義無法得到伸張”的揭露便是其批判態度之一。電影中的小鎮位于美國經濟并不發達的密蘇里州,名為艾賓(Ebbing)鎮,意為“沉淪中”,這是麥克唐納對于落后、衰退的社會一角的總結。在小鎮上,女主人公米爾德麗德的女兒安吉拉被強奸并焚尸,然而七個月之后,警方還是無法破案,這一方面固然有作案者沒有案底的原因,另一方面也與整個政府部門的效率低下有關。如當鎮民前來警局就三塊廣告牌投訴時,接警警員的記錄是“一個眼睛怪怪的女人和一個胖胖的牙醫來投訴了”,甚至沒有留下投訴者的姓名;而胖牙醫的手指被米爾德麗德用電鉆鉆了一個小洞,警方也對米爾德麗德“各執一詞”的說法無可奈何;警方明明能猜測到燒了警察局的人是米爾德麗德,卻因為暗戀米爾德麗德的侏儒詹姆斯為她做了一個經不起推敲的不在場證明,就沒有再追究米爾德麗德的縱火罪。在這樣的情況下,警方對于無法抓住殺害安吉拉的真兇的解釋,自然也是無法讓米爾德麗德信服的,無論是DNA的不匹配,抑或是不在場證明,對于米爾德麗德而言,都意味著警方的顢頇無能或有人包庇,以至于一直讓兇手逍遙法外,蒙混過關。
借由安吉拉一案的無法告破這一似乎是偶然性的、戲劇性的事件,小鎮整體環境的壓抑、陰暗逐步被暴露出來:墨西哥勞工、黑人遭受著歧視,警察迪克森威脅一個吐痰的黑人以破壞環境罪逮捕他;在威洛比警長自殺后,迪克森將廣告公司負責人韋爾比從二樓窗戶扔下,還毆打了廣告公司的女職員,隨后迪克森對黑人出言不遜,不料對方卻是新任的警察局局長;為了給米爾德麗德施壓,警方拘留了米爾德麗德的黑人女朋友;威洛比曾表示如果把那些有種族主義傾向的、恐同的、不干事的警察都開除,警察局就剩不下多少人了。而殘疾人,如侏儒詹姆斯也在生活中飽受嘲笑。年輕人如安吉拉則抽大麻,與自己的母親互罵“婊子”;母親米爾德麗德則在上一段婚姻中遭受著前夫的家庭暴力。一言以蔽之,整個社會是病態的、失序的。幾乎所有人都陷在正義無法得到伸張的境地中,受到他人的傷害又去傷害著別人。美國階層和觀念撕裂的保守州的大量負面的生活表象以一次奸殺案為起點展現在觀眾面前。
二、《三塊廣告牌》的創作方法
從創作方法上看,現實主義最典型的創作方法便是真實論和典型論,正如恩格斯在1888年的信《致瑪·哈克奈斯》中提到的:“據我看來,現實主義的意思是除細節的真實外,還要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真實論即尊重現實生活的本真面目。但如果一味復刻現實,那么無疑將落入自然主義、寫實主義的陷阱,因此現實主義要求“高于生活”,進入到“藝術真實”的境地中。典型論則意味著創造典型環境,這直接決定了人物的思想行為,而反過來,人物的思想行為又作用于典型環境。這也就是哈克奈斯的《城市姑娘》中奈麗在環境中只能逆來順受和高爾基《母親》中工人階級進行革命,巴爾扎克《高老頭》中拉蒂斯涅擁有了資本主義金錢關系后成為一個野心家等創作路線之間的區別。
米爾德麗德就是小鎮這一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之一,前夫帶來的家庭暴力,子女正值叛逆期導致了米爾德麗德的偏執、冷漠和強硬,因此她渾身散發戾氣,滿口污言穢語,以倔強的姿態回應一切,也正是她堅持不肯借車給女兒,導致了走夜路的女兒被強奸,一直被內疚感折磨的米爾德麗德才會不為所動地責怪警察,逃避內心的自責。又以威洛比的下屬迪克森為例,他是另一類典型人物,執法粗野,以折磨黑人嫌疑人聞名,還是一個以恐同來掩飾自己同性戀身份的人,并因戀母情結而時常遭到他人的嘲笑。迪克森無疑不是一個合格的警察,在讀警校時留級,在警局用工作時間看漫畫等臺詞和情節,都刻畫出迪克森業務水平的低下。然而看起來面目可憎的迪克森的“戀母”和暴躁很大程度上來源于自己幼年喪父,因此迪克森將威洛比視為自己生命中的“父親”,當看到米爾德麗德質問威洛比的廣告牌時,迪克森比威洛比更加憤怒和激動。而威洛比也一直關愛、保護著他。威洛比在自殺前,給妻子、迪克森和米爾德麗德留下了三封遺書,并為在經濟上已經山窮水盡的米爾德麗德續交了一個月的廣告費。在威洛比的遺書感染下,米爾德麗德和迪克森內心柔軟的一面都被喚醒:迪克森在大火之中為了威洛比的一句“你會成為一個好的警探”而搶救出了安吉拉案件的卷宗,米爾德麗德也在誤傷迪克森以后意識到了自己的野蠻粗魯,兩人從憎恨走向了寬恕,理解了對方。無論是米爾德麗德在對法律不抱希望時的“以火還火”,抑或是迪克森在精神之父感召下的“改邪歸正”,都是其本質性格推動下的行為。導演似乎只是對人物進行追蹤和實錄,但依然屬于有著導演主觀干預的痕跡。如迪克森在被燒傷住院后,與他住同一病房的竟是被他丟出窗外的韋爾比,而韋爾比在沒認出臉被白紗布裹著的迪克森時主動上前安慰,在迪克森流下眼淚承認身份后,盡管非常生氣但依然給迪克森倒了飲料,甚至幫他調整了吸管的方向,病房安排的巧合,韋爾比的不計前嫌,無疑是為了服務于影片的寬恕主題,屬于一種“藝術真實”。
三、《三塊廣告牌》與當代語境下的現實主義啟示
如前所述,被認為是技術主義、形式主義與“造型傾向”結合的好萊塢美學在全球電影市場上有著難以撼動的霸權式地位,只要對當代的理論和創作語境稍作檢視便不難發現,對于部分“前衛”的電影人而言,現實主義幾乎等同于保守或過時。人們必須承認,在大眾文化時代,電影實踐作為文化產業運作的一部分,所要提供給大眾的更多的是娛樂而非教化,是大眾所需而非主創所想。尤其是在非好萊塢電影遭遇危機時,電影的娛樂性,包括其形式上的觀賞性就會得到大力鼓吹,而現實主義則被人們所冷落與回避,即使是在人們依然肯定現實主義的情況下,現實主義也往往被要求“改革”或“深化”,即服從于商業策略,增加娛樂性或能實現向國際“接軌”的元素。這實際上是一種對現實主義的游離與背叛。而《三塊廣告牌》則給人們提供了一個范本,現實主義與娛樂性、可看性等之間并非不可調和,實現后者并不意味著就要扭曲、放棄現實主義的嚴肅性。
《三塊廣告牌》是麥克唐納作為導演的處女作,之前一直身為編劇的他,本身就擅長劇本的打磨。在《三塊廣告牌》中,電影就劇本本身而言,不僅敘事節奏漂亮,并且劇情不斷反轉,并為反轉設定了足夠的伏筆,這些都給予觀眾極大的觀影享受。如在廣告牌被焚燒時,觀眾都誤以為放火的人是迪克森,不料真相卻在米爾德麗德和詹姆斯約會時揭開,原來是前夫燒毀了廣告牌,而意識到自己報復錯對象的米爾德麗德盡管強忍沒有失控,但依然由于低落和怨恨忍不住對詹姆斯口出惡言,以至于詹姆斯憤然離去。此時電影不僅在廣告牌被燒一事上實現了反轉,米爾德麗德和詹姆斯的關系也急轉直下,超出了觀眾的想象。
除此之外,電影中還處處可見麥克唐納設計的黑色幽默,這為電影帶來了一定的喜劇性。黑色幽默強調的是對現實生活進行扭曲和放大,但是只要和黑色幽默大師科恩兄弟進行對比就不難發現,麥克唐納沒有因為穿插使用黑色幽默而使電影中的人物生活走向荒誕和失控。如當前夫要掐死米爾德麗德,兒子羅比拿刀架在父親的脖子上,矛盾一觸即發時,前夫的19歲女友佩內洛普卻進來問衛生間在哪里,當米爾德麗德嘲笑佩內洛普是有騷氣的動物園小妞時,佩內洛普似乎完全聽不懂其中的諷刺意義而認真地解釋自己換了工作,現在在馬場照顧殘疾的馬。當新局長告訴迪克森兵痞擁有不在場證明時,已經提示了他在國外,并且那個地方有沙漠,而迪克森卻依然茫然地說:“你也沒有縮小范圍啊。”完全沒有領會局長關于大兵當時在中東的暗示。而這也恰好是與電影中的環境相符合的,佩內洛普、迪克森正屬于這個偏僻、保守、封閉的小鎮上,文化程度極低的一類年輕人。而整部電影故事的起點,即奸殺案,也正是這樣的環境的產物。一言以蔽之,《三塊廣告牌》整部電影擁有一個扎實的劇本框架,情節在經得起推敲的同時,又給予觀眾歡笑、悲涼、溫情等交織的情感效果,即使是在設計能夠給觀眾娛樂的懸疑感或幽默時,劇情都在一個穩定可控、符合現實的空間之內。
如果說好萊塢電影代表了一種具備內容上的橫向覆蓋性、傳播上的大眾化,并且在全球化與技術發展的推波助瀾下得以席卷全球,獲取商業上強勢地位的電影美學,那么現實主義電影美學則具備的是與之迥異的內容在縱向上的延伸性,以及屬于特定時代、地方或民族的訴求。奧斯卡乃至金球獎與三大電影節,一直對擁有現實主義底色,注重題材社會性的影片保持著青睞,以增強學院派電影與來勢洶洶的商業電影對抗的籌碼。《三塊廣告牌》就可以稱得上是一部典型的在注重了電影文本技巧性、文學性的同時,有著對現實生活的高度關注,對人性與現實有著獨立思考和批判思想的優秀之作。在人們就中國電影在好萊塢電影挑戰下的文化戰略而迷惘時,《三塊廣告牌》無疑為中國電影人提供了有益的經驗與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