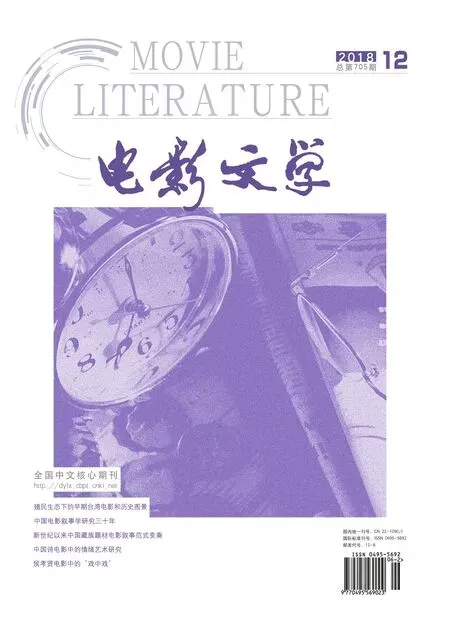論《三塊廣告牌》的敘事特征
史玉豐
(河南理工大學 文法學院,河南 焦作 454000)
《三塊廣告牌》延續了導演馬丁·麥克唐納以往作品如《六發子彈的手槍》《殺手沒有假期》和《七個神經病》里對暴力、死亡與救贖等主題的關注,在這些作品中,暴力酣暢淋漓的血腥表現、不忍直視的荒誕死亡、不可遏制的情緒爆發、無可救贖的生命個體、陰郁冷酷的電影色彩,都給觀眾留下了獨特的觀影體驗,由此也形成了他“直面戲劇”“黑色幽默”“以暴制暴”等藝術特色。《三塊廣告牌》中那種一觸即發的神經病似的緊張情緒已經得到有效控制,從而能夠使電影敘事張弛有度,在精巧的戲劇性設計中表現人生無可調和的矛盾和沖突,卻又透出更多的人性暖意,其中有著對“以暴制暴”的理性思考,并提出了用愛、關懷與寬容去探討精神救贖的可能。
《三塊廣告牌》敘事特征表現如下:
一、暴力敘事
暴力一直是麥克唐納鐘情的電影敘事元素,在《三塊廣告牌》中,他主要是通過色彩暴力、語言暴力和精神暴力以及對暴力的反思來表現的。
色彩暴力。紅色與火是“暴力”最重要的視覺象征。三塊廣告牌在綠蔭疊嶂、陽光明媚的密蘇里州德林克沃特公路邊赫然矗立:“怎么回事,威洛比警長?”“兇手依然逍遙法外?”“強奸致死?”極具視覺沖擊的紅底黑字揭露著安吉拉死亡事件的血腥和殘暴,以一種沉默的暴力追問拷打與之有關的當事人:威洛比警長,同時也將這種來自弱勢群體的質問拋向美國社會。象征著暴力、血腥與復仇的紅色廣告牌將小鎮卷入令人瘋狂的戲劇時刻,同時也將米爾德麗德·海耶斯置于與小鎮尖銳對峙的緊張關系之中,空氣中彌漫著暴戾和不安,眾多人物被一一卷進,帶著他們生活的無奈、失意,甚至病痛和死亡。
影片中的廣告商名叫Red Welby,“red”來源于他的紅頭發,他租給米爾德麗德廣告牌,在警察的警告之下毫不妥協,使這一事件繼續發酵;他又突然以無賴的形式逼迫米爾德麗德交錢,說以前交的錢只是定金。他是暴力的起源之一,也是暴力的承受者,被迪克森打得進了醫院,但他同時還是暴力的消解者,他不計前嫌,給燒傷的迪克森倒了一杯橙汁,表現出善良寬容的一面。
火是影片中暴力升級的標志。它更直接,更猛烈,更瘋狂,在黑夜中燒掉廣告牌的大火是如此觸目驚心,以至于徹底把米爾德麗德逼向瘋狂報復之路,讓她在深夜鋌而走險火燒警察局,即使犯罪也在所不惜,體現出“以暴制暴”的敘事特征。
語言暴力。影片中“fuck”詞頻之高令人咋舌,人們在語言暴力中宣泄著不滿和仇恨,同時也被這種語言暴力反噬:米爾德麗德與安吉拉相互惡毒詛咒,不料竟一語成讖,造成女兒慘死,這也是米爾德麗德在彪悍外表之下不可與外人訴說的巨大隱痛:她認為自己的惡毒詛咒導致女兒慘死,從而無法原諒自己。
語言暴力也體現出一種力量。雖然整部影片在夏日玫瑰舒緩安詳的音樂中展開,敘述語言卻鏗鏘有力,充滿金屬般的光澤和力量,讓整個影片充滿了戲劇張力,表現了人物內心深處的絕望、掙扎和焦慮。影片中的長句子更是精彩,例如米爾德麗德面對女記者所爆的粗口,一氣呵成,淋漓盡致,氣勢驚人,她在停車的瞬間將這個長句子拋給反應未及的女記者,然后在對方的錯愕之中絕塵而去,顯示出逆天的霸氣,給觀眾則帶來痛快酣暢的情感體驗。
精神暴力。在影片中,彪悍的米爾德麗德身著藍色工裝,頭發緊緊攏起,我行我素,人人忌憚。她心思縝密,對胖牙醫施以狠狠的報復,將他的拇指鉆了一個洞;她語言犀利,對神父的指責施以伶牙俐齒的反擊,讓其啞口無言;她動作敏捷,對扔飲料的學生大打出手,在眾人的冷眼中毫不退縮。然而,這位強悍的母親卻是一位長期遭受家暴、被丈夫拋棄、獨自撫養兒女的悲劇女性。她陷于對女兒失事的強大愧疚中無法自拔,三塊廣告牌與其說是對警長和社會的詰問,不如說是米爾德麗德對自己內心的懺悔和贖罪,所以她才會把廣告牌看得如同生命一般。她為她粗暴的愛的方式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后悔不迭,陷入異常的孤獨和永無休止的自我譴責中。
暴力反思。影片的深刻之處在于對暴力進行反思:到底是什么導致了暴力,“以暴制暴”是否是唯一的解決方式?父愛的缺失和母親教育的偏頗導致了迪克森警探性格的缺陷,認為大打出手是解決世界上所有問題最直接也最有用的方式,但實際上他每次都把事情搞砸,虐待黑人、暴打廣告商、酒吧打架,武力成為他向這個世界證明自我的重要方式。直到威洛比警長的信才讓他對自己有了深刻反思,從而做出一系列轉變。米爾德麗德也是如此,當她在暴力情緒難以遏制之時,那句“憤怒招致更大的憤怒”還是點醒了她。正是對暴力的反思,才使得救贖成為可能。
所以,影片在關注暴力之時,更加關注暴力背后人們的生存困境。他們找不到可以擺脫生活困境的方式,只好選用暴力突圍,以擺脫自己在面對困境時的負罪感、無力感和孤獨感,所以,暴力不僅僅是一種行為,更是一種反抗絕望和人生困境的手段,具有人生突圍的意義。
二、互文性敘事
互文性敘事使影片成為一個多維立體結構,電影元素相互指涉,有效拓展和豐富了敘事空間。例如Red Welby看的《好人難尋》,《好人難尋》是美國女作家弗蘭納里·奧康納的代表作,它的黑色幽默、荒誕暴力等書寫特點與麥克唐納的影視作品有著驚人的相似,它從一開始就暗示著這個Ebbing小鎮將要上演一場愚蠢與怪誕、暴力與死亡的好戲。將《好人難尋》作為影片的互文性文本,使之成為一個多聲部的合唱,體現出獨具匠心的精巧設計,同時也領略一種來自黑色幽默的反諷意味,它充滿象征和隱喻,顯得不同凡響。
與劇情同時進行的互文性敘事,還有電影配樂。例如電影一直都在表述的死亡和救贖主題:影片的死亡主題以愛爾蘭民謠Last
rose
of
summer
奠定了憂傷與神秘的基調:“……當所愛的人已逝去,誰還愿留在,這荒冷的世上獨自凄涼?”His
Master
's
Voice
中的宗教救贖主題,用在迪克森這只迷途的羔羊身上非常貼切:一個戰士聽到了穆罕默德和耶穌的呼喚,看到了自己童年的一面,聽到的全是生活與愛的聲音,聽到了牧師的尖叫:“此中有邪念 必須要放下!”而在Buckskin Stallion Blues中則發出對愛輕柔的呼喚:“If love can be and still be lonely/Where does that leave me and you?Time there was, and time there will be/Where does that leave me and you?(假如愛如此孤獨,你我將身在何處? 時間之河緩緩流淌,我和你將去往何方?)”迪克森得知警長死訊之前,用耳機聽的那首ABBA樂隊的名曲Chiquitita出自專輯《愛的主題曲》,歌詞以循循善誘的方式告訴Chiquitita
,忘記過去的憂傷,修復折損的羽翼,“You'll be dancing once again and the pain will end(你會再次起舞 痛苦終將結束)”。最終使影片走向夏日玫瑰般的憂傷,也走向夏日玫瑰的平和,廣袤大地包容了一切。三、張弛有度的敘事節奏
影片對于敘事節奏的有效控制尤其讓人稱道,首先表現在敘事力量的相互制衡,使之始終處于一種緊張中的平衡狀態。三塊殘破的廣告牌上,無論是圖畫還是文字,都隱喻著米爾德麗德·海耶斯現實生活的支離破碎:婚姻早已告終,拋下妻子兒女的丈夫正與19歲的動物管理員打得火熱;貌美叛逆的女兒去年被強奸致死,且被大火焚燒成焦炭;案子遲遲未破,經歷人生絕大痛苦的她表面平靜,內心卻有一股不可遏制的戾氣等待爆發……影片中其他人也正面臨著危機:頗有威望的警長威洛比無法消除癌癥病痛的折磨,性格暴烈的警探迪克森總是將事情搞砸而毫不自知。當矛盾和沖突在這些人物中展開時,一種緊張危險的情緒在銀幕彌漫開來,充滿了十足的戲劇張力。然而事情沒有如麥克唐納以往作品中的暴力肆虐,在影片中,我們會隨時發現與暴力相反相成的因素。例如,在色彩運用上他一改以前影片的陰郁冷鷙和殘酷血腥,呈現出一派清新亮麗和溫馨自然:云霧繚繞林木蒼翠的山巔,晨光中靜靜安放的秋千,午后金子般的陽光照耀碧綠的草地,在充滿著田園詩般的寧靜氛圍中,米爾德麗德不斷往廣告牌下運送鮮花,還有神諭般出現的溫順麋鹿,這些靜謐溫情的鏡頭對暴力和苦難形成了一種有效消解,使影片的基調從躁動走向平和。
影片對敘事節奏的有效掌控還表現在敘事動力能夠環環相扣,張弛有度。在前一敘事動力即將消逝之前,后發敘事動力隨即跟上,共同塑造了這一精彩絕倫的電影敘事:米爾德麗德在平靜的小鎮樹立起三塊廣告牌,逼問以威洛比警長為代表的當權者和美國社會,使得平靜的小鎮掀起軒然大波,使小鎮直接分為兩派:支持警長的大多數和支持米爾德麗德的少數派,甚至出現了胖牙醫要傷害米爾德麗德反被她報復的驚險故事。面臨胖牙醫的指控,米爾德麗德可能面臨牢獄之災,但在警局問詢的時候,威洛比警長突然吐血,米爾德麗德一句“I know,baby”,一下子就消解了橫亙在二人面前的鴻溝,從仇恨變成憐憫,而米爾德麗德也被警長下令釋放。到這里,敘事似乎進入了平緩期,各方力量都在保持不動,敘事的力道較為舒緩。而威洛比警長的自殺重新將米爾德麗德以及廣告牌推向了風口浪尖,在她面臨各方壓力而毫不退縮的同時,威洛比警長的信使得這位暴戾母親的內心因為警長的理解、關懷和愛而悄然發生了變化,同時她知道了她的第二筆廣告費是警長給她付的。因為警長之死而帶來的第二個影響是迪克森警官暴打廣告商從而失職的事件。暴力之后,無論是電影的案件進程還是個人的命運空間,都進入長時間的停滯和虛妄時期,敘事節奏又趨向平緩。第三次敘事動力來自于火燒廣告牌,它直接刺激了米爾德麗德內心憤怒的大爆發,讓她直接火燒了警察局,在怒氣得以釋放的同時,她又發現迪克森冒著生命危險帶出來的正是女兒的案卷,這一刻她內心百味雜陳,加上侏儒詹姆斯的保護,使她避免牢獄之災。而后的敘事逐漸變得溫暖,負責貼廣告牌的年輕人給她送來了備用印刷品,讓三塊廣告牌重換新顏,這簡直讓米爾德麗德歡欣鼓舞。小說的第四次敘事動力來自于迪克森在酒吧聽到一個人在講述類似安吉拉的犯罪事件,他撓了對方的臉,留下大量的DNA備查,同時也將無限的希望留給觀眾,影片至此達到真正的高潮,但對方卻不是殺害安吉拉的兇手。這一懸念跌宕起伏,讓每個人充滿希望,又跌入失望的谷底,在充滿懷疑的追問中,迪克森和米爾德麗德能夠確定的是,這個人是一個逍遙法外的強奸犯。當法律無可奈何之際,這兩個帶有神經沖動的獨行俠聯合起來,共同奔赴遠方,那種豪氣以至于讓觀眾可以在瞬間忘記事件的合法性,留給觀眾的是豪氣沖天的荷爾蒙宣泄、相互和解的脈脈溫情和走向未知的開放性結局,至此,這部舒緩有致的影片完成了它最后一個節奏,堪稱完美。
影片最后,米爾德麗德和迪克森決定驅車去抓捕罪犯,在無盡的公路指涉之處,我們的神經再一次興奮起來,讓這兩個充滿戲劇性、善于節外生枝的同伴一同前行,前方等待他們的不知道是何樣的人生悲劇,抑或是斗智斗勇的精彩,電影以這樣的方式告知我們,生活遠未完結,暴力、死亡和救贖將會以另外一種新的面目出現,這種開放性敘事創造出新的審美視野和敘事想象,將影片推向一個深邃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