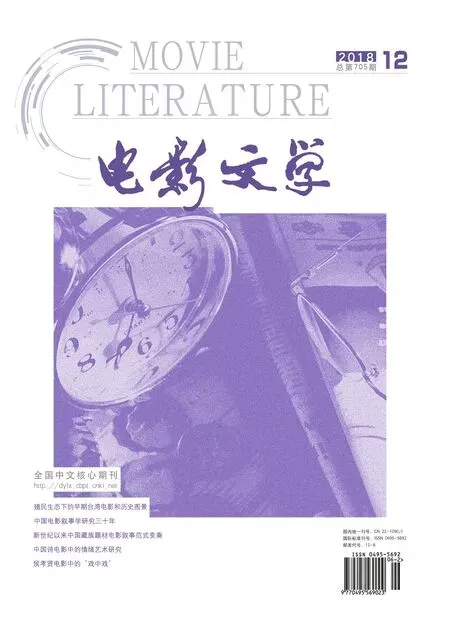電影《消失的愛人》文化敘事新解
任春華
(長春理工大學(xué) 光電信息學(xué)院,吉林 長春 130000)
好萊塢著名導(dǎo)演大衛(wèi)·芬奇擅長黑色風(fēng)格電影,他的電影中既有商業(yè)化的藝術(shù)考量,同時也兼具個人化的影像風(fēng)格。《消失的愛人》(Gone
Girl
)是導(dǎo)演大衛(wèi)·芬奇近年來頗受好評的作品,該片無論是在懸疑、犯罪抑或是倫理片的范疇都可圈可點,頗具藝術(shù)價值與研究價值。針對《消失的愛人》的電影理論研究多數(shù)集中在敘事結(jié)構(gòu)、敘事角度等最基本的敘事學(xué)理論層面,或者是針對大衛(wèi)·芬奇的電影風(fēng)格做出的研究。然而,如果對吉莉安·弗琳的同名原著和改編劇本進行研究不難發(fā)現(xiàn),無論是敘事過程中制造劇情反轉(zhuǎn)的敘事推力,還是造成尼克與艾米虛偽婚姻與復(fù)雜人性的深層原因,都離不開當代美國文化的深刻影響。經(jīng)由敘事內(nèi)容與文化內(nèi)容的結(jié)合來看,對于大衛(wèi)·芬奇這部經(jīng)典作品會有進一步的理解。一、媒體文化作為敘事推動力
電影《消失的愛人》根據(jù)吉莉安·弗琳的同名小說改編,大衛(wèi)·芬奇擅長的黑色電影風(fēng)格與小說文本自帶的陰暗氣質(zhì)相互輝映,構(gòu)成了《消失的愛人》獨特的現(xiàn)實主義批判風(fēng)格。《消失的愛人》將敘事的矛頭對準婚姻,完全撕碎完美幸福的婚姻的華服,將華服之下生滿的虱子赤裸裸地暴露出來。本·阿弗萊克扮演的尼克和羅莎曼德·派克扮演的艾米是一對人人稱羨的模范夫妻,他們從紐約搬到密蘇里過著平靜的生活。在尼克和艾米結(jié)婚五周年之際,艾米的失蹤徹底打破了二人看似風(fēng)平浪靜的婚姻生活。在尼克看似焦急,實則平靜,甚至內(nèi)心帶有一絲不懷好意的竊喜的情緒之下,警方和社會民眾對艾米這個小有名氣的女人開始了搜尋,人人都認為艾米已經(jīng)被綁架、深陷危險之中或者遭到毒手的時候,艾米的日記本出現(xiàn)在人們面前,日記的字里行間都將這個犯罪嫌疑人指向了自己的丈夫尼克。然而,這一切都只是艾米自導(dǎo)自演的一場鬧劇,這是她給尼克的結(jié)婚五周年的“禮物”。影片最終,艾米重新回到了尼克身邊,用一個又一個謊言緊緊地拴住了尼克。
從吉莉安·弗琳的同名小說到大衛(wèi)·芬奇執(zhí)導(dǎo)的電影版《消失的愛人》,幾次敘事的高潮都是伴隨著劇情的大幅度反轉(zhuǎn)出現(xiàn)的,然而影片堆積的敘事動能卻是在一次次尼克登上電視,透過媒體與人們對話的過程中釋放的。在《消失的愛人》當中,媒體扮演了一個至關(guān)重要的功能角色,媒體不僅是尼克和艾米經(jīng)營自己角色的工具,同時也是推動這場陰謀的主要推手。在影片當中,媒體推動敘事的發(fā)展進程可以總結(jié)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媒體塑造了尼克的好丈夫角色。尼克從最開始報警稱自己的妻子失蹤,在大眾媒體上經(jīng)營著傷心欲絕的好丈夫形象,他懇求罪犯不要傷害自己的妻子,在結(jié)婚五周年之際他懇求罪犯能夠?qū)⑺蓯鄣钠拮悠桨菜突氐剿纳磉叀5诙A段,媒體塑造了尼克的犯罪嫌疑人角色。隨著艾米那本事無巨細記錄得密密麻麻的日記本的出現(xiàn),尼克和艾米生活中的點點滴滴逐漸透過媒體進入大眾視野,日記幾乎記錄了尼克與艾米從相愛到結(jié)婚的全部細節(jié),以及二人在婚后的種種事情。在記錄婚后生活的字里行間,人們看到的只是一個越來越懶惰邋遢,對艾米倍加冷落,甚至是感到厭倦的尼克。于是,尼克成為“艾米失蹤案最大的嫌疑人”。第三階段,媒體重新塑造了尼克的好丈夫角色。當艾米殺死戴斯以后,渾身是血地重新回到了公眾視野,在媒體面前她公開表達了自己對尼克的愛,為尼克洗脫了所有嫌疑和罪名,尼克能做的就是保護好這個“受傷的脆弱女人”。如此一來,尼克再次成為媒體和大眾眼中的“好丈夫”,二人也重新成為“完美夫妻”了。
影片敘事的三個階段的發(fā)展,媒體都成為主要的敘事推動者。艾米是大眾媒體的寵兒,她深知媒體和大眾需要什么,于是她費盡心思地設(shè)計了自己被“殺”的所有細節(jié),她明白只要稍微釋放出一絲血腥味兒,媒體就會像鯊魚一般追隨過來,她的名氣,她和尼克的看似完美的愛情,婚姻中的出軌和謀殺,這些都是當代媒體最熱衷的關(guān)鍵詞,媒體不在意事實的真相,大眾希望看到什么,什么就是媒體眼中的真相。導(dǎo)演大衛(wèi)·芬奇諷刺了媒體的無良和愚昧,否定了當今媒體仍有絲毫的道德性可言,媒體只是饑餓的豺狼,一旦捕捉到傷口散發(fā)的血腥味兒,立刻會追隨而來并將受傷者啃食干凈。
二、婚姻文化與社會文化的互文
無論是吉莉安·弗琳的小說原著,還是大衛(wèi)·芬奇執(zhí)導(dǎo)的電影,都將現(xiàn)代社會的婚姻抨擊得體無完膚。尼克與艾米的婚姻在短短的五年時間里就變成了一具空殼,耗盡了二人所有的愛與精力,以及對彼此虛幻的想象。在這五年當中,尼克和艾米彼此都很清楚對方早已不是自己熱戀時期認識的那個人了,尼克在失去了工作之后變得邋遢、懶惰,完全沒有進取心,身材也日漸臃腫。為了讓他們的生活不至于太過狼狽,他們從大都市紐約搬到了尼克的老家密蘇里——一個徹底的鄉(xiāng)村。艾米也對尼克越來越冷淡,無法忍耐自己曾經(jīng)帥氣十足的丈夫變成了如今這般模樣,自己精致現(xiàn)代的生活也墮落到如此地步。他們的婚姻如今只剩下麻木地消耗彼此的性愛以及名存實亡的一副空殼。
尼克與艾米婚姻生活也是大部分現(xiàn)代都市人婚姻的折射。在離婚率居高不下的美國社會,愛情與婚姻更像是隨等可取的速食快餐,甚至融入了當下的消費文化。艾米是著名兒童書籍作家夫婦的獨生女,她是父母書中那個完美的美國女孩,書中的小女孩的原型人物,現(xiàn)實中的艾米也是要求自己按照完美的女孩標準生活,不吃垃圾食品,不歇斯底里地發(fā)脾氣,永遠保持苗條的身材和迷人的個性。她與尼克的結(jié)合,是因為尼克作為現(xiàn)代美國男性的代表,時尚、帥氣、幽默、浪漫,幾乎涵蓋了所有完美男性的特征,完美女孩艾米與完美男孩的結(jié)合是一種對完美婚姻想象的必然實踐結(jié)果。他們一起在紐約生活,經(jīng)營著他們摩登而精致的完美都市婚姻生活,從精神層面到物質(zhì)層面,他們都力求完美,這也是生活在美國中心的紐約最基本的要求。于是,我們看到尼克和艾米的結(jié)合首先反映了當代都市文化,人們對愛情與婚姻有著不切實際的完美想象,他們?nèi)莶坏脤Ψ缴砩嫌幸唤z的缺點,首先是物質(zhì)生活要符合都市生活的標準,其次在外人看來要有一個光鮮亮麗的外表。對于婚姻更是如此,現(xiàn)代社會虛榮的物質(zhì)文化也浸染到了婚姻層面,艾米不允許自己的生命中出現(xiàn)“離婚”這個污點,就算婚姻早已經(jīng)名存實亡,她依然要成為父母書中描繪的那個完美的艾米,以及大眾認知中完美的美國女人艾米。
空虛的、虛榮的物質(zhì)文化是左右艾米與尼克婚姻的罪魁禍首,從大都市紐約來到鄉(xiāng)村密蘇里,這已經(jīng)對艾米的完美婚姻打上了不完美的標記。然而,她與尼克之間只有麻木不仁的性生活,在偌大的家中二人已經(jīng)形同陌路,她不允許自己一手經(jīng)營的完美生活就此崩塌。因為,艾米已經(jīng)看到了回到家鄉(xiāng)密蘇里的尼克日益消沉,早已不是在紐約街頭與她約會的迷人男子。于是,用一個個巨大的謊言和精心設(shè)計的“謀殺案”來重塑自己的婚姻與愛情,甚至是自己的丈夫,是艾米所有行為的最終目的,這也是她為了自己虛偽婚姻做出的最后努力。
小說家吉莉安·弗琳和導(dǎo)演大衛(wèi)·芬奇共同將導(dǎo)致這場婚姻鬧劇的根源鎖定在虛榮的大眾文化和社會文化上,消費文化與物質(zhì)文化也是導(dǎo)致尼克和艾米悲劇婚姻的直接原因。
三、艾米“腹黑角色”的生成
《消失的愛人》真實地反映了當代美國文化的現(xiàn)狀,女權(quán)主義、個人主義、消費主義等,全部都在影片敘事當中有所體現(xiàn)。然而這些當代文化內(nèi)容都以一種辯證的方式出現(xiàn)和存在,在尼克與艾米的婚姻悲劇中,以小見大地折射出整個美國社會的現(xiàn)實狀態(tài)。
艾米是一個完美主義者,同時也是大眾文化消費的對象。從小到大,艾米就是父母暢銷書中描繪的那個完美女孩,也是別人眼中的完美美國女性,她的生活就是對于完美美國女性養(yǎng)成術(shù)的踐行,她不允許自己的身體上、生活上存在任何的瑕疵。這個被艾米仔細經(jīng)營的完美女孩“艾米”是她應(yīng)對這個世界的空虛的外殼,是她作為一名女性的生存武器。也正是艾米隨性灑脫的個性和完美的形象深深吸引了尼克。出身鄉(xiāng)村的尼克也是在時時刻刻經(jīng)營著自己完美的美國男性形象,他將自己在大都市學(xué)習(xí)到的所有吸引女孩的招數(shù)都用在了艾米身上,他讓自己風(fēng)趣迷人,時時刻刻用浪漫的方式傳遞著自己的愛意,塑造著自己品位獨特的都市型男形象。在任何一個人看來,艾米與尼克的結(jié)合是兩個如此完美的人的結(jié)合,是理所應(yīng)當?shù)氖虑椤T谔摌s心作祟下,艾米選擇尼克成為自己的另一半,這種選擇是有其必然性存在的,是大眾文化影響下的必然選擇結(jié)果。然而,艾米由于從小就被作家父母塑造成為暢銷書中的那個完美女孩,她是所有美國人心中完美的代名詞,已經(jīng)是當代美國大眾文化的一部分,潛在的她也是大眾文化消費的對象。因此,在艾米的愛情和婚姻模式當中,消費意識也成為潛意識中的引導(dǎo)因素,她的個人形象和婚姻生活是需要被大眾消費的,這也使她永遠無法容忍丈夫和婚姻的不完美,即使是尼克已經(jīng)小腹微凸、邋遢懶惰,她依然要別人知道自己的婚姻是如童話一般幸福美滿的。
同時,艾米也是一個女權(quán)主義者,在愛情與婚姻當中她是絕對的權(quán)力掌控者。結(jié)婚之后,她想盡一切辦法經(jīng)營自己的婚姻生活,讓自己的愛情和婚姻保鮮,如結(jié)婚周年紀念日的時候,她總會制造各種浪漫的小驚喜給尼克,但是這些依然無法減緩二人愛情與婚姻的腐敗速度。這些小驚喜變得越來越乏味,二人漸漸失去了共同語言,毫無感情可言。當這場婚姻變得越來越不可控時,艾米無法容忍控制力的缺失,于是在二人結(jié)婚五周年紀念日當天,自導(dǎo)自演了一場血腥的“謀殺案”。她需要對尼克顯示出自己的絕對控制力,她不是尼克認為的那個頭腦空空的女孩。
于是,通過設(shè)計自己的失蹤、出逃、虐殺與回歸,艾米在大眾與傳媒的幫助下重新成為這場婚姻中掌控權(quán)力的人,實現(xiàn)了自己對尼克的絕對控制力。如果尼克選擇與她離婚,大眾與媒體無疑會將他用語言“撕碎”,更別提生活在自己家鄉(xiāng)密蘇里這個人際關(guān)系親密、思想保守的鄉(xiāng)村。
因此,《消失的愛人》中艾米的“腹黑角色”的生成是大眾消費文化、女權(quán)主義等文化思想共同作用的結(jié)果,是當代美國社會文化的產(chǎn)物。這樣一個被文化異化的女性形象,潛在地表露了當代美國女性的隱匿心理,是一個想要成為卻無法成為的角色形象,極度觀照了當下的美國文化。
四、結(jié) 語
電影是文化的投影,是文化與美學(xué)共同作用的產(chǎn)物。大衛(wèi)·芬奇的黑色電影風(fēng)格在《消失的愛人》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fā)揮,無論從影片敘事內(nèi)容的架構(gòu)上,還是影片呈現(xiàn)的視覺風(fēng)格上,都達到了一致和統(tǒng)一。在這個黑暗、冷酷的婚姻故事背后,折射的是當代美國社會的文化生態(tài),以及人們在媒體的引導(dǎo)下表面熱情實際冷酷的精神狀態(tài),人們對于娛樂新聞的趨之若鶩以及精神世界的匱乏,讓媒體輕而易舉地反復(fù)塑造尼克的個人形象,人們只在乎自己從媒體上看到的,而不在乎事實真相究竟是什么。這也是作家吉莉安·弗琳和導(dǎo)演大衛(wèi)·芬奇共同做出的精彩絕倫的文化敘事,以及對于社會現(xiàn)實的無情批判。以文化作為解讀敘事安排和主題內(nèi)容的工具也成為解讀和研究《消失的愛人》的一個新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