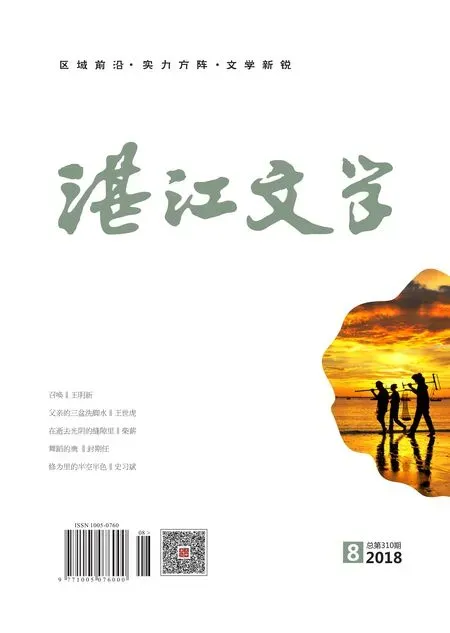作為人生救贖的詩歌
◎ 余愛群 程繼龍
詩人梁永利以“自在”與“拷問”命名詩集,虔誠地述說自己的意志,以自覺的態度展現自我。相比年少時的“輕狂”,當下詩人以更為清醒的理智去審視、“拷問”自身。實質上這也是詩人對自己內心的一種回應,人到中年,生活在現代社會,面對世事的變遷,不可避免地感受到現實與人生無法平復的“傷痛”與“無奈”,疲憊感充斥開來,轉而“寄情表志”于詩,因此也把抒情言志的詩變成了“為人生”的詩。
饒有意味的是,梁永利詩歌里面滲透著人生的冷暖。這種個體生命(生存)的境況和情味,詩人并沒有刻意去展示,而是于詩歌的言語自然流露而出,成為其詩歌一種“個人”的底色。詩人不同境遇的觸發,淋漓盡致地展現在詩歌中。
人生軌跡行進到中年,增添了許多況味。詩人現實的無奈感、人生的疲倦感,是因為他所生活的雷州半島——祖國最南端近幾年的巨大變化,進一步“沖擊”他的生活乃至記憶而觸發的。“酸雨冒出煙囪/污水堰塞海口/大工業的迷霧/在小城鎮盤旋”(《南風行》),在城市發展的過程,就連小城鎮也受到“工業”迷霧的“侵襲”。“因橫笛在春天亂吹/我的親人/打聽不到歸家的方向/南邊是新高速入口/北邊留給高鐵”(《寧愿》),“我的親人”打聽不到歸家的方向,詩句帶有一種淡淡的無奈感,仿佛所到之地是“陌生”的地方,一座擁有“新高速”“高鐵”的新型現代大都市。詩人不止一次訴說他所熱愛、懷念那座——青蔥綠意和富有“鄉野氣”的港城,“我的故土/榕樹景氣/聚云為雨”,多雨水潤澤的鄉土,生長著四季常存的“綠意”,久久的回蕩在詩人的心。《日毒》中“老爸說:‘要把蟲曬死/麻雀說:‘把彈弓槍曬壞’”展現了原始、粗野的情趣。“鄰家建了新樓/填平半畝農地/他見不著日毒/從此/他只用普通話講/太陽很猛”分明能感受到一種巨大的消逝,卻又無法流于外表地訴說情感,沒有一個字說著痛,卻著實讓人感覺到無言的哀傷。粗野、富有生命力的東西——象征著農村的一種閑情逸致的變化、消逝,在“老爸”的話語中表現得非常明顯,一種“野生情趣”被鄰家的新樓“填平”了。“燈光下/鄉音沙啞”(《寧愿》)苦澀之感吞咽而下,隱約感到詩人的痛楚。如果夜晚燈光下映照出詩人的身影是在沉思中掙扎,那么“沙啞”便是詩人經受到的一種歲月打磨的痕跡。由此可知,詩歌使他在現實生活“無處伸展”的感受——人生無奈、人性的痛苦得以傳達,而這種自我“暴露”,正是詩歌的“救贖”最真切的內涵,刻錄他現實生活狀態。
然而現實的風霜刀劍并沒有磨平梁永利“棱角”,早年理想和超脫是他一直找尋、堅守的“赤誠”。詩句“飛瀑怎么能放棄年少的情懷”(《高山看不見它的影子》)仿佛是對自己的發問,詩人仍舊擺出“踏浪的姿勢”(《草裙舞》)。于是承載了“救贖”的詩表現出他豐富的人生體驗。詩人不僅抒寫韻味無窮的自然,還抒寫親友之間的默默溫情,《過故人莊》簡單的敘述中表現了詩人對“瘸子”的真摯情誼。結尾的戲謔“邀請我過故人莊作策劃/我先讓他背熟一首詩”巧妙道出多年相識,否則難以開此玩笑。《踏浪》“出門會碰上浪/踏唄/二狗想著大魚/能換上大妞的花裙子”以輕松爽朗的調子訴說友人“二狗”的純情憨厚。他在詩中寫禪意的幻想,包含了人生哲思。“回向我的心——天實無量的壽/地是有法的廣/人是可度的佛”(《拉薩的雪》),天地都是“無疆無界”的寬廣,“人是可度的佛”即人能自我救贖——回歸內心。“南無阿彌陀佛——這句話咽吞了無數次/口水已如甘露/每天/我慢慢播灑/菩提樹下紅塵沉下/沉下”(《過海南開示》),詩人心境的安然,塵世的紛擾在此刻化為“過眼云煙”,心靈得到撫慰。
同時,他抒寫的自然,不局限于自然本身,還包含投射于自然之上的個人生活選擇和志趣,甚至對一個時代的普遍思考。“操著土話的詩人”、“家鄉的紅樹旁”、“家鄉的燈塔”、“滅跡的鹽和海欖花”、“家鄉門楣上”、“特呈島的碼頭”、“坡頭村”、“童年一瞬間高了枝頭”、“七月才把我插進家鄉的泥土”,鑲刻在一層話語里的是“故鄉”所指意蘊。除了詩歌“能指”——所能組合處理得到的“整體”詩意,這些詩語本身就有濃重的地方特色與鄉土味,因而顯示出獨特魅力。“我又想到家鄉的燈塔/那束光/照亮航道/夜鷗翔集的地方/只見燈塔的倒影”(《關于塔》),很多詩篇都能讀到詩人家鄉、故土的回憶與念想,事物間的聯想,于千里之外也能憑借其敏感的詩心,將紛繁事物聯系起來,牽連出生命記憶。“鄉音刻進枝頭/重新長出”(《石榴》),因為石榴花香涵蓋了鄉音的象征意義,所以詩人把鄉音重新刻進石榴枝頭,重新長出的是濃濃“鄉情”與美好“希冀”。詩人強烈的“融根歸土”意識,自覺“察省”式地在生活中尋找、感悟,并于詩句中吐納,獲得的是一種抒發式的“救贖”。寄存“鄉魂”的詩歌“救贖”他的人生,乃至于詩人精神、魂魄。
正因感知到詩歌“救贖”他的精神、魂魄,就不難理解“詩如其人”的含義。讀其詩如見其人,我們吟詠一番,能在他的詩歌中讀出一種明朗,隨性。得益于“江山之助”與人生歷練,他寬厚、豪爽又細膩的性情是湛江的原野、海岸、城市環境中生長出來的。詩人對故鄉充滿著一種情懷與理想,喜歡抒寫“漁火”“漁女”“海國”“踏浪”。這種“海水味”打小醞釀在他的胸懷,而在詩歌中舒展。這種隨性也是詩人自我的節度,趨向自由的心。且隨性中見其含有一種瀟灑之氣的“超脫”,詩歌中多處體現“超脫”意味與傾向。從“跳動的人心/它的棲息/從不依山傍水”到“寂寞時過著自在的生活/歡樂時遍野飛歌”(《九龍山》),詩人不依山傍水、特立獨行的瀟灑身姿佇立在我們眼前。“恒河有沙/你的終南/坐等日暮/乃至無窮”(《無窮》)是詩人對陶淵明采菊悠然性情的繼承。這些,都是詩人對“自由”的汲取與承擔。
象形地看,他的詩歌所承擔的“功效”有如酒——借以釋放自我性情,慰藉人生。詩歌《喝》“我夢中念念不忘的這個字/我成為罪過的這個字/誰知道錯在哪里/是暗夜的驚動?/是一個酒鬼的企圖?”,人生的疲倦感借著酒意抒發開來,不求一醉方休的灑脫感,只希望消解濃得化不開的惆悵。“喝”好像是都市中人擺脫不了的生活的一部分,交際應酬,親朋聚會,個人感傷,都少不了“喝”這個動作,正如詩人所寫的“一個字會連接我日常的舉措”。而詩句“所有發誓同笑聲一樣”,“笑”與“哭”感覺的是哀痛,“發誓”就像“笑聲”看似多么“荒誕”,但是醞釀在其中況味又值得人細細斟酌。隨著酒中飄散醇香,人生品嘗到的“味道”也慢慢彌散開來。
詩人對于生活中的“任何”都以認真的姿態去承受,面對病痛,詩人“倔強”的“閃電一遍遍找出疼痛的根源”,時而也會用“最黑的星是膽結石”詩語幽默的化解“沉重”——“躺下/死亡的門檻或許幾秒鐘”(《結石》)。這正體現了作為塵世中人——生命的殘缺,但又因有了“殘缺”,生命才算真正意義上“完整”。刻印上了個人的生存痕跡的詩歌,將一層層獨特的生命體驗以“真實的面貌”展現在眾人面前。因此詩充當了酒,在梁永利的抒寫中越發濃烈,搖曳出韻味,成就了一種個人的秘密的救贖之道。就像“蝙蝠”咬碎“黑色”,在“嘶鳴”聲中“把寫詩的真理”掛在臉上(《我想西川的南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