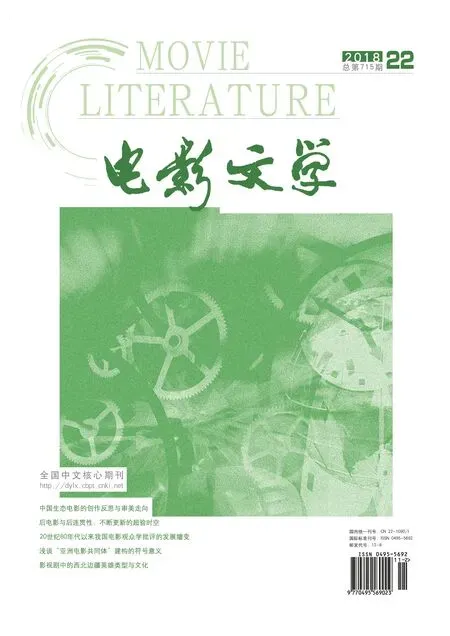異質(zhì)與融合
——電影《米花之味》空間的敘事表達(dá)與文化的現(xiàn)代性建構(gòu)
秦 蒙
(曲阜師范大學(xué) 傳媒學(xué)院,山東 日照 276825)
電影《米花之味》是鵬飛導(dǎo)演的一部傣族題材電影,同時(shí)也是他的第二部劇情長篇,相比于第一部作品《地下香》的過于壓抑,《米花之味》在畫面質(zhì)感上呈現(xiàn)出清新明亮的特點(diǎn),藍(lán)天白云、綠色的原野、寶石藍(lán)屋頂?shù)龋利惖淖匀伙L(fēng)光,詩意化的鏡頭拍攝,使得影片在進(jìn)行空間敘事及探討現(xiàn)代性問題的同時(shí)不至于壓抑、沉悶。影片是一種張力的空間敘事,空間的異質(zhì)與現(xiàn)代性的融合是影片的側(cè)重。
一、空間的張力與異質(zhì)敘事
空間作為電影敘事的載體,其設(shè)置不僅是介紹故事發(fā)生的環(huán)境及背景,并且是促進(jìn)張力敘事和異質(zhì)敘事的生發(fā)。多賓曾說過,“人的周圍環(huán)境以其獨(dú)特的方式來表達(dá)整部影片或影片個(gè)別場面的主題”。勐卡村內(nèi)的空間與村外的城市空間作為敘事空間,通過對空間中的人物、事件及細(xì)節(jié)進(jìn)行處理,構(gòu)建起影片的敘事意義。
(一)鄉(xiāng)村空間外弛內(nèi)張的張力敘事
“我們在雙臂的重量中發(fā)現(xiàn)了向下拉的力量,在雙肩上發(fā)現(xiàn)了向上舉和支撐的力量。軀干顯示了對地面的壓力,雙腿則顯示向上的力量以支撐這種壓力。”鵬飛電影外弛內(nèi)張形成的張力給觀眾帶來一種獨(dú)特的敘事感受。影片用一種詩意化的方式進(jìn)行拍攝,客觀、平淡、寧靜的“小津”式長鏡頭,喂豬、采茶、晾衣等勞動成了一種自在的審美行為,細(xì)節(jié)的展示具有生活化、真實(shí)感,對于矛盾的存在也以一種溫情的方式予以對待和處理。張與弛之間相互作用的張力,通過外在的隱忍與克制來作用內(nèi)在的矛盾與沖突,最終達(dá)成了深層次的和解。家、寺廟、溶洞作為鄉(xiāng)村敘事空間中的典型場所,是張力敘事的核心和主體。外出打工歸來的單身母親與留守鄉(xiāng)村的“問題”女兒之間關(guān)系的轉(zhuǎn)變發(fā)生在家這一場所空間中,兩人的關(guān)系由疏離到初步和解,敘事張力在個(gè)體空間中得以體現(xiàn)。寺廟作為公眾性、儀式性的場所同樣是敘事的張力空間,寺廟本是莊重、嚴(yán)肅的場所,各種矛盾卻在此空間中得以呈現(xiàn)乃至激化,這便是空間的張力敘事所產(chǎn)生的影片的敘事意義所在。從家到寺廟,從個(gè)體空間到社會性空間,相反的作用力一直在其中產(chǎn)生作用,促進(jìn)敘事張力的張弛,促進(jìn)空間敘事的進(jìn)展,最終達(dá)到極致。于是,溶洞作為升華性空間,具有凈化的作用,相反的力量達(dá)到了暫時(shí)性的和解,幾乎只有最純粹的存在,人性的本真存在、人與自然的天人合一的境界,空間的張力敘事在此得以完美和升華。
(二)城鄉(xiāng)空間二元結(jié)構(gòu)的異質(zhì)敘事
在城市中心視點(diǎn)的鄉(xiāng)村敘事之外,新力量導(dǎo)演們逆向而動,開始采取城鄉(xiāng)并存的二元視點(diǎn)敘事,并觀照鄉(xiāng)村。影片對城鄉(xiāng)空間的意義的發(fā)掘十分重視,城市空間雖然沒有進(jìn)行重點(diǎn)的展現(xiàn),卻作為與鄉(xiāng)村空間對立的空間構(gòu)成了空間的異質(zhì)敘事,敘事核心是雙方對于自身文化主體性的要求。空間是權(quán)力的場域,不同空間形成了一種權(quán)力關(guān)系。影片所呈現(xiàn)的鄉(xiāng)村空間,則由一種異質(zhì)的關(guān)系所構(gòu)建,充滿了矛盾、異質(zhì)的存在。葉喃開車回鄉(xiāng),行駛在彎曲的山路上,此時(shí)城市的汽車與鄉(xiāng)村的牛車兩種異質(zhì)的交通工具相遇形成了一種明顯的權(quán)力關(guān)系,顯示了城市空間的敘事主動性。影片中異質(zhì)性的存在還有很多,推動了空間敘事意義的構(gòu)建。從哥等人在葉喃家吃飯商討,滿嘴的掙錢大計(jì),腳下卻扔了一地的骨頭殘?jiān)@些帶有諷刺性意味的場景敘事以及電視上騰沖挖玉的“瘋狂”場面插入葉喃母女吵架之前,顯示了城鄉(xiāng)兩種異質(zhì)文化空間的對抗及鄉(xiāng)村文化在面對城市文明的主動性時(shí)所產(chǎn)生的焦慮。異質(zhì)敘事并非簡單把諸多差異、矛盾的成分堆砌在統(tǒng)一的空間中,而是一種巧妙的結(jié)合、有機(jī)的聯(lián)系,相互作用形成了異質(zhì)的糅合。寺廟是典型的異質(zhì)空間存在,影片對寺廟的強(qiáng)調(diào)及其敘事意義的構(gòu)建格外重視。寺廟本應(yīng)是神圣的祭拜場所,而在影片中卻成為提供Wi-Fi的公共娛樂廣場,手機(jī)、現(xiàn)代婚紗、“錢花”等本不屬于寺廟的事物頻頻出現(xiàn)在寺廟中,解構(gòu)了寺廟的神圣性,同時(shí)也是對于鄉(xiāng)村文化現(xiàn)代性的解構(gòu)與建構(gòu)。這種不同空間的元素雜糅或者說共存于同一空間中相互矛盾卻又相互關(guān)聯(lián),這種異質(zhì)性敘事設(shè)置推動了城鄉(xiāng)空間二元結(jié)構(gòu)的敘事實(shí)現(xiàn)。
二、少數(shù)民族文化的現(xiàn)代性建構(gòu)
從廣義上來講,現(xiàn)代化指的是傳統(tǒng)社會邁向現(xiàn)代社會的進(jìn)程,是一種人類歷史演進(jìn)的過程,現(xiàn)代性則是這一過程的本質(zhì)。從哲學(xué)上講,現(xiàn)代性是對于主體性的確認(rèn)及構(gòu)建。現(xiàn)代化對少數(shù)民族的影響是巨大的,改變了他們的工作生活和思想價(jià)值觀,對于勐卡村的多數(shù)村民,他們的視線集中在如何拉取更多的游客以得到更多的經(jīng)濟(jì)利益,對于宗教習(xí)俗甚至是“花錢搞個(gè)民俗儀式就可以了”。少數(shù)民族文化的現(xiàn)代性是通過城市與鄉(xiāng)村、宗教與科學(xué)、世俗與信仰、現(xiàn)代與民族等的異質(zhì)與融合來建構(gòu)的。
(一)現(xiàn)代性與民族性并置的鄉(xiāng)村圖景
少數(shù)民族如今的生存狀態(tài)是一種現(xiàn)代性與民族性并置的圖景,同一文化空間內(nèi)兩種異質(zhì)的文化主體并存,兩者之間的內(nèi)在抵牾是無法逃避的文化現(xiàn)代性構(gòu)建難題。影片中,葉喃多次駕車行駛在鄉(xiāng)村的路上,汽車的尾氣與靜止的鄉(xiāng)村美景構(gòu)成一幅意味深長的畫面,現(xiàn)代工業(yè)的“產(chǎn)物”與傳統(tǒng)的鄉(xiāng)村自然的“交鋒”會是怎樣的結(jié)果,答案留給我們思考。飛機(jī)是影片中極具現(xiàn)代性的一個(gè)標(biāo)志,它只在影片的結(jié)尾處實(shí)際出現(xiàn)過一次,其他時(shí)候則是通過勐卡村民們的描述出現(xiàn),飛機(jī)作為重要的敘事因素推動了故事的進(jìn)展,作為現(xiàn)代性的標(biāo)志推進(jìn)了現(xiàn)代化的建設(shè)。而此時(shí)勐卡村卻在進(jìn)行祭拜石佛的民族舞蹈排練,想恢復(fù)中斷五年的石佛祭拜儀式。在賀英旺這一人物身上,這種異質(zhì)文化的并置性體現(xiàn)得很明顯,作為村里的年輕人,他接受了現(xiàn)代文化的熏染,扎著臟辮、舉辦文藝晚會、組織社工活動等,具備了現(xiàn)代性的思維方式,但骨子里的民族性扎根很深,在面對文化現(xiàn)代性構(gòu)建難題無法解決時(shí),依然遵循過去傳統(tǒng)參與民族祭拜儀式。現(xiàn)在性與民族性在這一文化空間中形成了一種特殊的關(guān)系,為了促進(jìn)經(jīng)濟(jì)發(fā)展實(shí)現(xiàn)現(xiàn)代化轉(zhuǎn)型,必然要將民族的封閉性打破,但他們本有的民族性根基則要求其必須保持自我的文化價(jià)值和獨(dú)特性。于是,便形成了這種現(xiàn)代性與民族性并置的生存狀態(tài),兩種文化主體處于動態(tài)的相對平衡之中,平衡是暫時(shí)性的,終將會被打破,這是少數(shù)民族文化現(xiàn)代性建構(gòu)的必然結(jié)果,結(jié)果如何則在于時(shí)代的抉擇以及歷史的作用。
(二)宗教價(jià)值的現(xiàn)代性體現(xiàn)與認(rèn)同
隨著社會現(xiàn)代化進(jìn)程的推進(jìn),不是宗教的體現(xiàn)與認(rèn)同發(fā)生了變化,而是人們主動去進(jìn)行的價(jià)值觀的選擇。宗教是一個(gè)社會系統(tǒng)的黏合劑,但在現(xiàn)代性環(huán)境下,這種歸屬與認(rèn)同已弱化,被個(gè)體同時(shí)具備的公民與族群的雙重的身份所逐漸取代。在公民身份下,追求經(jīng)濟(jì)利益是社會現(xiàn)實(shí);在族群身份下,保持宗教的信仰是個(gè)人的宗教權(quán)利。這種物質(zhì)追尋與精神尋覓的矛盾體現(xiàn)在影片中,村民懷有信仰遇到佛跡會予以敬拜,但仍然會為了提高經(jīng)濟(jì)收入而花錢舉行儀式以破除宗教禁令。個(gè)人對宗教是一種矛盾態(tài)度,族群集體對于宗教也是處于疏離與聚合的矛盾之中,這是一種集體的信仰弱化,或者說是一種集體的宗教價(jià)值抉擇。宗教作為少數(shù)民族村落的權(quán)威,掌握了鄉(xiāng)村意見表達(dá)的權(quán)利與話語的權(quán)利,這種權(quán)威的呈現(xiàn)很大程度上是經(jīng)由各種宗教儀式表達(dá)出來的,宗教儀式的弱化與世俗化在本質(zhì)上代表了宗教的話語權(quán)威的削弱,而現(xiàn)代性的話語權(quán)威是通過科學(xué)來表達(dá)的,這在電影中有明顯的表現(xiàn)。喃杭為了調(diào)換位置用巧克力討好林老師,結(jié)果被林老師反將一軍,運(yùn)用科學(xué)知識將吃過的巧克力重新組合成完整的一塊。喃湘露因紅斑狼瘡引發(fā)腎衰竭,“叫魂”這種宗教迷信之術(shù)并沒有挽回她的生命。影片中這些內(nèi)容的出現(xiàn)代表了宗教與科學(xué)對于話語權(quán)利的較量。“宗教是一個(gè)動態(tài)的概念,是一種與特定的時(shí)代相聯(lián)系,具有多種表現(xiàn)形態(tài)和豐富內(nèi)涵的社會性的精神現(xiàn)象與文化現(xiàn)象。”所以,宗教并非是一成不變的,宗教價(jià)值在社會現(xiàn)代化進(jìn)程中發(fā)生了變化,具有了現(xiàn)代性體現(xiàn)與認(rèn)同,宗教作為少數(shù)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宗教的現(xiàn)代性發(fā)展與變化構(gòu)成了少數(shù)民族文化的現(xiàn)代性建構(gòu)。
(三)民族文化身份的主體性建構(gòu)
在現(xiàn)代化社會中,對于文化的定位是要求其具備普遍性,形成一種普世價(jià)值觀。而少數(shù)民族的特質(zhì)則是其文化的獨(dú)特性,這是他們民族性的根基,因此,少數(shù)民族在文化現(xiàn)代性構(gòu)建中必然會身陷囹圄,無法真正審視自我、衡量自身價(jià)值,無論是單個(gè)的人還是整個(gè)的社會群體,都在面對這樣難以解決的問題。鵬飛導(dǎo)演的電影《米花之味》則是從這個(gè)范疇上來思考文化的主體性,與其他思索少數(shù)民族文化主體性的電影不同,鵬飛導(dǎo)演沒有用一種偏見的敘事態(tài)度去批判現(xiàn)代性對少數(shù)民族的影響,而是堅(jiān)持用一種客觀、平靜的拍攝方式來反映少數(shù)民族的本真文化,關(guān)切少數(shù)民族在民族文化身份的現(xiàn)代性建構(gòu)過程中的困惑、矛盾與選擇,關(guān)切他們的民族文化身份的主體性建構(gòu)。
回顧之前中國的一些關(guān)于少數(shù)民族的電影,特別是關(guān)于云南的少數(shù)民族的電影,包括《米花之味》在內(nèi),有一個(gè)共同之處,便是在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構(gòu)中,社會性別隱喻一直參與了云南影像文本對民族身份的建構(gòu),女性向來是影片的敘事焦點(diǎn)及民族身份的構(gòu)建媒介。女性作為一種被動的書寫,浸透了少數(shù)民族身份的主體性設(shè)想,透露出少數(shù)民族建構(gòu)自身文化身份的主體性的艱難。葉喃作為影片中重要的女性,她所經(jīng)歷的一切,包括婚姻破裂、母女隔閡、宗教限制等,表層上是她自我身份認(rèn)同的失敗,歸根到底則是民族主體性身份認(rèn)同與建構(gòu)過程的困難與艱辛。影片中的男性雖然大多數(shù)處于“失語”狀態(tài),但關(guān)鍵時(shí)刻的話語權(quán)還是顯示出其男性主導(dǎo)的權(quán)威,這種沉默的掌控力阻礙了性別身份的現(xiàn)代性建構(gòu)。因此,民族文化身份的主體性建構(gòu)不僅在于普世化的同時(shí)堅(jiān)持自我的獨(dú)特價(jià)值,還應(yīng)該打破這種性別身份建構(gòu)的障礙,以實(shí)現(xiàn)本質(zhì)上的少數(shù)民族文化的現(xiàn)代性建構(gòu)。
三、結(jié) 語
電影的敘事并非是去實(shí)際解決民族文化的現(xiàn)代性問題,它是在給我們提供一種參考,讓我們能夠去深入思考少數(shù)民族文化身份在現(xiàn)代社會的主體性構(gòu)建。如何將自我的意識與普世的價(jià)值觀進(jìn)行協(xié)商乃至融合、升華,在現(xiàn)代化境地中,既能將多重的文化身份帶來的認(rèn)同焦慮予以消除,同時(shí)又能構(gòu)建自我文化身份的主體性,這才是影片的敘事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