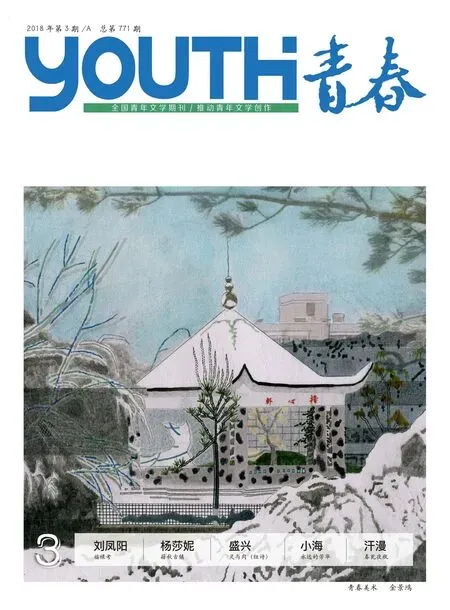籍秋古鎮(zhèn)
每天晚上,我都會(huì)為女兒讀個(gè)小故事,“三個(gè)士兵疲憊地走在一條鄉(xiāng)村路上。他們又累又餓,事實(shí)上,他們已經(jīng)兩天什么東西也沒吃了。”
女兒睜大眼睛聚精會(huì)神聽的樣子十分可愛。
“當(dāng)三個(gè)士兵接近一個(gè)村莊時(shí),村民忙開了。他們知道士兵通常是很餓的,所以家家戶戶都把可以吃的東西都收藏起來。饑腸轆轆的士兵們想出了一個(gè)絕招。他們向村民們宣布,要做一鍋石頭湯。好奇的村民們?yōu)樗麄儨?zhǔn)備好了木柴和大鍋,士兵們真的開始用石頭煮湯了。當(dāng)然,為了湯的味道更鮮美一點(diǎn),他們還需要一點(diǎn)佐料,比如鹽和胡椒什么的……當(dāng)然有一點(diǎn)胡蘿卜會(huì)更好……卷心菜呀、土豆呀、牛肉呀配一些也不錯(cuò)。”
我頓了頓,女兒焦急地問,“后來呢?”
“后來,”我指著繪本上的圖畫說,“最后,一鍋神奇的石頭湯真的煮好了,好喝得連國王都可以喝了。”
“媽媽,你喝過石頭湯嗎?”
“我……”
“媽媽媽媽,你別睡啊,醒醒啊。”
我從亂七八糟的夢里醒過來,發(fā)現(xiàn)口水流到半倒著的副駕駛的椅背上。我偷偷擦了擦嘴角,又不動(dòng)聲色地用后背蹭去椅背上的口水痕跡。我看了看正在開車的林老師,他扭過頭看我。我微微笑了笑,不知道有沒有被他看見我流口水的尷尬畫面。
“最近工作不順利?”林老師問。
“啊,你怎么知道?”
“一直皺著眉頭說夢話。”
“我說什么啦?”我坐起身子,把放倒的靠背調(diào)直。
“‘不行不行,根本沒有可行性,預(yù)算也超出了……’大概這些。”
我想是夢到昨天晚上,我把做的報(bào)告打印出來修改,越看越不滿意。內(nèi)容就不說了,遣詞造句也一股濃濃的學(xué)生腔,真不知道怎么能寫出像同事那樣超酷的報(bào)告出來。
“能力差唄。”我嘆了口氣。
“還是這么不自信。”林老師輕輕地說。
“我們到哪兒了?”我問。
“如果我告訴你,作為地理老師,我迷路了,你會(huì)不會(huì)笑話我?”
“什么嘛。”我笑了起來。
“是真的,從上一條盤山路出來以后,GPS就完全失靈了。”
“那我們要去的籍秋古鎮(zhèn)在什么地方?”
“應(yīng)該是往西,但現(xiàn)在陰天看不見太陽,不過從植被的生長來看,就那個(gè)方向了。”林老師指了指左前方,“現(xiàn)在就這一條小道,順著走,碰到人再問吧。”
真是,我心里嘀咕著。從早晨八點(diǎn)多開車到現(xiàn)在快兩點(diǎn),就是為了不被熟人發(fā)現(xiàn)的約會(huì)。林老師是我高中時(shí)的地理老師,那個(gè)時(shí)候莫名其妙地喜歡地理課、喜歡他。搞不清是因?yàn)橄矚g地理課而喜歡他,還是因?yàn)橄矚g他而喜歡地理課。但同學(xué)們卻沒有我這樣的感受,甚至覺得林老師是一個(gè)爛呼呼臟兮兮的老男人,地理課也乏味無趣。
我看了看林老師的側(cè)面,發(fā)髻線后退,剩下的頭發(fā)也都油膩稀疏。車?yán)锷l(fā)著一股濃重的老油氣味。說不上難聞,卻實(shí)實(shí)在在飄散在車?yán)锏目諝庵校拖褚粭澊u木結(jié)構(gòu)、百年以上的老房子。車子也是夠破,吭噔吭噔地在鄉(xiāng)村小道上跑了四五個(gè)小時(shí)。硬邦邦的座位把我的屁股顛得發(fā)疼。
小道漫長,看不見盡頭,路邊盡是相似的深秋景色,不覺有些犯困。突然林老師伸出右手,一把抓住了我擱在腿上的左手。我一個(gè)激靈,完全清醒了。我這才真切地意識(shí)到,答應(yīng)和林老師出來,就已經(jīng)做好了和他發(fā)生關(guān)系的打算。真的做好準(zhǔn)備了嗎?
我緩緩抽回手,是啊,就像完成高中時(shí)沒有完成的心愿。情竇初開的少女總會(huì)有一個(gè)想像的對象,那個(gè)時(shí)候想像不偏不倚地落到了林老師頭上。他不優(yōu)秀,甚至看起來的確爛呼呼臟兮兮,但既然已經(jīng)決定了,況且車已經(jīng)開出四五個(gè)小時(shí),沒有辦法回頭了。
“哎,你看,前面有村子,也許已經(jīng)到了。”林老師指著給我看。
眼看著村莊就在半山腰的霧氣中半隱半現(xiàn),車子的發(fā)動(dòng)機(jī)卻突然停止了工作。林老師趕緊踩住剎車,車子在這條僻靜的小道上不動(dòng)了,而且再也沒有動(dòng)。重新啟動(dòng)了幾十次,完全沒有反應(yīng)。林老師打開前車蓋,也看不出哪里出了問題。
“叫拖車吧。”我說,突然反應(yīng)過來,這里沒有信號。“電話信號也沒有嗎?”我拿出手機(jī)看了看,屏幕顯示時(shí)間的數(shù)字跳了幾下,之后全屏呈現(xiàn)密集的黑色圓點(diǎn)。什么情況?我看看林老師,他舉著他的手機(jī)對我搖搖頭,屏幕上也滿是黑點(diǎn)。
我們只好棄車,背上行李包步行向村莊走去。山林間的秋葉可謂美艷。杏黃、火紅,我像是出生以來第一次如此近距離地接觸到滿目的秋景,皮膚像在濃郁的色彩中被染上了凄涼的暖色。大概是從那一刻起,有什么東西滲透皮膚,進(jìn)入到了血液,林老師也是這樣吧。或許是我胡思亂想,但這以后,我們被我們熟悉的城市拋開了,然后很久很久我們都沒回去。
“你醒醒,喂,醒醒……”我被韓方修推醒。
“嗯……”我迷迷糊糊睜開眼睛,看見韓方修睡在我右側(cè)。雖然還沒結(jié)婚,但我覺得遲早會(huì)的吧。他是那種看上去可以信賴、以及理解力較高的人。
“你知道林老師去哪兒了吧?”他問。
“你什么意思,”我突然清醒了,“不知道你在說什么。”
“你不知道我在說什么,可我清清楚楚聽到你在說什么。你說,‘林老師,我們離開這兒吧,這兒不對勁。’你知道他在哪兒對不對?”
“我不知道!”我清楚自己又說夢話了。
林老師的老婆過來問了幾次,她查到林老師失蹤之前和我有過幾次通話記錄。我一口咬定我和林老師只是通話,除了上次高中同學(xué)聚會(huì),我們沒有見過面。我一直重復(fù)著,我和林老師沒有單獨(dú)見過面,沒有單獨(dú)見過面。
“也許我說了關(guān)于林老師的夢話,那還不是因?yàn)榱掷蠋煹睦掀趴偸莵眚}擾我,不過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夢’罷了。”因?yàn)槲液土掷蠋熓遣徽?dāng)?shù)年P(guān)系,不可以承認(rèn)。所以我沒有單獨(dú)見過林老師,沒有單獨(dú)見過林老師。漸漸我發(fā)現(xiàn),我似乎真的沒有見過林老師。那個(gè)深秋的古鎮(zhèn),不過是我的一個(gè)夢,夢里面有一個(gè)和林老師長得相似的男人。他是我少女情懷的一個(gè)投影,一個(gè)虛構(gòu)。
我和林老師沒走盤山公路,覺得走山間小道會(huì)更快到達(dá)村子。山坡比遠(yuǎn)看起來陡峭得多,林老師走在前面,時(shí)不時(shí)拉下我的手或小臂。到達(dá)中途的一個(gè)緩坡,我們停下來,大口地喘氣。
“是不是陰天的關(guān)系,霧蒙蒙的像做夢一樣。”我伸手摘下一片楓葉,噠的折斷聲,清晰地傳進(jìn)耳朵。“這里好安靜啊。”我深深吸了口潮濕的空氣。
“如果我說地理老師喜歡詩詞的話,你會(huì)不會(huì)笑話我?”林老師問。
“我保證能猜到你現(xiàn)在想吟什么詩。”我笑起來。
“你說。”
“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于二月花。”
“哈哈哈哈。”我們一起大笑起來。
一路上我們沒有什么對話,不過是“小心”“看那棵樹”“快到了”……我使勁想回憶上學(xué)時(shí)和林老師有關(guān)的事情,可以當(dāng)作話題的共同經(jīng)歷。可我尋找不到他成為我少女幻象的原因,感到記憶一片蒼白。
村莊的輪廓越來越近,可依然籠罩在氤氳霧氣中,連呼吸也變得飄渺,遍尋不到現(xiàn)實(shí)感。又走了大約十多分鐘,一株似乎代表著崇高、傳統(tǒng)、準(zhǔn)則、保守、愚昧……的巨大榕樹出現(xiàn)在面前。我嘲笑自己為什么要給一棵樹加上眾多定義,前方的村莊有著不容侵犯的姿態(tài),讓人不愿踏入,也不想接近那棵樹。
特別是榕樹下,一尊石馬的雕像,馬頭上清晰可辨的鬃毛,和雕刻得細(xì)致入微的雙眼皮,馬身曲線柔軟,卻因?yàn)榘祷疑氖模兄嫣氐臎_突和不自然。
“好奇怪的感覺啊。”我喃喃說著。
“天氣不好的原因吧。”林老師拉起我的手,“先找到人再說吧。”
我們踏進(jìn)了這個(gè)從唐代開始,就以石刻著稱延續(xù)至今的籍秋古鎮(zhèn)。
再爬上一個(gè)小土坡后,便出現(xiàn)了青石板鋪陳的小路。路邊丟棄著很多雕刻著傳統(tǒng)圖案的石塊和類似井沿、石鎖,或不知道用途的大石塊。有的相對完整,有的四分五裂,有的上面已經(jīng)長出高高的植物。人家也漸次出現(xiàn),多是石頭建造的古樸建筑。院落、照壁、房屋……一律是滲透了十足水氣的深灰色。
一口水井邊的地面異常濕滑,一個(gè)老奶奶捧著一盆衣服,小心翼翼地走下來。老奶奶的臉上、手上全是像刀刻似的深深皺紋。不知是因?yàn)樨?fù)重,還是年紀(jì)的原因,就像即將飄落的枯葉,整個(gè)人顫顫巍巍,
“你好,”林老師客客氣氣地問,“請問鎮(zhèn)上的酒店,呃,客棧,不是,旅館在哪里啊?”
老奶奶抬頭看看我們,目光直直地落到我的臉上。
“姑娘臉上的輪廓線條真好看啊。”老奶奶答非所問。
“請問……”林老師提高了嗓門。
“住店啊,”老奶奶說,“過了前面那個(gè)路口,看見一座掛燈籠的房子,轉(zhuǎn)進(jìn)房子旁邊的巷子,穿過巷子就是,一直往西,招待所就在廢棄的石雕場最西面了。”
我們謝過老奶奶繼續(xù)向前走,很快看見那座掛燈籠的房子。所謂燈籠,已經(jīng)破敗到千瘡百孔,只留下淡粉色的曾經(jīng)是燈籠的印記。
轉(zhuǎn)進(jìn)巷子,林老師說,“果然是雕刻之鄉(xiāng)啊,連這樣的老人家都知道輪廓、線條這些。”林老師看看我,“不過,真的是好看啊。”
我突然感到臉紅,也因?yàn)槟樇t這件事而臉紅,像情竇初開的小姑娘,實(shí)際上已經(jīng)和韓方修談了兩年多,大概快結(jié)婚了。
行走在落葉的青石小路上,我和李老師的手握得緊緊的,即使是和韓方修,即使是熱戀時(shí)期,也沒有人這樣握緊過我的手。我希望這不是林老師的一往情深,只是他單純的生理上的欲望,因?yàn)楝F(xiàn)在的我感到瑟瑟發(fā)抖,想要趕緊完成任務(wù),趕緊回家,離開這個(gè)陰森森的地方。
小巷窄到展開雙臂,指尖可以觸碰到兩邊房屋的墻壁。我真的這樣做了,展開胸、肩,盡量延伸手臂,左右手的指尖抵住濕漉漉的灰色石墻。林老師微笑著靠近我胸口,我突然間迷茫在一片溫?zé)嶂小A掷蠋焼伪〉纳眢w,竟然充滿熱量,暖融融的,讓我一個(gè)勁地向前抵住他的身體,直到把他抵在潮濕的石墻上。
我記得第一次和韓方修接吻的時(shí)候,已經(jīng)靠得那么那么近了,卻始終沒有最后接觸到一起的勇氣,像隔著一公里那樣的一厘米距離。即使最后吻在了一起,卻還是能夠感受到彼此,感受到他的嘴唇,他的鼻子。
我和林老師緊緊地接吻,像衣服上的撕拉粘一樣。一邊是密密麻麻的彎鉤,一邊是密密麻麻勾住彎鉤的拱形。像發(fā)泄學(xué)生時(shí)代沒有發(fā)泄出的情緒,那個(gè)時(shí)候就想像這樣緊緊勾住林老師的脖子,死死地把他固定住。就像忘記了一切,連腦漿都在溫?zé)嶂腥诨V钡胶芫靡院螅覀儌z一起深深地嘆了口氣。
“走吧。”林老師說。
我跟在他后面,看見他的背包上,因剛剛被壓在潮濕的墻壁上,而呈現(xiàn)出一塊近似圓形的水跡。像是一張表情怪異的人臉,輪廓模糊,線條扭曲。
窄巷出來,眼前豁然開闊到眼睛不能適應(yīng)。巨大的廢棄石雕場,嗖地一下落在眼前。各種大型的雕像、石塊、殘缺,與灰蒙蒙的天空呼應(yīng)著填滿整個(gè)視線。我不自主地發(fā)出“啊”的驚嘆,其壯觀是因?yàn)槌涑庵斯さ暮圹E,卻又像是幾千年天然形成。
各種人物雕像,完全沒有規(guī)律。左邊是唐代刻畫寬袖舞動(dòng)的飄逸,右邊卻是母子牽手,像街心公園里的和諧主題的裝飾品。更多的是斷臂缺腿的殘次品,或被雨打風(fēng)蝕的殘存部分。種類豐富到無法想象,石刻的宇宙星球、萬圣節(jié)的鬼怪幽靈、微縮的高樓建筑或真實(shí)建筑的局部、人體器官、現(xiàn)代化的電器用品、精密器械、繁雜的交通工具、單獨(dú)的字句或成篇的書籍長卷……更多的是表情扭曲、四肢殘缺的人像。就像是幾個(gè)世紀(jì)被定格,然后胡亂堆砌在一大片的空地上,層層疊加,有的甚至高達(dá)十來米。
“如果我說,這和我想像的世界非常接近,你會(huì)不會(huì)覺得我很可怕?”林老師問。
我尷尬地笑笑,實(shí)在不知道怎么回答。后來我回憶這個(gè)震撼的畫面時(shí),始終看不到我當(dāng)時(shí)看見的那個(gè)角度。大多數(shù)時(shí)候,我只能看見像航拍一樣遠(yuǎn)遠(yuǎn)的高空鏡頭。我身穿灰紫色的抓絨外套,像一個(gè)小點(diǎn),站在采石場的最東邊。與東倒西歪的大型石刻相隔對峙,又像一幅整體似的色調(diào)融合為一體。林老師呢?那個(gè)時(shí)候林老師在哪里?回憶的畫面里我看不到林老師的身影,就像我獨(dú)自面對一整個(gè)世界。
“直線沒有辦法穿過去呀”林老師說。
我們只好沿著采石場的邊緣向西,但實(shí)際上,它沒有完全清晰的邊緣。我們踩著滾落下來的石刻人頭、支離破碎的顏體石碑、停滯的巨型鐘表……步履艱難地爬行。
找到鎮(zhèn)上旅館的時(shí)候,已經(jīng)將近晚上十一點(diǎn)。
“師傅,醒醒,住店。”林老師推醒裹著軍大衣,睡在前臺(tái)邊長沙發(fā)上的值班員。
“嗯,嗯——”師傅含含糊糊地爬起來,緊了緊身上的軍大衣,摳了摳眼角的眼屎。“噢,身份證。”師傅伸出手。他的手掌粗糙干裂,一條條像是刀劃刻的僵硬掌紋。
“這個(gè)鎮(zhèn)上人口不多吧?旅游的也不多嗎?過來的時(shí)候沒碰到幾個(gè)人。”林老師問。
“鎮(zhèn)上人不少,好幾百個(gè)呢。”師傅一邊抄著身份證號碼一邊說,“旅游?這個(gè)季節(jié)哪會(huì)來這兒旅游,這兩天就降溫咯,你們也真會(huì)挑時(shí)間。”
“看天氣預(yù)報(bào)沒說要降溫啊。”林老師看看我,“你帶的衣服夠不夠?”我搖搖頭,扯了扯袖子“這件是最厚的了。”
“不怕。”林老師摟了摟我的肩膀,又是一股暖意襲擊全身。我慌張地意識(shí)到,我始終在等待林老師觸碰我,就像這輩子如果沒有林老師的觸摸,我或許會(huì)死不瞑目一樣,也許從上他的地理課開始就有了類似這樣的感覺。
拿了鑰匙走進(jìn)房間,我竟然幻想著我被抵在門后的狂吻,相互瘋狂脫掉對方的衣服,一路散落的衣服延續(xù)至床邊。可我們還是按部就班地用電熱水壺?zé)碎_水,泡了帶來的方便面,等著面泡軟,然后稀里嘩啦地吃完了整碗的面條,喝完了最后一滴面湯。
我洗澡的時(shí)候,林老師悄無聲息地進(jìn)了衛(wèi)生間。隔著玻璃的水汽,林老師看起來就像油畫色塊堆積的平面。我用手抹開玻璃上的水霧,看見林老師慢慢地脫掉外套、長褲、秋衣、秋褲和內(nèi)褲。
我就是在等待這個(gè)時(shí)刻吧,我曾經(jīng)痛恨自己為什么渴望和一個(gè)沒有任何突出優(yōu)點(diǎn)的男人做愛,這種欲望把我折磨的死去活來。他會(huì)介紹全國礦產(chǎn)資源的分布,會(huì)講解八大行星的運(yùn)行,會(huì)分析水循環(huán)的過程……僅此而已,一個(gè)地理老師正常不過的課本知識(shí)。但現(xiàn)在什么也想不起來,他只是一具肉體,男性器官凸顯。多年以后,課堂以外,能看到灰藍(lán)色外套和舊懨懨牛仔褲里面的肉體,我渾身柔軟下來。一路上滿眼的石塊像巖漿一樣融化,我拉開淋浴的玻璃門……
我們躺在標(biāo)準(zhǔn)間的一張窄床上。“你知道,我就要退休了嗎?”林老師問。
我點(diǎn)點(diǎn)頭,撫摸著林老師寬寬的肩膀。我沒有料到第一次和林老師做愛,卻像與對方熟知很久。撫摸著林老師的松弛卻光滑的皮膚,感受著節(jié)奏平穩(wěn)卻自然舒暢的過程。我想確定這不是一個(gè)我創(chuàng)造出來的男人,當(dāng)然不會(huì)是,何必創(chuàng)造出這樣一個(gè)不完美的男人,有太多太多可以說起的缺陷,但對于我來說,這是多么的完美。完美到我不需要承擔(dān)與他相處的責(zé)任,不需要一點(diǎn)點(diǎn)的造作和掩飾,只在這一刻享受它的完美,我希望它更持久和漫長,但還是會(huì)結(jié)束,但已經(jīng)足夠完美。
回去之后的很多夜晚,沒有林老師的夜晚,我會(huì)在黑暗中睜開眼睛,最大限度地回憶林老師支撐在我的身體上方,回憶他摩挲我的背脊。我知道時(shí)間過去越久,回憶就會(huì)越淡。我希望通過反復(fù)復(fù)習(xí)可以記住他的味道,他手指的觸感,他帶給我的渾身癱軟的松弛。這其中一定有了再加工,因?yàn)槲乙呀?jīng)無法確認(rèn)和林老師在一起是什么樣的狀態(tài),也更加不確定,林老師是一個(gè)活生生的人。
早上起來,我和林老師在旅館前臺(tái)旁的一張桌子上吃了粥和一種夾了梅干菜的烤餅。屋子里已經(jīng)變得冷颼颼的了,昨晚那個(gè)穿軍大衣的服務(wù)員說,半夜開始降溫的。也許是因?yàn)橐徽苟己土掷蠋熅o緊抱在一起,相互取暖,絲毫沒有感到降溫。但現(xiàn)在熱乎乎的粥喝到一半,剩下的已經(jīng)變得只有溫?zé)帷?/p>
“附近有賣衣服的地方嗎?”林老師問服務(wù)員。
“沒有。”服務(wù)員干脆地說,“是不是嫌冷?我這兒有一件我老婆放這兒的棉大衣,要不給這姑娘穿起來?不過就這一件。”
林老師接過棉大衣遞到我面前,“穿起來吧,別凍感冒了。”
我看了看這件灰不溜秋的棉衣,毫無式樣可言,好在湊近聞了聞沒有什么難聞的味道,只有一種像石灰的氣息,并不讓人討厭。我套上棉衣,覺得自己像一只笨拙的灰熊。
林老師說,“我回下房間,把能套上的衣服都套上,冷得真是有點(diǎn)兒吃不消啊。”
林老師回來的時(shí)候,滑稽的樣子讓我撲哧一下笑出來。大概是在里面套上了所有的秋衣秋褲,皮衣里面還有一件牛仔外套和夾層的夾克,整個(gè)身體看起來繃繃的壯壯的,襯著一顆發(fā)髻線特別高的腦袋,渾身都是喜劇效果。
我走上前,挽起林老師的胳膊,看看他看看自己,悄悄地對林老師說,“看起來很般配啊。”
林老師忍著笑,轉(zhuǎn)身又問服務(wù)員,“鎮(zhèn)上的汽車修理行在哪里啊,我們的車在山下壞了,能不能找個(gè)修車師傅看看?”
“我怎么知道修車行,我又沒有車。”服務(wù)員硬邦邦地說。“不過,你可以到鎮(zhèn)委會(huì)問問,那里還有個(gè)展覽館可以參觀下。”
我們打聽了去鎮(zhèn)委會(huì)的路,裹緊衣服出了旅館大門。
一夜之間,樹葉全部掉光了,光禿禿的樹枝張牙舞爪地扭曲成各種姿態(tài)。陽光倒是不錯(cuò),卻被呼呼的大風(fēng)吹得異常稀薄。所有的青石路面和墻壁變成了干燥的淡灰色,像蒙上了一層灰霾,隨時(shí)就要干裂開來。
鎮(zhèn)委會(huì)的牌子像墓碑一樣豎立在一棟石頭房子的前面,我和林老師進(jìn)去后才發(fā)現(xiàn),房子沒有門。
“林老師!”突然坐在房子里的一個(gè)人叫起來。我和林老師在眼睛適應(yīng)了屋里的昏暗之后發(fā)現(xiàn),鎮(zhèn)委會(huì)里的一個(gè)工作人員竟然是我的同班同學(xué)于萬陽。我慌忙把牽著林老師的手松開,但我想這并沒有逃過于萬陽的眼睛。
“林老師,張……張琪?”于萬陽有些驚訝地看著我們。“噢——你們……噢噢。”于萬陽很快恢復(fù)了鄉(xiāng)村干部應(yīng)有的語調(diào),“你們是來旅游的吧,歡迎歡迎,你們倆……沒什么沒什么,上學(xué)那會(huì)兒就有點(diǎn)兒看出來了。”
既然在這偏僻的地方出現(xiàn),既然是我和林老師牽手而行,什么解釋都沒有辦法掩飾了,不如就大大方方地面對好了。我對于萬陽笑了笑,反倒林老師緊張兮兮地說,“不是不是,我們正巧……不是你想的那樣。”
我想著和林老師一整晚相擁而睡,以為的溫存、感情,不過就是兩個(gè)人在黑暗里見不得人的齷齪行徑,心里有了些別扭難受。
“嗯,你現(xiàn)在在這里工作?”林老師問于萬陽。
“對,小小的書記而已,主要是管理鎮(zhèn)上的人各司其職。大學(xué)畢業(yè)后就過來了,大成績沒做出什么,不過大家也都安居樂業(yè)。”于萬陽筆直地站立著,相比較上學(xué)時(shí)縮頭縮腦的樣子,有了一點(diǎn)兒事業(yè)有成的樣子。
那時(shí)我記得于萬陽似乎追過我,雖然我不能確定,但他總喜歡拉著我和我談未來。他說他讀完大學(xué)后想考公務(wù)員,去做大學(xué)生村官。那幾年“大學(xué)生村官”這幾個(gè)字,帶著一種莫名的神秘。我根本無法想像,一個(gè)外地的大學(xué)生可以把握好農(nóng)村里那種錯(cuò)綜復(fù)雜的裙帶、人際關(guān)系。
我記得我有個(gè)遠(yuǎn)方的農(nóng)村親戚,她說話簡直就像《紅樓夢》里的平兒,“奶奶的那利錢銀子,遲不送來,早不送來,這會(huì)子二爺在家,他且送這個(gè)來了。幸虧我在堂屋里撞見,不然時(shí)走了來回奶奶,二爺倘或問奶奶是什么利錢,奶奶自然不肯瞞二爺?shù)模俨坏谜諏?shí)告訴二爺。我們二爺那脾氣,油鍋里的錢還要找出來花呢,聽見奶奶有了這個(gè)體已,他還不放心的花了呢。所以我趕著接了過來,叫我說了他兩句,誰知奶奶偏聽見了問,我就撒謊說香菱來了……”光是這錯(cuò)綜的繁雜關(guān)系,就把我弄得暈頭轉(zhuǎn)向,不覺得于萬陽可以弄得清楚,不過現(xiàn)在看來,他真的做到了。
“林老師我?guī)銈兊教幑涔浒伞!庇谌f陽說。
我悄悄把凍得冰冷的手伸向林老師,卻被他擋了回來。我一點(diǎn)兒也不想在這里閑逛,這和我想像的浪漫旅行完全不同。我只想立刻回到旅館,或者趕緊修好車回家。
于萬陽帶著我們走了將近十分鐘,到了鎮(zhèn)上的展覽館。展覽館里陰森森的,陳列的巨大石頭發(fā)出猙獰的寒光。是不是所有的展覽館都像魔窟一樣昏暗、陰冷。
“從唐代起,這里就是是一座開采石頭的礦山,這里的石頭具有雕刻性、堅(jiān)韌性、石材性,石材性主要是指體積夠大,”于萬陽滔滔不絕地介紹著,“以及藝術(shù)性,它具有藝術(shù)創(chuàng)作所需的顏色、光澤和相應(yīng)的紋理……”于萬陽指著一排半人高的石塊自豪地說,“這些就是我們這里產(chǎn)出的石頭。”
我根本無心聽他講解,只覺得冷到骨頭里。
“我出去曬曬太陽,在外面等你們。”我說著向外走。
“也好,我再慢慢看一會(huì)兒。”林老師沒有回頭,眼睛專注在石頭上面。
已經(jīng)完全是冬天的景象了,滿眼灰色,包括穿著灰不溜秋棉衣的我。太陽蔫蔫地照耀,一副敷衍的態(tài)度。展覽館門前,一張?zhí)僖伪伙L(fēng)吹日曬得破敗,接縫處好多斷裂,但顏色異常深邃,青褐色中透出暗黑的酒紅色,像血液灌注而成。
我撣了撣椅子上的灰,一屁股坐上去,細(xì)細(xì)感受陽光微弱的暖意。我越來越厭惡這個(gè)地方,特別是和林老師做愛過后。我承認(rèn),那是令人愉悅的體驗(yàn),但僅此而已。或許是我想要的太多,但明知道不可能有更多。現(xiàn)在我的目的已經(jīng)達(dá)到了,好了,現(xiàn)在可以讓我回去了嗎?
正想著,一只貓不知從哪里躥出來,輕手輕腳地踱到我腳邊,在我的小腿上來回地蹭。真是一只讓人開心的小家伙,肥嘟嘟的,也許是野貓,但橘白相間的花紋干凈油亮。它并不認(rèn)生,瞇著眼睛抬頭看著我,打了一個(gè)特別大的哈欠。嘴里尖銳的牙齒全部暴露出來,一瞬間顯出野性的張揚(yáng),嘴一合上,又是一副軟萌的姿態(tài)。
我拍拍大腿,示意貓咪上來。它果然騰地一躍,力度平穩(wěn)地落在我的大腿上面。就像為了讓我撫摸而存在。觸摸到貓咪腦門的時(shí)候,它那一副享受的表情把我給逗樂了。我一下一下地從頭頂順溜到尾巴,心里就像蜷縮在棉花云里一樣,膨脹到要化開。困意不知不覺地上來了,迷迷糊糊像看到我摟著我的女兒,溫柔地在給她講故事……
“哈哈哈哈……”我被笑聲驚醒,睜開眼睛,看見兩個(gè)黑影逆著光站在我面前。
“坐著也能睡著?”林老師笑著說。
“這畫面真好看呀。”于萬陽轉(zhuǎn)到我左邊,又繞到我的右邊,把不大的眼睛瞪得大大的。“真好看,就像一座雕塑作品。別看我是學(xué)文科的,這些年在這兒天天看石頭、看雕像,我也懂一些的嘛。《少女與貓》,這個(gè)名字怎么樣?漂亮,真是漂亮。”
貓受到打擾,躥下地面縮到了墻角。我沒有搭理于萬陽,拍拍褲子上粘著的貓毛站起身,“林老師,車子什么時(shí)候能修好啊?”
“車子?噢,對,車子。小于,你們這兒有修理汽車的嗎?”
“鎮(zhèn)上是沒有啊,得跟著運(yùn)石頭的大車下山,就是我跟您說的開采石料那兒,有大車來運(yùn)石料,下了山肯定會(huì)有的。”
“噢,挺不方便的啊。”
“是啊,林老師。不過你不是說想在這兒住一陣子嘛,那就不著急了。”
“怎么不著急。”我嘟囔著,心里責(zé)怪林老師為什么對回不去一點(diǎn)兒也不緊張。我很想對他發(fā)火,卻礙于于萬陽在場憋在心里。
中午,我們在于萬陽的辦公室吃飯,簡單的兩個(gè)菜,兩人竟說要不醉不歸。
“你也一起喝一點(diǎn)兒嘛。”林老師已有了些醉意,拉著我把酒杯遞到我面前。
我扭過頭,越發(fā)地不高興。我想要和林老師像度蜜月似的膩在一起的感覺。我想像著我們牽手在風(fēng)景如畫的景區(qū),像情侶一樣避開人群接吻,我們輕聲笑著開一些暗示性的小玩笑相互挑逗,我們迫不及待地回到酒店,一次又一次地纏繞住對方的身體。
可是眼前的這個(gè)男人,一杯接著一杯地灌下白酒,從臉紅到指尖,高高的額頭上滲出可見的點(diǎn)點(diǎn)油心。他大聲地說著話,左邊嘴角積著一塊白沫。
“你說是不是,我教了一輩子的地理了,我從來就沒和土地打過交道。我那教的是什么地理啊,就是照本宣科,就是誤人子弟。我跟你說我對那種生活早就厭煩透了。你知道是不是,你能看出來是不是,我那個(gè)時(shí)候就是喜歡張琪,怎么樣,我就是選她當(dāng)?shù)乩碚n代表。人家不愿意。我能怎么樣?我是人民教師,我這輩子都是人民教師。我要當(dāng)農(nóng)民,我和你說的是認(rèn)真的,明天,是不是明天,你告訴我,什么時(shí)候,幾點(diǎn)集合,四點(diǎn)半?我去。你知道什么,我力氣大得很呢,我渾身都是精力,我發(fā)泄不掉,找女學(xué)生?開玩笑,我是人民教師。我能干那種事嗎?我明天一定去,我老當(dāng)益壯,我喜歡這兒,真的,我就想過這種日子……”
于萬陽戳戳我,“你攙林老師回旅館吧,他說明天要和村民一起去開采石料,四點(diǎn)半在這兒集合,別忘了啊。”
“你趕緊找人把我們車子修好。”我冷冰冰地丟下一句,架著林老師吃力地站起來。林老師比我想像的輕很多,但一路走回旅館房間,我已經(jīng)累得散了架。
我手一丟,林老師直挺挺地倒在床上。他一會(huì)兒鼾聲如雷,一會(huì)兒又呼吸微弱。我坐在床邊的一把靠背椅上,迷迷糊糊地以為林老師死掉了。
我們排著隊(duì)繞著林老師的遺體緩緩逆時(shí)針而行,嗚嗚懨懨的哭泣聲不時(shí)從隊(duì)伍中傳出。靈柩邊的花籃散發(fā)出百合的甜膩香氣,我看見林老師的臉被化妝成慘白的底色,兩頰打上不自然的紅暈。中式的衣領(lǐng)緊緊圍裹著脖子,像是窒息而死。林老師不喜歡這樣的妝容啊,他想要黝黑的皮膚,沒有束縛的伸展四肢,肆無忌憚地表達(dá)愛意,而不是這樣僵硬地躺著。
我突然間想要哇地張口大哭。我捂住嘴巴,不愿引起別人的注意。我和林老師只是普通的師生關(guān)系,從學(xué)生時(shí)代開始,我始終把對林老師的愛欲埋藏在心靈最深的地方,剛一萌芽就用整個(gè)身體使勁地把它掩埋。林老師說,“張琪,你來當(dāng)?shù)乩碚n代表。”
“不。”我堅(jiān)決地回答,堅(jiān)決到發(fā)出的聲音不像是我自己的聲音。我渴望和林老師相處,甚至在夢里和他擁抱、接吻。可是我又害怕和他相處,哪怕只是去辦公室送作業(yè)或試卷。我知道我面對他會(huì)露出恐慌的表情,會(huì)手足無措,這些在一個(gè)大人眼里,會(huì)顯而易見地暴露出內(nèi)心。所以一定不能被他發(fā)現(xiàn)。
但是,現(xiàn)在他已經(jīng)無法發(fā)現(xiàn)了。因?yàn)樘稍陟`柩里的林老師,緊閉著雙眼。臉色慘白,堆積著不自然的紅暈。我再也控制不住悲痛的情感,沖到靈柩邊,尖銳的哭聲沖破喉嚨,“林老師……林老師……你不要走……你陪我啊……”
“張琪——怎么了?又做噩夢?”我被人搖醒。
我睜開被眼淚迷糊住的眼睛,眼前朦朦朧朧,過了一會(huì)兒才看清身邊的韓方修。
“我夢到林老師死了,我和很多人去參加他的追悼會(huì)。”
“林老師只是失蹤,而且那么大的年紀(jì),離家出走的可能性也不是沒有。”
“嗯。”我不置可否地點(diǎn)點(diǎn)頭。
沉默片刻之后,韓方修翻到我身上。他已經(jīng)熟悉我身體上的每一個(gè)地方,沒有親吻,也沒有過多的撫摸。像以往一樣的輕微快感之后,韓方修輕聲地說,“你還是去醫(yī)院看看吧,神經(jīng)科或者心理科。”
“我沒什么問題,就是做噩夢而已,不用你操心。”
“你整夜整夜地說夢話、做噩夢,你難道不覺得這很嚴(yán)重嗎?”
“這段時(shí)間工作壓力比較大,可能過一陣子就好了。”我想把壓在我身上的韓方修推到旁邊,可他一動(dòng)不動(dòng)。
“我不知道你和林老師之間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想過問你們的事情,我只是希望你盡快把身體弄好,這么長時(shí)間了,你沒有睡過一個(gè)完整的覺,整天迷迷糊糊,經(jīng)常神經(jīng)質(zhì)一樣地發(fā)作。況且我的睡眠質(zhì)量也受到很大影響,這樣下去,我不知道我們……”
“你不要說了!”我抑制不住地咆哮起來,我死死揪住韓方修濃密的頭發(fā),把他從我身上揪下。我覺得我就像發(fā)狂的野獸,四肢猛烈地踢打,我大叫著,“我沒有問題,我不是神經(jīng)病,你覺得我有問題對不對?你就是嫌棄我了,你懷疑我和林老師有關(guān)系是不是?你覺得我不正常對不對?我沒有神經(jīng)病,沒有神經(jīng)病……”
硿嗵一聲,我從靠背椅上栽到地面,我爬起來,發(fā)現(xiàn)剛才自己睡著了。林老師的鼾聲又劇烈地響起。也就是在昨天,我和這個(gè)男人相擁在這張床上,現(xiàn)在看來卻那么陌生。屋里的一切也陌生起來,它們吸收了寒冷和黑暗,像僵硬的石塊不再有一點(diǎn)溫存。
我躺到林老師身邊,厚厚的棉衣隔著我們。我試探著把手伸進(jìn)林老師的褲子,希望像昨晚那樣,在里面尋找到熱情。但一切都是冰冷的,松弛得像忘記了我的存在。我睜大眼睛,感受到天色漸漸黑暗,今晚真是冷得出奇,滲透進(jìn)骨頭里的寒冷。在沒有任何取暖設(shè)施的房間,和一具尸體一樣冰冷的男人。恍惚間,我模糊記起我的女兒,一個(gè)溫軟的小嬰兒,散發(fā)著熱乎乎的奶香。像是為了與這里的一切發(fā)生沖突而存在,她在哪里,她到哪里去了?
半夜時(shí)分,我聽見細(xì)細(xì)索索的聲音,我睜開眼,什么也看不見。
林老師在黑暗里說,“我去開采石料的地方看看,你繼續(xù)睡吧。”
我憑著聲音,一把抓住林老師的衣角,“不要走,陪我。”
“已經(jīng)快四點(diǎn)半了,來不及了,乖,你還能再睡好久呢”林老師甩開我的手。然后聽見開門、關(guān)門,離開的腳步。
我又睡著了,睡得昏天黑地,持續(xù)的噩夢,夢到被韓方修發(fā)現(xiàn)了我的出軌行為,夢到詹總把我熬夜寫出的報(bào)告狠狠砸在我身上,夢到我被封印在石塊里做成一座雕像,夢到我被人按住注射鎮(zhèn)定劑,夢到白色的天,灰色的地,夢到我在石窟里凍得瑟瑟發(fā)抖……終于我渾身冰涼地從噩夢里掙脫出來。
天色大亮,可還是沒有絲毫的暖意。我凍得骨頭發(fā)痛,無論哪里都沒有一絲溫度。這到底是什么地方,這還是我的噩夢吧。我想趕緊醒過來,我會(huì)死在我的夢里。
我在房間里轉(zhuǎn)悠,不知道該去哪兒。對了,我還帶著一本書,看書可以打發(fā)時(shí)間。我打開雙肩包,伸手向包里摸索。我驚恐地摸到一塊冰冷的石塊,哆嗦著一點(diǎn)點(diǎn)地從包里抽出。一本石頭雕刻的《死亡通知單》緩緩出現(xiàn)在眼前。灰暗的色調(diào),沉甸甸的手感,書名凹陷地雕刻在長方形的石塊上,側(cè)面書頁的紋理纖細(xì)致密。但無法打開,無法打開一本石頭雕刻而成的小說。我尖叫著將石頭書摔在地上,石頭書破碎成七八塊不規(guī)整的形狀,但是還是打不開,打不開。
我沖出房間,路過旅館前臺(tái)的時(shí)候,看見穿著軍大衣的服務(wù)員,僵直地坐在椅子上一動(dòng)不動(dòng),眼珠卻跟著我的步伐轉(zhuǎn)動(dòng)。
我飛奔向鎮(zhèn)委會(huì),我要問問于萬陽這是怎么回事。先找到林老師,然后盡快離開這個(gè)鬼地方。緊張地奔跑也沒有讓我感到身體發(fā)熱,或者是因?yàn)闈駳庹慈驹诹艘路希痈械酱坦堑暮狻N易プ约海樽约旱淖彀停蚁胍约盒褋恚M快醒過來。
鎮(zhèn)委會(huì)里,于萬陽正和一個(gè)男人在一起吃飯,爐子上燉著一鍋湯。咕嘟咕嘟地沸騰,卻看不見一點(diǎn)兒熱氣。
“林老師在哪兒?”我氣喘吁吁地問。
“和其他人一起去采石料了呀,你不是知道的嗎?”于萬陽從鍋里舀了一碗湯,喝了一大口。
“我要去找他,這里有問題,我要和他離開這里。”
“哪有什么問題啊,吶,我已經(jīng)安排好了,你呢,就去展覽館那里曬曬太陽,摸摸貓就行了,其他也沒什么適合你做的。”
“我要回去,請你告訴我林老師在哪里,我再說一遍我要回去。”
“怎么可能回去呢?”于萬陽慢悠悠地說,“先喝碗湯嘛,喝完了去展覽館那兒坐著。”
“我不要喝什么湯,我要回去!”我一腳踢翻了身邊的爐子,湯鍋從爐子上滾了下來。一鍋石頭,一鍋浸泡在水里的石頭。大大小小,灰不溜秋的石頭。這就是于萬陽正在喝的湯。
我呆呆地望著滿地的水跡和石塊,望著于萬陽憤怒的表情,半天說不出話來。
“喂喂,”Stella擠擠我肩膀,“你快醒醒,詹總說話你也敢睡?”我強(qiáng)打起精神,大概是昨晚寫報(bào)告寫得太晚了,整個(gè)人恍恍惚惚的。
“所以說,”詹總的聲音永遠(yuǎn)充滿熱血。“這次去籍秋古鎮(zhèn),既是旅游,又是工作,更是我們團(tuán)隊(duì)精神的體現(xiàn)。”
“去籍秋古鎮(zhèn)?”我低聲問Stella,“去幾天?”
“三天。”
“這么久?我還得回去問問韓方修。”
“這不還是未婚夫嘛,現(xiàn)在就盯這么緊?”
“他這個(gè)人就會(huì)疑神疑鬼的,反正我覺得他疑神疑鬼的。”
“所以說,”詹總又提高了一度嗓門,“這次的企業(yè)拓展旅游,大家會(huì)全天候地相處,這樣可以暴露一個(gè)人的缺點(diǎn),也可以展示一個(gè)人的優(yōu)點(diǎn)。對中高層來說,是發(fā)掘后備力量的好時(shí)機(jī),對新人來說,是向前輩學(xué)習(xí)的好機(jī)會(huì)。所以每個(gè)人都務(wù)必參加。”
鎮(zhèn)委會(huì)陰冷的房子里,于萬陽瞪著我,冷冷地說,“林老師是不會(huì)回去的了,你安安分分地坐展覽館門口去,再?zèng)]有什么其他的事情了,這有什么不好呢?”
“我要找到林老師,我要離開這里,我要找到林老師,我要離開這里,我要找到……”我喃喃地說著,向門口走去。
“你根本走不掉的。”于萬陽冷笑著說。
走出沒有門的門,我看見一群灰壓壓的人群從四面八方涌向鎮(zhèn)委會(huì),旅館的服務(wù)員,和我穿著一樣棉衣的服務(wù)員的老婆,洗衣服的老奶奶,還有殘缺身體部位的男人、女人、老人、孩子…… 他們把我包圍起來。他們臉色灰暗,目光僵硬。我想推開人群,但他們站立得紋絲不動(dòng)。洗衣服的老奶奶一把捏住我的胳膊,其余的人幫襯著,把我架著向展覽館走去。
顫顫巍巍的老奶奶,竟然有那么大的力氣。我完全掙脫不了她的手臂。我高聲呼叫救命,呼喊林老師,聲音像被冷漠的陽光稀釋,在大片的灰色中發(fā)不出共鳴。
我被人群綁縛著來到展覽館門前,他們用一根粗粗的藤條把我捆綁在展覽館門口的藤椅上,手固定在膝蓋上,屁股完完全全坐在椅子當(dāng)中。這樣的姿勢結(jié)結(jié)實(shí)實(shí),我無法挪動(dòng),就連藤椅也像由石板地面生長出來一樣,紋絲不動(dòng)。陽光直線刺入我的眼睛,我沒有辦法睜開眼睛,我恍惚看見他們抱來一只貓,用同樣的藤條,把貓捆綁在我的膝蓋上,我的左手被迫按在貓的頭部。
“快摸貓,快摸貓……”他們齊聲說。
手無法動(dòng)彈,無法躲閃,貓露出鋒利的牙齒,扭轉(zhuǎn)頭,在我的左手腕處咬下深深的傷口。鮮血滴滴答答地落下,順著身體,滴落到藤椅上,藤椅像干渴的禾苗,汩汩地把血液吞噬進(jìn)去。由暗紅變?yōu)轷r紅,又由鮮紅一點(diǎn)一點(diǎn)凝固成暗紅。
Stella扯下我的墨鏡,“快醒醒,到了,睡美人。”
突然被摘下墨鏡,陽光異常刺眼,眼睛瞇縫著一點(diǎn)點(diǎn)睜開。大巴車上的同事,正陸陸續(xù)續(xù)地下車。
“喔,到了?”我說,“這就是籍秋古鎮(zhèn)?”
我下了車,狠狠地伸了個(gè)懶腰,大巴車一路顛簸,身體像被綁縛住一樣緊繃。四下望去,各種旅游團(tuán)隊(duì)、散客人來人往,絡(luò)繹不絕。從停車場出來不遠(yuǎn),我們排著隊(duì),點(diǎn)著人頭,進(jìn)了籍秋石刻博物館。
“從唐代起,這里就是是一座開采石頭的礦山,這里的石頭具有雕刻性、堅(jiān)韌性、石材性,石材性主要是指體積夠大,”導(dǎo)游滔滔不絕地介紹著,“以及藝術(shù)性,它具有藝術(shù)創(chuàng)作所需的顏色、光澤和相應(yīng)的紋理……”
“張琪——”突然有人喊我。
我四處尋找,看見一個(gè)人小跑著過來。是我的中學(xué)同學(xué),叫什么來著。感覺就在嘴邊的名字卻說不上來。
“啊,是你啊,你好。”我一邊想他的名字一邊打著招呼。
“你們是來旅游的?”他問。
“是啊,你也是來旅游?”
“我在這里工作。”他說著,從夾在腋下的小包里取出一張名片。
上面寫著:籍秋國際旅游投資管理有限公司黨委書記 于萬陽
對,于萬陽,他叫于萬陽。
“哇,于書記啊。”我笑著說,“好久不見啦,畢業(yè)有多少年了?”
“哪有多久,上次中學(xué)同學(xué)聚會(huì)我們不都參加的嗎?”
我覺得頭腦發(fā)昏,難道真像韓方修說的因?yàn)樗卟缓茫旎谢秀便钡摹?/p>
“哦,對對對。”我言不由衷地說。
“你后來喝斷片了吧?”于萬陽問。
“后來?”
“后來你又拉著我去酒吧,和我說你不相信林老師會(huì)變那么老。你還說要送件禮物給林老師,因?yàn)槭堑乩砝蠋熉铮韵胨蛪K珍稀的石頭,還向我咨詢石頭的問題。”
“是嘛,好像有點(diǎn)兒印象。”我完全不記得我說過這些,“那真是喝多了,哎呀,真是很難堪呀。”我笑著掩飾尷尬。
“那你今天可以好好挑件給林老師的禮物了。大廳過去是石雕展,穿過展覽廳,出口處是家大型商場,主要賣石雕,也有不少貨真價(jià)實(shí)的原石。”于萬陽湊到我耳邊,“付款的時(shí)候就說是我朋友,有折扣的。”
“哎哎,”Stella走到我身邊,“你快去看,那邊有座石雕可有意思啦。”
“那你們?nèi)ネ鎯喊桑庇谌f陽向我和Stella點(diǎn)點(diǎn)頭,“我馬上也有點(diǎn)兒事,常聯(lián)系。”
Stella拉著我來到展廳西北角的一座石雕前,“看,像不像你?”
“少女與貓”,作品標(biāo)簽上寫著。
女孩兒穿著厚厚的棉衣,坐在一把藤椅上,她的膝蓋上臥著一只貓。女孩兒撫摸著貓的腦袋,眼睛瞇縫著,像是在享受冬日正午的陽光。作品纖細(xì)入微,女孩兒面部線條清晰利落,從貓毛到藤椅的紋理極具寫實(shí)。看著看著,竟也有些昏昏欲睡,這大約就是藝術(shù)的魅力。
“少女與貓”的旁邊,是一座“洗衣服的老人”石雕。老人的面部、手部皺紋縱橫,但從洗衣的動(dòng)作中,穿透出原始的力度。給人以現(xiàn)實(shí)的存在感。
再走過去,是一組群雕。作品標(biāo)簽上寫著,“開采石料的工人”。他們運(yùn)用各種原始的工具,或挖或鏟或抬或挑,腿腳穩(wěn)健,面無表情。在一群工人當(dāng)中,我一眼看見了那個(gè)發(fā)髻線后退,頭發(fā)稀疏的男人。
“林老師……林老師……林老師……”
我睜開眼睛,四周已經(jīng)完全黑了下來。我不知道我被綁在這里多久,身體完全麻木。膝蓋上的貓不知道什么時(shí)候掙脫捆綁,不見了蹤影。手腕上被貓咬噬的傷口還在隱隱作痛。我看見林老師跪在我身邊,試圖解開捆綁我的藤條。
“林老師,”我無力地說,我冷得連嘴巴都僵硬了,“我們離開這兒吧,這兒不對勁。”
“怎么解不開啊。”林老師緊皺著眉頭,指甲摳進(jìn)藤條系成的疙瘩里。“你等著,我去找找有什么工具。”很快,林老師在展覽館的屋檐下找到一片薄薄的石片。他又跪到我身邊,用石片一點(diǎn)點(diǎn)地割斷藤條。
“我知道這里不對勁,”林老師說,“從參觀展覽館開始我就知道了。這里存在有花崗巖,石灰石,砂巖和滑石等等,它們是不同的巖石類型,沉積巖,變質(zhì)巖、火山巖。你明白嗎?這些類型的石頭不可能同時(shí)出現(xiàn)在同一個(gè)地方,但這里都有。”林老師停下手里的動(dòng)作,抬頭看看我,“所以,這里不是一個(gè)現(xiàn)實(shí)的地方。”
“我不明白。”
“盡管這樣,”林老師加快了手里割藤條的動(dòng)作,眼睛死死盯住快速移動(dòng)的石片,“我卻喜歡這里,我不打算離開。”
“為什么?”我覺得自己就要哭出來。
“我對你有強(qiáng)烈的欲望,愛欲、性欲,從你還是個(gè)小孩子的時(shí)候開始。我厭惡我這樣的情感,特別是在現(xiàn)實(shí)的世界里。這里簡單很多,人成為單一的工具,執(zhí)行固定的單純的命令。這大概就是我理想的生活吧,可以在筋疲力盡后忘記思想,并且這不是一個(gè)短期的狀態(tài),它可以持續(xù)百年、千年,直到風(fēng)化的那一天。”
藤條噠地割斷了。“好了,我知道你想離開,你還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有很多的事情要想,這里束縛不住你的。”
我緩緩站起身,身體就像被塵封千年一樣僵化。“我想陪你。”我說。
“我知道你說的是實(shí)話,但只是現(xiàn)在,你應(yīng)該生活在你的世界,那里色彩繽紛,而不是這樣的灰暗和陰冷。”
林老師說得是對的,我舍棄不了他給我的溫存,但更舍棄不了我熟悉的生活。“可是,我該怎么離開?”
“再過一會(huì),采石的工人們就要到了,我已經(jīng)是他們中的一員。你悄悄尾隨我們走到采石場,我們干活的時(shí)候你躲起來。等到運(yùn)載石料的卡車隊(duì)過來后,你找準(zhǔn)機(jī)會(huì)溜上卡車,和石料一起運(yùn)下山。據(jù)我觀察,這是唯一通向現(xiàn)實(shí)的出路,除此以外再?zèng)]有別的途徑可以出去。”
工人們的身影已經(jīng)像無數(shù)黑點(diǎn)一樣從遠(yuǎn)處出現(xiàn),密密麻麻向這里匯集。步伐穩(wěn)健,面無表情。
“記住,”林老師說,“上了卡車后,千萬不要睡著。如果睡著了,永遠(yuǎn)也不能出去。一定要保持清醒,千萬不要睡著,不要睡,知道嗎?不要睡。”
“不要睡,不要睡啊。”
我痛苦地睜開眼睛,看見一位身穿白大褂的年輕女人,在我身邊不停地對我說,“不要睡啊,不要睡。”
身體動(dòng)彈不得,我轉(zhuǎn)動(dòng)眼珠,發(fā)現(xiàn)自己在一輛運(yùn)行著的救護(hù)車上。年輕女人對著一個(gè)在做記錄的護(hù)士說,“心跳逐步復(fù)蘇,血壓110,心跳52,估計(jì)自殺時(shí)間為凌晨四點(diǎn)三十分。”
我疲憊不堪,左手手腕上的傷口被包裹著厚厚的紗布,汩汩流淌的血液大概已經(jīng)凝固了吧,藤椅上的暗紅色血塊被林老師擦掉了嗎?真的很困很困。
“媽媽,媽媽,你醒醒呀。”女兒脆嫩地嚷嚷著把我搖醒。“你怎么就睡著了呢?我還醒著呢。”
我合上繪本,關(guān)上床頭的小臺(tái)燈,“好了,你乖乖地睡覺吧。”
“媽媽,”女兒小聲地問,“媽媽,爸爸到底長什么樣子?”
“嗯……”我不知道該如何回答,想了想說,“人類最了不起的財(cái)富就是擁有無窮無盡的想像力,你可以自己想像爸爸的樣子呀。爸爸的年齡也許比媽媽大很多很多,也許和媽媽差不多大。爸爸的頭發(fā)也許又少又稀松,也許非常濃密。”
“媽媽,你不陪我啦?”
“對啊,媽媽還有工作要做,今晚要寫完一份長長的報(bào)告。很難寫的。”
“媽媽你會(huì)不會(huì)寫著寫著又睡著了?”
“會(huì)啊,因?yàn)閶寢屖撬廊恕!蔽倚χ鴰吓畠悍块g的門,走向書房。
電腦旁的臺(tái)燈發(fā)出柔和的米黃色光線,讓人昏昏欲睡。
“不要睡著,不要睡著。”卡車規(guī)律的顛簸使我的眼皮愈發(fā)沉重。我裹緊身上灰色的棉衣,身邊的巨型石料冰冷潮濕,呼呼的大風(fēng)直撲在我身上。
我不能睡著,我堅(jiān)定地把眼睛睜到最大,看見東邊有太陽的光暈從山坳處露出,是溫暖的桔色,而不再是慘淡的白光。
我撫摸微微凸起的小腹,有一個(gè)熱乎乎的小生命在我冰冷的身體里跳動(dò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