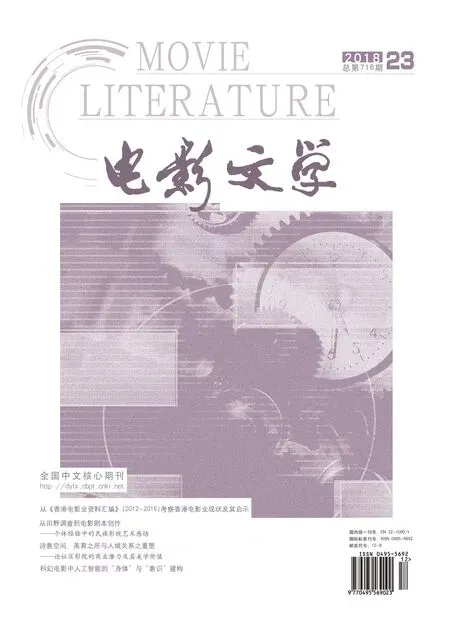十七年時期喜劇題材電影的樣式探索
楊金鳳
(東北師范大學 傳媒科學學院,吉林 長春 130000)
以1949年為界,以“題材”而非“類型”來組織劃分和生產電影成為中國電影的新現象。國家意識形態凌駕于電影創作之上,領導者嘗試通過一種潛移默化的方式來宣傳鞏固政權。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電影作為大眾喜聞樂見的文化形式成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的工具。十七年時期喜劇題材電影的“笑”隨著國家文藝政策和當局的意識形態發生變化,在政治與藝術的夾縫中艱難前行。
一、喜劇題材電影的蟄伏期
《電影政策獻議》中電影人構想的新中國電影要延續新中國成立前的公司化模式,以娛樂和營利為目的。然而,新中國亟待建立起新的政治和文化環境來鞏固新生政權,領導者對于電影有著一套政治化的管理和運營模式。電影要為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體制上照搬僵化的蘇聯模式,其生產、發行和放映在國家的統一管理下具有高度集中化、政治化、一體化的特點。國家壟斷型的電影體制使電影失去了它原本自由的發展空間,電影的娛樂性、藝術性和商業性也被取締。
復雜的現狀和隨之而來《武訓傳》的批判以及各項整風運動的開展,迫使十七年喜劇題材電影進入長達七年的蟄伏期。1949—1955七年中,沒有出現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喜劇題材電影,“從心理層面講,殘酷的現實與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使廣大的電影創作者不自覺地選擇了拒絕喜劇創作的‘集體無意識’”。雖然喜劇題材電影未能出現,但也未能抑制藝術家的創作熱情,一些私營電影制片廠的影片如《我這一輩子》(1950)、《關連長》(1951)、《我們夫妻之間》(1951),東影廠《葡萄熟了的時候》(1951)、《結婚》(1953)、北影廠《趙小蘭》(1953)等都融入一些輕松愉快的喜劇元素。盡管創作者如此謹小慎微,以《關連長》為代表的喜劇元素電影依然受到了批判,影片中塑造的關連長性格飽滿、詼諧幽默、平易近人,演員表演也盡可能采用夸張放大的肢體動作來營造喜感。但這不符合當時陳波兒提出的以“陽剛之美”塑造近乎完美的銀幕英雄形象要求,《關連長》沒有將主要人物表現得高大挺拔,缺乏所謂的英雄氣概,因此《人民日報》曾批判它“把人民解放軍描寫得粗魯彪悍沒有文化教養,完全沒有抓住解放軍的‘本質’和‘戰略思想’,嚴重歪曲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形象”。喜劇題材電影的創作舉步維艱,藝術家們選擇拒絕喜劇的“無意識”,喜劇電影處于漫長的蟄伏期。
然而,電影始終是一種藝術,不能局限于政治教化和意識形態宣傳。“建國初期,電影的政治宣傳與教育功能被過分擴大化,審美和娛樂功能更是被忽略以至于無人考慮。從1949—1953年所出作品幾乎全是正經八百的正劇影片,使人感到單調。”電影長期以來只是通過說教性的場面赤裸裸地宣傳意識形態,其效果并不盡如人意,日益單調的電影創作使觀眾喪失觀影興趣。
二、喜劇題材電影的破冰之旅
直到1956年“雙百方針”的提出才讓喜劇題材電影的創作有了喘息之機,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促使藝術家們有了新的思考和探索。陳荒煤曾在雙百方針后發文:“藝術創作需要遵循一些普遍規律,然而我們都忘了甚至完全忽略了藝術的特征。無所謂正劇,無所謂悲劇,也缺乏喜劇。”有了相對寬松的文藝政策和電影專家適時的鼓勵,藝術家創作熱情高漲,對于電影新題材摩拳擦掌,喜劇題材電影應運而生。據統計整個十七年時期的喜劇題材電影約有30多部,根據相關史料和文獻我們不難看出這一時期關于喜劇題材電影樣式的探索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個階段:諷刺喜劇(1956—1958)、歌頌型喜劇(1959—1961)、生活輕喜劇(1962—1965)。
(一)喜劇題材電影樣式的階段之一——諷刺喜劇初探
1956年到1958年是喜劇題材電影創作的第一個春天,我們將這一階段的喜劇電影稱為“諷刺喜劇”。諷刺喜劇作為第一個探索的樣式出現并非偶然,在中國電影史上,帶有“諷刺”意味的喜劇電影傳統由來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紀20年代的“滑稽戲”,三四十年代又出現了以《太太萬歲》《烏鴉與麻雀》《假鳳虛凰》《三毛流浪記》為代表的喜劇電影。
同樣是諷刺喜劇,這一時期的諷刺喜劇與《烏鴉與麻雀》《假鳳虛凰》的諷刺力度相比已減弱不少,之前多諷刺黑暗腐朽的社會制度帶給人的苦難,甚至直接抨擊當局統治者。十七年時期的諷刺喜劇電影多是對現實社會丑惡現象的揭露,“諷刺社會風習,僅限于道德范疇而非制度上的懷疑,其目的主要為導向教化型”。《新局長到來之前》諷刺的是一種溜須拍馬、損公肥私的官僚主義作風;《不拘小節的人》表現的是個人違反公共道德卻不自知的現象;《如此多情》中諷刺婚姻愛情里見異思遷“攀高枝”的不良風氣。電影人通過弱化諷刺來尋求喜劇題材電影創作的可能性,但內心依然戰戰兢兢生怕出現政治上的錯誤,呂班曾這樣描述:“怕弄不好,怕弄巧成拙,怕弄得‘低級’了,怕諷刺不準確,尺寸掌握不對,輕重拿捏不當,怕歪曲了現實,怕把諷刺變為污蔑,怕……”就在這種前怕狼,后怕虎的情況下,1956年后依然涌現出一批優秀的諷刺喜劇電影如《新局長到來之前》(1956)、《不拘小節的人》(1956)、《如此多情》(1956)、《沒有完成的喜劇》(1957)。不幸的是,呂班導演一語成讖,《沒有完成的喜劇》還沒有上映就被批判為反黨反人民的“大毒草”,呂班也結束了自己的藝術生涯被打成右派。隨后《球場風波》(1957)、《尋愛記》(1957)、《誰是被拋棄的人》(1957)等也全部受到批判,1958年的“拔白旗”運動也將《花好月圓》從銀幕上拔掉。諷刺喜劇剛興起不久就被扼殺,喜劇電影人都“談笑色變,望喜生畏”。
(二)喜劇題材電影樣式的階段之二——歌頌型喜劇的轉變
歷經了諷刺喜劇的批判和“拔白旗”等運動后喜劇題材電影的創作陷入僵局,直到1959年國慶十周年獻禮之際,電影界都缺少喜劇電影作品。喜劇題材電影要想突破重圍就必須轉型,在夏衍的指導下歌頌型喜劇讓人眼前一亮,以《今天我休息》(1959)和《五朵金花》(1959)為代表的新喜劇樣式廣受好評,引起高度關注。此時喜劇電影由傳統喜劇以“諷刺”來表現電影主題的舊模式轉變為以歌頌新社會、歌頌新人物為特征的“社會主義喜劇”。
歌頌型喜劇的新模式主要有以下特點:情節設置上消解了二元對立,沒有明顯的對立情節;基調上歌頌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和欣欣向榮的時代風貌,展現沐浴在新中國陽光下的美好生活;創作手法上不再采用“諷刺”手法,笑的制造主要依靠“巧合”和“誤會”,詼諧、幽默、風趣成為基本手法;主題上主要表現人民內部矛盾,沒有大的沖突。主角都是積極陽光正面向上的人物形象,通過正面人物身上種種令人發笑的性格來表現新時代人們的崇高思想和奉獻精神。“笑”的發生元素主要依靠的是“誤會”和“巧合”,通過“笑”營造出一個朝氣蓬勃、充滿干勁的社會主義新社會,讓其正面積極地引導和寓教于樂的教化功能在電影中發揮到極致。“巧合”和“誤會”成為營造情景、推動故事發展的動力。這樣的喜劇題材電影獲得了觀眾和專家的廣泛認同,這一模式成為十七年歌頌型喜劇的范本。歌頌型喜劇一改諷刺喜劇的尖銳,少了對現實的針鋒相對、深刻批判,多了一分溫和的贊揚和對現實的粉飾。
(三)喜劇題材電影樣式的階段之三——生活輕喜劇的嶄新走向
本來以為歌頌型喜劇是一種有別于傳統喜劇的革命“新物種”,新中國喜劇終于找到了一條直通羅馬的康莊大道,可以大有作為。然而現實卻是歌頌型喜劇的創作和發展并不如藝術家們想象中的順利和多產,三年自然災害以及與蘇聯決裂產生的一系列問題加上黨的八屆十中全會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導致電影界和文藝界風向大變,1962年陳毅在座談會上重新闡述知識分子政策,摘掉知識分子“資產階級”的帽子,藝術家們才恢復積極性。
此時他們也意識到如果一味地歌頌現實生活而缺乏生活的真實血肉必然會遭到觀眾的厭惡。這一點從亞里士多德對喜劇的理解也可以看出——喜劇是模仿低劣和丑陋。一味地“歌頌”不能構成喜劇電影需要的沖突和矛盾,而“諷刺”雖然是喜劇的靈魂之一,卻不能被完全認可。如果將“諷刺”和“歌頌”相雜糅,形成以“歌頌為主,諷刺為輔”的喜劇創作模式,不失為一種兩全其美的辦法,由此開始了更加貼近人民群眾的生活輕喜劇探索。這里諷刺的對象也由原來的不良社會現象轉變為更為溫和的對于落后觀念的批判,展現的主要矛盾不再是社會矛盾而是人民內部矛盾,就此開辟了一條生活輕喜劇的發展道路,迎來了十七年喜劇題材電影創作的第三個“小高潮”。1962—1965年出現了許多膾炙人口的喜劇電影,如《錦上添花》(1962)、《李雙雙》(1962)、《魔術師的奇遇》(1962)、《女理發師》(1962)、《大李老李和小李》(1962)、《滿意不滿意》(1963)、《抓壯丁》(1963)、《山村會計》(1965)、《龍馬精神》(1965)等,1965年后伴隨著政治形式的緊張鮮有喜劇作品面世。
與歌頌型喜劇不同,生活輕喜劇承認矛盾和斗爭的存在,在社會主義社會這樣正面的大環境下,依然存在一些消極部分,電影面向偉大時代的各個生活角落以生活化的視角來表現人物,圍繞人與人之間的小摩擦小矛盾、生活和工作中態度的個體差異、夫妻之間相處以及同志之間的人情世故等,概括說就是“有矛盾而不必尖銳;有沖突而不必激烈;有諷刺而不必辛辣;有歌頌而不必過高”,結局無一例外是家庭團圓、夫妻和睦、破私立公、改邪歸正等避重就輕的策略,矛盾嚴格限制在“人民內部矛盾”范圍內,遵循了喜劇審美的本質特征:寓嚴肅于嬉笑的人生批評。
三、結 語
(一)國家意識形態對文藝創作的影響
十七年時期意識形態始終左右著喜劇題材電影的發展,電影題材的多樣化并沒有改變它的政治屬性,喜劇題材電影只是換一種方式來完成意識形態的“詢喚”。喜劇樣式無論怎樣改變都必須貼上意識形態的標簽,保證政治的正確性。影片必須滿足意識形態的要求,意識形態猶如一條無形的枷鎖緊緊圍繞喜劇題材電影的創作,新中國的電影人試圖在電影的本體特性與意識形態話語之間尋求平衡點。
(二)喜劇電影的健康發展必須立足現實
十七年喜劇題材電影的樣式探索有著沐浴時代風雨的啟蒙色彩,藝術創作在任何一個時代都不是孤立的,喜劇電影要想尋求一個健康穩定的發展環境就必須適應當時的歷史文化、經濟政治,創作出既能符合主流又符合大眾審美,能夠表現當下社會現象的作品。
(三)喜劇電影需要培養自己的文化品格
喜劇本質上需要一種對人生世事的洞察心境,它不應僅僅是博人一笑,而是讓觀眾笑過之后有所思考,喜劇要具有自己的文化品格,要真正上升為現代人的生存智慧。伴隨著社會的發展與深入,喜劇須向歷史與現實的縱深處挖掘,深化內容、創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