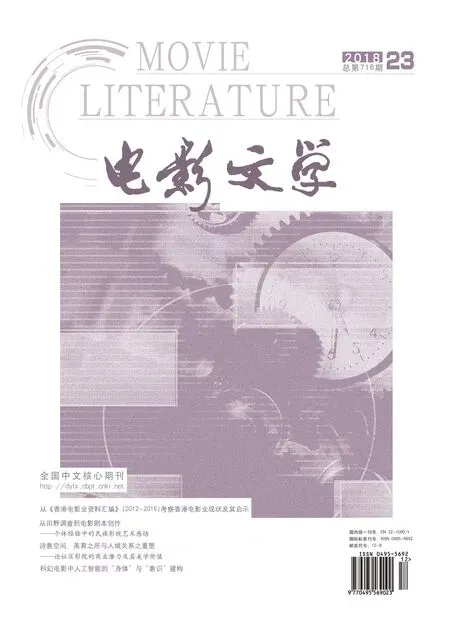阿彼察邦電影中的間離研究
張 良
(北京電影學院,北京 100088)
“間離效果”又稱“ 陌生化效果”,德文為VE RFREM-DUNG-SEFFEKT ,德文里原沒有這一詞匯,是20世紀德國戲劇大師布萊希特自己創立的理論術語。用布萊希特的話來說:“所謂間離效果,簡言之,就是一種使所要表現的人與人之間的事物帶有觸目驚心的、引人尋求解釋,不是想當然的和不是簡單自然的特點,這種效果的目的是使觀眾能夠從社會角度做出正確的批判。”
一、模糊的間離
阿彼察邦電影中的間離,雖然作用上也是使得觀眾與影片中的角色產生了距離,但其精神內涵卻與布萊希特的間離大相徑庭。在阿彼察邦看來,電影不應該是教育、批判或者表達思想的工具,正如他在一次采訪中談到他的一個裝置藝術作品時所說的:“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政治性過于明顯了,但在一開始這個作品是非常抽象的。我認為如果一個人想非常直接地講一個故事(觀點),那最好是寫本書,而不是做電影。”
所以,阿彼察邦的這種間離,不可能是布萊希特式的。雖然阿彼察邦的電影也摒棄了戲劇性,不會讓觀眾“陷入”情節之中,在這一點上與布萊希特所推崇的戲劇的間離效果是相似的,但阿彼察邦仍然堅持一種東方的、現象學的美學觀點,他的電影中的間離不會是純理性的,更不會是說教的或者表達思想的,而是一種模糊的、不可理解的甚至非理性的間離。間離并不必然代表某種含義的明確,這似乎是很多藝術電影的共同特點,阿彼察邦的電影尤其如此。
比如《祝福》(Blissfully
Yours
)的最后一個鏡頭:這個鏡頭是固定機位俯拍,特寫,長度只有三秒,Roong躺著轉身直視鏡頭。雖然只有三秒,但是這個直視鏡頭的動作所制造的間離感卻是非常強烈的。在習慣了前一個長鏡頭中Roong蒙眬的睡眼以及半夢半醒之間的慵懶氛圍之后,觀眾突然看到Roong轉身、睜開眼睛、冷峻地直視鏡頭,令人非常意外,前后鏡頭對比如此之強烈,其產生的間離感也被非同尋常地加強了。我們知道在商業片中,常常要通過給觀眾“造夢”,讓觀眾“進入”故事中,從而實現“縫合”。“縫合”是拉康提出的一個概念,后來被讓·皮埃爾·歐達爾運用在電影分析中,認為“縫合”功能使得觀眾不再懷疑電影的真實性,從而使“敘事的安全”得以保證。而在這個鏡頭中,導演有意識地打破了“縫合”,讓觀眾脫離敘事,有的人也許會問,這個鏡頭究竟想表達什么含義呢?
遺憾的是,這個鏡頭沒有對話、沒有旁白,動作也很簡單,不能帶給我們任何提示,甚至在前后鏡頭中我們也找不到什么隱藏的線索。當然我們可以有各種猜測,比如認為Roong這徹底清醒的一瞥點出了本片的主題,比如表現了現代社會帶給人的矛盾和分裂,比如在叢林里雖然可以短暫逃避和放松,但終究還是要回到城市面對現實的……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甚至這些理解可能是大相徑庭的。但筆者認為糾結于這些含義是沒有意義的,我們恰恰要跳出這種非要找到某種含義甚至是“標準答案”的思維,才能真正理解阿彼察邦的電影美學。
在阿彼察邦的電影思維中,電影是感性的、充滿夢幻的,而不是用于直接表達思想或者觀點的工具,甚至他多次將電影比喻為一種“冥想”:“如果文字能表達這些情感的話,我會毫不猶豫用文字來表達。但(文字并不能)我只能用電影這種對我而言類似于冥想的藝術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感覺。”
也就是說,在阿彼察邦的電影中,間離并不必然與某種含義上的明確化相關。筆者認為在這個鏡頭中,阿彼察邦本就沒有試圖給觀眾一個確切的含義。非戲劇性是阿彼察邦所有電影的共同特點,所以采取這種意義模糊但又強烈的間離方式,首先是合乎阿彼察邦電影的整體風格的;其次,這種模糊的、似懂非懂的“迷之狀態”給阿彼察邦的電影帶來了一種“余味”。這種“點到為止”“留下余味”難道不正是我們常說的控制的、間接的美學的體現嗎?為了區別于一般的、表達思想的、布萊希特式的間離,我們不妨把這種間離稱為“模糊的間離”。
二、“心靈的逼近”
阿彼察邦電影中的直視鏡頭,還有一種“心靈的逼近”的作用。“心靈的逼近”源于蘇牧教授在《榮譽》中對特寫鏡頭的作用的闡述,蘇牧教授所說的“逼近”的對象是劇中人物,而本文這里所說的“逼近”的對象是觀眾。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不妨看看阿彼察邦電影中的另外兩個直視鏡頭的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綜合征與一百年》(Syndromes
and
a
Century
)中直視鏡頭的部分(72分35秒到79分18秒):(一)敘事元素
1.替代
與鄉村醫院相比,這里日光燈替代了陽光,喝酒替代了音樂。陽光是自然的、溫暖的,音樂讓人心情愉悅,而且讓人與人接近;日光燈也能帶來能量,但卻是冰冷的,喝酒也能讓人放松,但只是一種短暫的麻醉而已。醫生把酒瓶藏在假肢里,也隱喻了喝酒并不是健康的放松方式。
2.雜亂
房間像是臨時的、沒裝修完成的,墻角隨意堆放著假肢,旁邊桌子上厚厚的灰塵,以及臟亂的水泥地。這種環境處處給人一種不安定、不踏實的感覺,有一種頹廢的氣氛,似乎這里并不是久留之地。
3.冥想治療法
醫生給患者治療時,讓他冥想“太陽”“叢林”“瀑布”等,但事實上患者卻坐在這樣一個冰冷、雜亂的地下室里,這無疑是一種巨大的諷刺。對比鄉村醫院也就是本片前半部分的自然景色,就更加強化了諷刺的感覺。這種冥想治療當然不會有效果,患者自己也說“什么都沒感覺到”。而作為敘事元素,這段冥想其實不僅是治療,而是表達了城市人夢想的生活方式,但他們卻離這種生活越來越遠。
(二)視聽方案
這是一個長達近七分鐘的長鏡頭,更重要的是,鏡頭在此期間有一個推和拉。
1.色調
白色日光燈、白色墻壁、衣服顏色、桌椅和地面都是冷色,整體上給人一種冰冷和蒼白無力的感覺。這對應了本片的主題,即現代城市醫院雖然面積大、設施先進,但是人情味卻不比從前的鄉村醫院,在這里的人無論醫生還是患者精神上都很壓抑,生活不豐富,而且感覺很空虛,這種感覺像是一種病在他們之間相互傳染。
2.推鏡頭
推鏡頭是從第74分54秒到75分30秒,啟動時借助了醫生的走動作為調度,而且推鏡頭很緩慢,可見導演想盡量使觀眾不要注意到這個鏡頭運動,只是讓景別從中景推到近景,讓觀眾看主要人物和聽他們的對話,事實上本段落里醫生們也一直在對話。
3.拉鏡頭
拉鏡頭是從77分05秒到78分02秒,啟動時很明顯地向左橫搖,然后拉鏡頭,最后再向右微微橫搖,復位到最開始的鏡頭位置,構圖也恢復到和本段落一開始時一樣。相比推鏡頭,這個拉鏡頭首先是啟動得很突兀,其次是鏡頭中的所有人物都在原地沒有運動,所以鏡頭運動就顯得更加明顯。最后,隨著鏡頭的搖和拉,更多的人物進入了景框。導演這樣做無疑是想讓觀眾感覺到鏡頭的運動,從而讓觀眾從敘事中“跳出來”,意識到鏡頭的存在,也意識到自己在看電影。
另外在這個拉鏡頭的過程中,當鏡頭向左搖,左邊的醫生出現時,我們會驚訝地發現,她竟然是直視鏡頭的。而且,從鏡頭搖到她臉上到她轉頭,長達50秒的時間里,她就這樣長時間地盯著鏡頭一言不發!配合拉鏡頭,這種間離感在視聽和表演兩個方面被發揮到了極致,多么震撼啊!
第二個例子是在《熱帶疾病》(Tropical
Malady
)中,當“森林小隊”和叢林邊的一家人吃過晚餐后,Keng獨自坐在院子里的涼棚下,從這時開始Keng有多次直視鏡頭,其間片名和字幕出現(從8分45秒到10分08秒)。(一)敘事元素:展現動物性和欲望
在夜里的叢林邊、一個人、凝視而不說話、吃手指,這些元素都表現出某種程度的動物性;而多次略含笑意、充滿感情地看鏡頭,則表現出了一種愛的欲望。這種對于動物性和欲望的展現表現了本片的主題:人也是動物,叢林使我們看清自己內心的欲望。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緊接著這個鏡頭之后,有一段在公交車上Tong和對面坐著的陌生女孩頻繁對視的鏡頭,再次表現出了“動物性”和“欲望”,也很明顯是對這個鏡頭的呼應。
(二)視聽方案:直視和間離
這是一個近一分半鐘的長鏡頭,在這個鏡頭中,演員多次直視鏡頭。另一方面,在這個鏡頭中,開始出現片名和字幕,阿彼察邦自稱這個鏡頭“啟動”了整個電影。筆者認為這種方式還打破了觀眾的敘事期待,讓觀眾感覺到這將不會是一部普通的商業片式的講故事的電影。
上述兩個例子中,都是劇中人物直視鏡頭,除了震撼之外,如果我們細加體味,就會感到這些鏡頭還讓劇中人跳出了電影情節,突然變成了一個具有理性頭腦的、正在思考的人!他/她不再是被動地被觀看,而是產生了一種似乎與觀眾處在一個空間的平等的感覺,通過眼神接觸開始與觀眾形成“溝通”。這時候,觀眾會感到跳出情節的電影中的那個人物,也在觀看和思考觀眾所看到的影像,觀眾會問:他/她會怎么想這些影像?也就是說,電影中的人物成為又一個觀看和思考的主體,成了觀看著的、思考著的第三人。觀眾所想弄清的不再是情節本身,而是又多了一個劇中人對劇情的想法,這種新想法就是這些鏡頭產生的新東西,我們不妨稱之為“對思考者的思考”。
這個概念可以與女性主義電影理論中的雙重觀看相類比。按照勞拉·穆爾維的觀點,在女性主義電影理論中,認為女性作為被觀看的對象,既被電影中的人物觀看,也同時被電影觀眾觀看。而這兩種觀看的矛盾使“敘事空間的統一”受到“威脅”:(作為結束)的開始,窺淫——觀看癖的目光是傳統的電影快感的關鍵部位,它本身也可以被打破。有三種不同的看的方式與電影有關:攝影機記錄具有電影性的事件的看,觀眾觀看完成作品時的看,以及人物在銀幕幻覺內相互之間的看。敘事電影的成規否認前兩種,使它們從屬于第三種,其有意識的目的始終是消除那攝影機的闖入,并防止觀眾產生間離的意識……然而,正如本文所論爭的,在敘事性虛構影片中看的結構在它的前提中包含一種矛盾:作為閹割威脅的女性形象不斷威脅敘事空間的統一,并且作為干擾的、靜態的、一維的戀物而闖入那幻覺的世界。
由此可見,在以上所舉的阿彼察邦電影的兩個例子中,電影中人物的思考,也同時被電影觀眾所思考,這種矛盾同樣會使阿彼察邦的電影敘事空間無法統一,所以具有很強的間離效果。
而進一步,筆者認為,“對思考者的思考”還會給觀眾帶來一種壓力,因為你感覺到劇中人跟你看一樣的東西而若有所思卻沒有說出來。這種“迷之思考”,加上他/她直視你的“心靈的逼近”,無疑會帶給觀眾一種潛在的壓力甚至惶恐,就像學生在課堂上突然發現老師盯著你看一樣,在這一瞬間,你感到電影似乎對你有所期待,或者說電影突然高高在上,你被俯視了……
瑪麗·安·多恩認為,在電影中“男人很少去勾引那些戴眼鏡的女孩”,戴眼鏡的女人同時意味著理智性和不可欲求性,因為在影片中,女性所戴的眼鏡并不總是意味著觀看的缺陷,而是一種積極的觀看,甚至只是對抗被看的觀看行為本身。知識女性觀看和分析,以侵占凝視的方式,向一個完備的表征系統發出了一種威脅……琳達·威廉姆斯解釋了在恐怖電影類型中,女性的積極觀看最終如何受到懲罰……
在阿彼察邦的電影中,劇中人物對觀眾的“觀看”,也同樣可以視為一種積極的、對抗性的觀看,而不同的是,劇中人物并不會像恐怖電影中積極觀看的女性那樣受到“懲罰”,只是更加引起觀眾的關注和重視,某種程度上讓他/她成為一個“先知”。但是,同樣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電影中的人物是為了表達某種思想或者觀點,含義外露、意義過于明顯,那觀眾就會感到被冒犯了,甚至被當作學生“教育”了,這時候電影就會受到“雙重懲罰”:首先劇中人物會失去觀眾的認同;其次,即便觀眾不感到被冒犯,也至少會感到過于直白,電影本身的藝術水準因此會遭到質疑。有些不成熟的創作者為了強調自己的觀點也許會這樣做,觀點是表達清楚了,卻因為“雙重懲罰”而得不償失。所以,正如阿彼察邦的做法,模糊化才是最好的處理——觀眾既不會覺得被冒犯,同時又感到了某種“心靈的逼近”。
前文曾經提到過,即便是模糊不定的非“標準答案”,我們仍然可以對這些鏡頭給予某種解讀。比如上文提到的《綜合征與一百年》的那個鏡頭,筆者認為含義有兩個:
1.全球化問題
通過鄉村醫院和城市醫院的對比,導演想表達的是鄉村和自然給人帶來的幸福感,以及城市化、現代化甚至全球化帶來的人精神上的問題。
2.電影作為諷刺的工具
當一位醫生正通過冥想療法讓病人想象“陽光”“叢林”和“瀑布”時,另一位醫生卻直視鏡頭,這樣,不但那些美好的想象被打破了,甚至連這種治療也變得很滑稽。我們會質疑這種對自然的空想意義何在,也會為人類的這種處境而感到悲哀。在這里,電影本身不再是敘事工具或者造夢工具,而是表達諷刺的工具,是導演觀念的載體。
而上文提到的《熱帶疾病》中的那個鏡頭,阿彼察邦則在一次采訪中做過解釋:“這部電影是關于凝視的。當你被一個人吸引,你就像老虎一樣盯著他/她,催眠、壓倒他/她。當字幕出來時,Keng看著鏡頭,就像是一種歡迎的姿態,間離,讓觀眾認識到這就是電影,不是現實,這個凝視啟動了整個電影。”他還說:“那個鏡頭拍了十遍……我問他:‘你能像老虎一樣對著攝像機調情嗎?’這確實有點難!”
三、結 語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阿彼察邦非但不拒絕,甚至是歡迎觀眾跳出情節對他的電影進行思考的,只是他自己不希望解釋過多。在一次訪談中,關于《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中的巖洞是否“柏拉圖式的洞穴”,阿彼察邦說:“是的。但我得停下來了,我解釋越多,電影本身的神秘性就越少了!”
筆者不由得聯想到電影大師小津安二郎有一句名言:“人生和電影都是以余味定輸贏的。”阿彼察邦電影中的間離,受到他的電影思維和藝術風格的影響,具有獨特的藝術特征和藝術效果。比起直接表達思想的、布萊希特式的間離,阿彼察邦電影中的間離顯然更能散發出小津所說的那種“余味”,它體現了阿彼察邦對電影藝術的深層次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