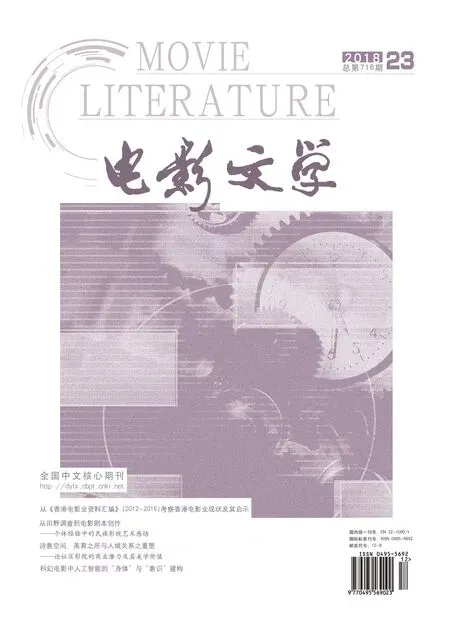變異與新生
——《影》的俠文化探微
杜 遠
(長春光華學(xué)院,吉林 長春 130033)
俠客一直是我國民間所特有的人物塑造范式,也是理想人格在我國文化當中一個比較具有代表性的展示,在漫長的文學(xué)作品塑造的歷史中,俠的多樣的表現(xiàn)方式和心理狀態(tài),被逐漸塑造為了一種文化群像,俠本身的形象意義也逐漸帶有了中國文化的色彩,成為一種獨特的民族文化。如果必須要給俠或者由俠所代表的文化傳統(tǒng)做一個定義,那么其中包含的多元化文化內(nèi)涵勢必要被或多或少的遮蔽,在這個復(fù)雜的文化系統(tǒng)面前,我們無意于詳細地界定什么是俠,或者什么是俠文化,僅僅在此從一個籠統(tǒng)的角度描述這個中國典型文化范式,并且將這個簡單的分析結(jié)合新近的電影文本《影》進行討論。
在張藝謀的《影》這部電影文本中,俠的精神包括傳統(tǒng)意義上的俠客精神,都督子虞所招攬的影武士,應(yīng)當屬于傳統(tǒng)意義上的門客,在不少古代文獻中,俠的起源正是這些義無反顧投身于政治活動、為主盡忠的門客身上。盡忠這個行為是最早成為俠客身上的特質(zhì)的。隨著歷史階段的不斷發(fā)展,俠的內(nèi)涵也在不斷地補充著,在隋唐時期,俠已經(jīng)明顯地從為主盡忠的俠客,變成了為國紓難、為民申冤的任俠,這種俠客大多是自發(fā)的行為,帶有濃重的傳奇色彩,仿佛是連同他們所身在的社會也具有一種獨特的社會邏輯關(guān)系,從這種描述的特殊性上看,任俠更多的是來自于文人的想象與標榜,是烏托邦社會設(shè)想中的一種烏托邦形象。任俠一般沒有歸屬關(guān)系,按照自我的善惡標準從是社會行為,在古代的歷史典籍中記載的不多,但是在文學(xué)作品中卻是數(shù)見不鮮,這些俠客身上有著明顯的特定塑造方式,在文學(xué)文本和這種文化潮流的興盛中,往往具有理想人格的成長和影響。
如果將俠和俠文化本身,看作是一個不穩(wěn)定的、需要被時刻補充的一個文化觀念集合,那么任俠這個文化現(xiàn)象就是歷史發(fā)展過程當中下文化的一個最核心的代表,這種現(xiàn)象具有俠文化的特質(zhì),同時也具有任俠文化本身的文化特性。從這個角度來看,張藝謀導(dǎo)演的作品《影》,是當代文本創(chuàng)作過程中從任俠的角度對俠文化的內(nèi)涵又一次補充和建構(gòu)的過程。
一、傳統(tǒng)“任俠”與《影》中的人物
任下的傳統(tǒng)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漢時期,這個時期政治局勢比較動蕩,社會的晉升秩序被打破,許多普通的社會底層民眾渴望獲得更多的社會權(quán)利,打破既有的利益分配關(guān)系,因此出現(xiàn)了一些具有較高文化水平和體力水平都社會群眾代表,這些人有的參與到政治關(guān)系的更迭當中,為政治斗爭的雙方其中的一方進行服務(wù)從而實現(xiàn)個人的理想和價值,另一些人則生活在民間為普通百姓的權(quán)利進行奔走和斗爭,后者逐漸成為了普通百姓通過當局合法的手段無法解決問題的最后的救命稻草。因此在普通民眾的想象當中這一類人往往被理解成為具有正義感和使命感的俠客形象。而與此同時這一類人,也往往以俠客自居,不屑于為政治權(quán)力進行服務(wù),一般情況下都處于社會的邊緣。在這一類人身上最具有特點的是這些人自詡為俠客的這一行為和行為心理,在他們的身上最普遍的是跨越權(quán)力器官行駛社會正義,并且進行社會正義的裁判。當然我們不能排除這一類人中有渴望積極投身于合法政治的建設(shè)過程當中的個體,不過從這些人身上來看他們身上所具備的浪漫主義特質(zhì),很難最終融入當時的社會政治格局當中。
隨著歷史的發(fā)展,這一類人成為任俠的理由也在逐漸發(fā)生著變化,在文學(xué)文本之中對這些人物心理的塑造也在不斷地發(fā)生著改變。任俠的特點不再是因為作為俠客本身的最顯著特征,而是將所面臨的情感和道德困境作為建構(gòu)俠形象的最主要方式。這是因為俠本身從其歷史發(fā)展演進的過程中,逐漸成為不是以暴力解決社會問題或者取代暴力機關(guān)的社會群體,這一類人通常有著超越普通民眾的情況和道德需求或者說他們與一般民眾的最顯著區(qū)別是其身份的特殊性并不來自于自我的能力,而是來自于自我情感抉擇和道德選擇的諸多特殊心理訴求。
將張藝謀的新作作為文本的代表進行分析,就不難發(fā)現(xiàn)在張藝謀的筆下這種俠客的變體。《影》中的俠客形象早已超越了一般的烏托邦形象的塑造,在這部電影文本當中,影子武士也是相比較而言最具有新的任俠文化的代表者。當然不能否認的是在這部電影當中存在著非常多元的俠客形象,比如反面角色楊蒼在某種角度上看,實際上是進入政治活動當中的俠客的代表。沛國君主和他的胞妹也都是俠文化當中隱忍和愛憎分明的典范代表。不過這些人都不能被稱之為最核心的任俠文化的代表,他們并沒有自認為俠客或者自覺地擔負起俠客的使命,最近有俠客色彩的角色實際上是田戰(zhàn)是和影武士這兩個角色,這兩個角色實際上都應(yīng)該屬于子虞的門客,在子虞為中心的政治斗爭當中發(fā)揮了各自的作用。而影武士是這個形象在他自我發(fā)現(xiàn)的過程當中不斷地與自我角色如何并在這個人融合的過程當中發(fā)掘了他自身的任俠特點,并且在文本中說明了任俠對于傳統(tǒng)俠文化的超越。
二、任俠的情感建構(gòu)與自我放逐
在任俠的形象建構(gòu)過程中有兩個相對重要的特點,任俠區(qū)別于傳統(tǒng)下課形象的核心內(nèi)容。其中的一個方面,是任俠形象的情感進步方式與傳統(tǒng)俠客之間的差異。一般情況下下課的形象與下課所面臨的情感選擇大多是受到國家意識形態(tài)的影響所形成的一種自我壓抑式的情感關(guān)系和情感表達。譬如在早期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具有代表性的俠客往往都是為了所謂的國家和社會公義放棄了自我的情感生活,轉(zhuǎn)而投入到了一種舍生取義的道路選擇中。這種俠客形象在中國現(xiàn)當代的文學(xué)歷史上也普遍存在,譬如古龍和金庸的武俠小說中的俠客形象,也大多是為了民族和國家大義放棄了自我的情感生活。
但是在任俠形象的構(gòu)建過程當中,自我的情感表達顯得尤為重要。任俠與傳統(tǒng)俠客不同,通常情況下不需要來自社會和官方的承認,而是積極的踐行自我的價值觀和社會理想,因此任俠的情感建構(gòu)就往往會更加尊重個體的身份。在《影》這部電影中,影武士所面臨的情感模式,主要是與子虞夫人之間愛情糾葛和與母親之間的親情發(fā)現(xiàn)。在這兩種情感關(guān)系的處理中,影武士都顯得相對被動且相對自我,創(chuàng)作者在他的情感關(guān)系當中刨除掉了社會與國家強加給他的公義,甚至可以說在他的自我發(fā)現(xiàn)的過程中,他自覺的拋棄掉了這種社會公義轉(zhuǎn)而進行了自我發(fā)掘式的情感表達,這是張藝謀對于任俠形象內(nèi)涵的一種新的補充。在這種情感的自我表達方式下,任俠所面臨的就是被當時的意識形態(tài)和社會文化所驅(qū)逐的結(jié)果。在影片的敘事高潮部分,影武士不僅在國主與家主的選擇之間都進行了放棄,同時他也放棄了自己的愛人和母親的仇恨。在他選擇放棄這些情人關(guān)系的同時,他在復(fù)仇和自我發(fā)現(xiàn)的外衣之下,實際上表達的是一種基于對自我任俠身份考量和確認的自我放逐形式。他沒有再繼續(xù)局限于俠形象本身所帶給他的社會束縛和意識形態(tài)的控制,而是轉(zhuǎn)而尋求一種自我和解的形式進行對任俠身份的認同,這是他最終選擇自我放逐這一結(jié)局的真正含義,這個答案也能夠在子虞夫人的選擇上得到答案,也就是說,這種屬于任俠身份的發(fā)現(xiàn),是包括影武士自我在內(nèi)的全社會的放逐,也是任俠形象所不同于傳統(tǒng)俠客形象的新的俠文化內(nèi)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