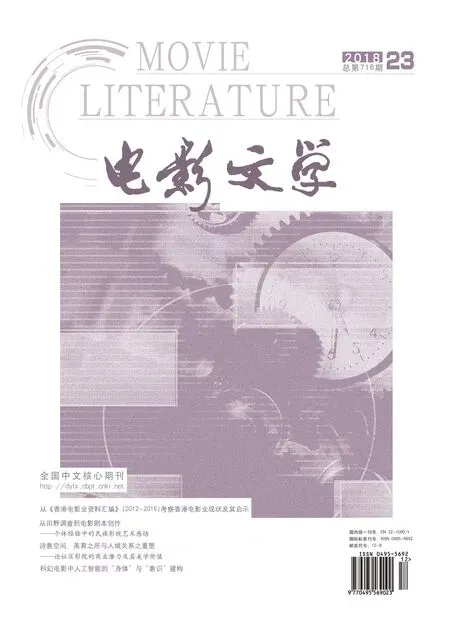偵探電影《三塊廣告牌》的敘事探索
鄭丹丹
(長江大學工程技術學院 外國語學院,湖北 荊州 434020)
在對《三塊廣告牌》的分類之中,對其社會類、劇情類的標簽屢見不鮮,但是不能忽視的是,這部電影的犯罪事實和案件參與者迫切希望找出兇手的敘事一直是貫穿這部電影的核心。我們無意去討論作為偵探類的電影到底應該具備哪些特質,或者偵探電影的分類邊界到底在哪里。我們只是試圖說明,在偵探類電影之中,圍繞某一起案件,勾連出與案件相關的人物與人物背景的敘事模式不容否認。這種敘事模式呈現出一種網狀的樣態,以中心事件(案件)作為貫穿始終的核心,圍繞這個核心,勾連出每一位人物,包括受害者、加害者、嫌疑人、探案者都存在著個體的敘事空間,在解決中心事件的同時,這些個體的敘事空間存在的問題也在不斷被解決被說明。這種敘事模式恰恰與《三塊廣告牌》相類似,不同的是,在《三塊廣告牌》中這種敘事模式發生了變化,雖然中心事件依然存在,但是中心事件并沒有真正意義上得到解決,相應地,當個體的敘事空間中的個體體認問題被解決之后,敘事就結束了,這實際上是一種以解決個體生命認知在權力結構作用中發生偏誤,又逐漸回歸自我的敘事追求,這也是這種類型的電影受到創作者與接受者歡迎的一個重要原因。
《三塊廣告牌》并不是最近這種類型電影的個例,本文試圖去分析這部電影,并不是要在內容上論證出這部電影與偵探電影的一致性,而是僅僅在敘事模式的層面上暫時將這種類型的電影歸類為偵探電影,并與偵探類型電影的敘事模式進行類比,目的是要說明蘊藏在這種敘事背后的深層次意圖,與這一類型的電影所提供出的一種全新的敘事可能。
一、傳統偵探電影的敘事特點
電影與小說的敘事不同,小說的敘事受到語言的限制,敘事的樣態更多呈現出一種線性的結構,這種結構在表現人物在某一空間內的社會性活動很難達到空間的平面化效果,在小說的敘事之中,不論作者做何種努力,敘事的節奏和人物的變化一定是按照既有的時間線索發展的,這種敘事最富于變化的就是改變敘事的時間,來達到突破時間與空間對于小說本身的限制,但是不論敘事時間與空間被做以何種調整,語言本身對連貫的時間的需要,永遠都是牢不可破的,這也導致了小說的敘事空間永遠都是被時間排列的,呈現線性的排列狀態。但是電影從這個角度上超越了小說這種依賴語言的敘事,電影不僅依賴于人物的語言表達,它也需要借用鏡頭來展現人物的行為狀態,因此鏡頭之后人物所處的空間是極具延展性的,空間受到時間的作用更加明顯,因為每一處空間都必須烙印上時間的特點,空間的敘事才會有所依據,但是空間并未因為時間的限制而減少對敘事的影響,甚至多個空間可以在同一時間內平行出現,一起構成敘事的張力。如果我們把電影的這種敘事特點放在尤其注重敘事策略的偵探懸疑一類的電影上來看,我們會發現這種特點尤其明顯。在傳統的偵探電影中,中心事件(案件)會利用電影的鏡頭特點,達到對每一個與中心事件有關的人物個體空間的發現,這種空間的發現是圍繞中心事件的解決而不斷被發現的,不過這種發現是一種已經既定的事實,在敘事者的角度中,這種空間的發現在需要符合邏輯推理的前提之下是需要被遮蔽的,因為每一種個體空間的敘事都有可能是中心事件的解決,基于這些敘事空間的串聯才能最終構成中心事件的發展事實。簡而言之,個體空間的發現都是服務于中心事件的解決的,一旦中心事件得以解決,那么敘事也就隨之結束。但是這種電影勢必會存在一種問題,當敘事的可能逐漸被減少,觀眾逐漸對種種敘事手段感到不再新奇,純粹以敘事的手段來吸引觀眾,或許會有嘩眾取寵之嫌。
二、權力結構與個體認知矛盾的解決
當中心事件發生時,實際上在說明某一種矛盾被激化,而參與到中心事件的每一個人物都是被某種權力結構建構到社會關系當中去的,一個人的死亡昭示著一種社會關系的斷裂,這種社會關系的斷裂也可以被視為權力結構在社會規訓的時候產生了缺陷。這個缺陷實際上與中心事件發生的環境背景和社會底色有著密切的關系。
從敘事空間的層面上看,這種著力表現社會狀態的敘事,依靠鏡頭敘事特意與文字敘事的特點,突出了在敘事空間上,可以同時展示某一場域之下多個個體空間的行為,使敘事在空間上具有同步性,并且以此為基礎,以某幾個主要人物為核心表現出某一社會場域之下的權力結構關系。從電影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心事件發生的小鎮是敘事的全部空間,一旦人物離開小鎮,就預示著個體的生命體認發生了變化,這是由于權力結構必須在一個一定的范圍內才能保持穩定。小鎮作為中心事件的發生地也是影響最大的場域,在敘事上與外界形成了一種閉合狀態,在這個“生態圈”中,不同的人彼此交互,形成了與以往不同的社會關系,而促成這些交互關系發生的,恰恰就是我們一再關注的中心事件。
在《三塊廣告牌》中,失去女兒的麗德與威洛比警長的關系、麗德與迪克森的關系、麗德與追求者詹姆斯的關系、乃至麗德與前夫之間的關系,都因為這場謀殺案而被敘述出來,在這些關系中,有在謀殺發生之前就已經存在的,也有在謀殺發生之后才締結的關系,但是無一例外的是,這些情感關系和人際交互都是因為謀殺的發生而被迫或者主動被推進的,每一對關系的深化圍繞著中心事件的討論而進行,甚至不僅是主人公麗德締結的關系,對于迪克森和警長威洛比之間的關系、雷德與父親的關系也符合這種關系的演變關系。但是就如上文所討論的,這些人物關系由于中心事件而締結,但是也一定要圍繞中心事件所發生的場域而變化。這個場域所指涉的不是中心事件發生的場所或者客觀意義上的空間,而是中心事件所涉及的權力場的抽象范圍,這個權力場仿佛是一個供相關人物表演的舞臺,是每一個人物締結情感關系、到達與自我和解的場所,一旦離開這個權力場,就意味著某種權力關系被解體或者被重新建構,個體的情感空間就會發生變化。
影片當中麗德和迪克森踏上了離開小鎮去找一個最有嫌疑的人,電影隨之結束。但是這個決定又明確地昭示著,迪克森已經自我蛻變成了一個敢于擔負責任、敢于正視自我的警察,舊有的依賴、拖沓與自我保護已經被撕碎,而麗德也終于在迪克森面前放下蠻橫、粗魯的舊有心理,兩個人實際上都意識到了自我在舊有的權力結構之下的異樣狀態,他們特殊性格的養成都是在面對生活的長期負荷之下,所產生的自我保護機制。這種自我保護,因為女兒被殺、警長自殺等事件而被重新認識,最終也因為中心事件的逐漸解決而被改變。而離開中心事件所覆蓋的權力場,正是敘事者追求的一種隱喻,他們克服了一種權力結構的影響,但也是由于對權力結構的反叛,他們也將進入到更大的權力場域之中。
另一方面,從內容上看,如果我們把中心事件與被宣布有罪本身視為某種權力結構的話,我們往往會發現,在中心事件解決的同時,每一位參與者都可以被宣布有罪,因為他們每一個人在處理社會關系的同時,受到權力結構的影響,都或多或少地影響了受害者的死亡或者加害者的施暴。更廣泛一點來說,每一位與中心事件有關的人物,或者是在中心事件發生以前就已經對個體生命的認知產生困惑,或者是在中心事件發生以后由于某種社會關系的崩潰,而察覺到了自我生命認知的不足或畸形。而在伴隨著中心事件的逐步解決的同時,這些自我生命的體認不斷與社會和自我達成和解,最終當自我和解以后,敘事的過程也就完成了。這實際上是在不斷拋棄所謂“真相”,隨著中心事件的解決,這在內容上是對個體的一種發現。
權力結構的關系在空間上對人物變化的發揮的作用實際上是基礎性的,是人物關系的形成和解體的前提。與以往的偵探題材電影不同,《三塊廣告牌》敘述的是發生在案件之后七個月的人物關系。這實際上給了人物在這段時間之內情感的發酵時間。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影片所拍攝的人物情感是緊接謀殺事件的,人物彼此的矛盾、同情都是在謀殺已經開始就形成了的,甚至敘述者也無意于反復強調這段時間對中心事件和人物的影響,在這里時間對空間的塑造作用十分微弱,這是因為小鎮中的權力結構關系是固定的,這種穩定的狀態因空間當中的某些特質的變化而終被打破。電影敘述的故事開始于廣告牌的租賃與重新安裝,但是人物的個體生命困惑卻并不是在廣告牌的重新安裝之后才開始的,比如迪克森的性格困境,他長期在失敗的陰影中生活,自私、懦弱、自大。促使他發生改變的是在電影中警長死后的一封遺書,但實際上,他在深層中對麗德還是抱有同情的,這種同情讓他認識到了自我的失敗,他與麗德的對立是由于他將自己的成功寄寓在警長的成功之上,這或許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源于父權的崇拜,而當他失去父權權威并且得到來自父權象征的權威確認的時候,他才會鼓起勇氣面對自我。這些內心矛盾才是最終促使他發生改變的根本原因。而電影試圖表達的就是因為中心事件所發揮的引導作用而形成的人物對自我的發現。這些自我發現促成了一種圍繞中心事件形成的自我救贖,還原了一種逼近生活的真實樣態。
三、邏輯的背叛與后現代的追求
在傳統的偵探電影中,與案件相關的人本身往往是電影敘事的核心內容,這類電影脫胎于傳統偵探小說的敘事,著力通過描寫排除破案者與受害者意外的嫌疑人的活動細節,按照邏輯推理的方式揣測案件中的真兇和案件發生的過程。
但是最近幾年出現的電影中,這種電影的敘事焦點發生了偏移,敘事的終極目的不再是對中心事件的發生過程進行邏輯層面的推斷和關鍵證物的搜集。如果我們還是把某一案件稱之為中心事件的話,那么圍繞這個中心事件的其他個體空間成為這部電影敘事的重頭戲。我們不難發現這種變化的來源實際上是脫胎于傳統的偵探小說的敘事模式的。在伴隨著中心事件解決的同時,個體敘事空間中一定包含著與中心事件相勾連的事件,這些事件雖然在早期的敘事中起到了迷惑觀眾、混淆真兇的敘事策略的作用,但是對觀眾而言,最令他們印象深刻的往往不是邏輯周密的推理過程,而是這些個體與中心事件之間結成的關系。按照邏輯思考和推理形成的事件原貌,勢必要還原事件發展的最早時間,也就是推理的結果實際上是要依靠線性的時間線索對事件給予解釋的。也就是說每一位觀眾都必須進入由邏輯構建起的社會場域之中,這實際上就是現代性所推崇的理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現代性當中證據與法律至上的一種表現。但是在敘事的過程中,人物的個體生命感知與中心事件的勾連,往往會超越邏輯的嚴密推理,而更加成為使人印象深刻的敘事部分,人與人在中心事件的解決過程之中所締結的情感關系成為接受者更加關注的部分。這種情感關系往往因為生活的真實而在相應題材的電影中表現為不可知和無緒的狀態,這實際上是一種對生活的回歸,以及對邏輯、理性等現代性代名詞的反抗。
在《三塊廣告牌》這部電影的敘事中,真相永遠是缺席的,每一個人都在迫切地渴望尋找到真正的兇手,但是直至影片的最后也沒有找到真兇。每一個人物個體的自我和解并不意味著對中心事件的放棄,而是在圍繞中心事件完成任務對事件發生以前的自我的超越與成長。這種敘事沒有交代一個完整或者確定的時間線索和符合線性時間發展的事件經過,即使是對敘述者來說,電影的真相和事件發展的原貌也是不可知的。敘事者或者創作者都不再扮演一個全知全能的人物,故事的發展,在劇情上完全超過了他們的掌控,甚至某些敘事對敘事者或者創作者而言也是被遮蔽的。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創作者和接受者共同的審美追求。邏輯的論證與精密的敘事安排總與真實生活存在著距離,這種距離雖然可以被稱為一種審美的向度,但是與真實生活迥然不同。而對真實生活的追求也是對被現代性話語遮蔽的真實性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