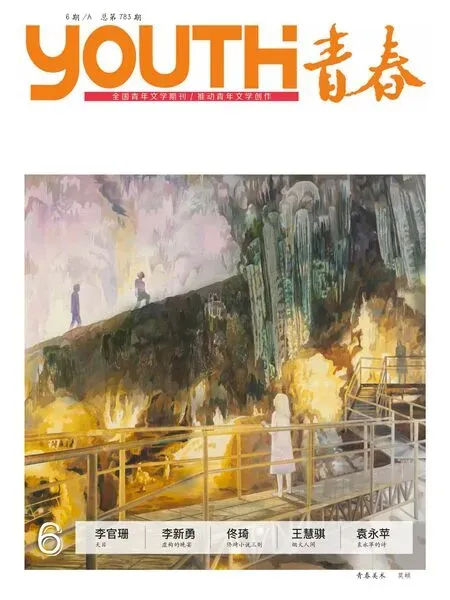兩地居:尋找魯迅
口 王磊光
紹興:在魯迅最初的居所
我從沒(méi)有見(jiàn)過(guò)一座城市如此偏愛(ài)黑色,像紹興這般。黑色的石頭古街、黑色的船、黑色的瓦、黑色的門(mén)、黑色的窗、黑色的樓板,連路邊的樹(shù)也似乎是黑色的了。墻倒是白色,但依然會(huì)鑲上黑色的邊。甚至不少現(xiàn)代化的大樓,其色澤也是暗色調(diào)。
行走在這個(gè)城市里,你一下子就觸摸到《野草》的底色和那濃得化不開(kāi)的情感,又想起了《鑄劍》中那個(gè)黑色的人。你忽然會(huì)明白,為什么魯迅那般熱愛(ài)木刻。木刻黑白分明的色調(diào),就是他故鄉(xiāng)的色調(diào)。
魯迅故里已經(jīng)不再屬于魯迅,變成了紹興文化,乃至整個(gè)越文化的長(zhǎng)廊。文化廣場(chǎng)上,立著一面墻,刻有魯迅的巨幅雕像,是魯迅吸煙的樣子,煙霧繚繞著他那充滿憂思的面容。魯迅故居與整個(gè)家族的房子連通在一起,里面建有魯迅紀(jì)念館、民俗風(fēng)情園等。魯迅家的房子十分寬闊,這讓我想到魯迅在上海最后的居所,那般逼仄,倒未必是他所喜歡的。百草園還在,卻不是我想象的模樣。整個(gè)園子主要是種菜,只有一側(cè)種著一點(diǎn)草,想必沒(méi)有“百草”。一棵高大的樹(shù),結(jié)著桂圓一樣的果實(shí)。身邊有人說(shuō),那是皂莢樹(shù),魯迅在書(shū)中寫(xiě)過(guò)的。但我知道,那不是皂莢樹(shù),皂莢是長(zhǎng)長(zhǎng)的。四周有鳥(niǎo)叫,叫聲十分清幽,倒是平添了一些彼時(shí)的感覺(jué)。只是不見(jiàn)鳥(niǎo)的影子。到處都是游客,直沖云霄的“叫天子”再也見(jiàn)不到了。
魯迅故里有咸亨國(guó)際影城、咸亨酒店。據(jù)說(shuō)咸亨酒店已經(jīng)世界聞名了。這個(gè)當(dāng)然得感謝魯迅。這里的街道早被改造成民俗街,店鋪一家接一家,賣著各種紀(jì)念品、食物、特產(chǎn)之類的。給我印象最深的是紹興臭豆腐和黃酒。黃酒又稱“花雕”“女兒紅”,或者“女酒”。“女兒紅”很動(dòng)聽(tīng),既通俗又雅致,叫人喜歡。“花雕”更是個(gè)好聽(tīng)的名字。我的朋友、作家劉麗朵寫(xiě)過(guò)一篇文章,叫《最愛(ài)是花雕》。一個(gè)北方女兒開(kāi)口便說(shuō):最愛(ài)是花雕!買斷江海是酒錢(qián)!這背后有著怎樣的豪氣與膽識(shí)!劉麗朵在北大的碩士論文,寫(xiě)的便是紹興府山陰人徐渭。但是,花雕,到底是個(gè)悲傷的名字。紹興古俗,要在女孩出生時(shí),選數(shù)壇好酒,封泥存上,等到女孩出閣之日,再打開(kāi)來(lái)謝客。倘若女孩未成年而先夭折,就稱為“花凋”。所以民間流傳一句話:“來(lái)壇女兒紅,永不飲花雕。”不過(guò),我最喜歡“女酒”這個(gè)名字,它把“女人”與酒聯(lián)系在了一起,把女性的種種融注在酒里。也可讓我們想見(jiàn)古越地女子的溫柔與英豪。——秋瑾就是這樣的越地女子。從魯迅故居往西南,不到兩里,即是秋瑾故居;往北,約兩里,便是秋瑾就義的古軒亭口。
民俗街上立有一些雕像,一律都是黑漆漆的。記得有一尊是孔乙己。然而這所有的黑色雕像,都有一股精氣神在,讓我想到一種形象:紹興師爺——博學(xué),脾氣大,好評(píng)點(diǎn)時(shí)事,好罵人,嚴(yán)肅中又不乏幽默。不用說(shuō),魯迅身上就有著濃重的師爺氣。
魯迅家對(duì)面便是三味書(shū)屋。書(shū)屋外有一條河,河水是黑色的。這種黑色自然不是紹興人喜愛(ài)的,它是環(huán)境污染的結(jié)果。一百年前,在魯迅的時(shí)代,紹興的水定非這樣。記得周作人回憶起故鄉(xiāng)的河,說(shuō)它有著“白鵝似的波浪”,那是多么清亮的水呵!幾只烏篷船載著游人,在河上緩緩行駛。烏篷很小,我懷疑這不是當(dāng)年的模樣,比起我在電視里看到的,要小上很多。我向一個(gè)本地人求證,他說(shuō)就那么大,從前也是這般大。烏篷是用來(lái)?yè)跤甑模陙?lái)了,人就躲進(jìn)去;太大會(huì)被風(fēng)吹壞。當(dāng)年,周家兄弟就是坐著這樣的船離開(kāi)紹興的么?
在老師授課的教室正中擺著一張桌子,桌邊放置數(shù)把椅子。其中一把椅子是壽鏡吾先生自己的座位,魯迅說(shuō)過(guò),壽先生是一個(gè)“極方正、質(zhì)樸、博學(xué)”的老人,雖然也有一把戒尺,但不常用。其它椅子,據(jù)說(shuō)是供客人坐的。學(xué)生的桌子在房間四周,靠著窗或墻壁。因此授課時(shí),學(xué)生是背對(duì)著先生。有了這個(gè)條件,魯迅才有機(jī)會(huì)偷偷地從小說(shuō)中臨摹下許多繡像。魯迅的桌子在最里邊的角落里。還是當(dāng)年的桌子,刻著全中國(guó)人都熟悉的那個(gè)“早”。
從魯迅故居出來(lái),幾百米遠(yuǎn),就是“沈氏園”了。一個(gè)私家園林,傳承上千年,已成為今日聲名遠(yuǎn)播的“沈園”,只因陸游與唐婉的一段悲催的愛(ài)情故事。我從沒(méi)有想到,魯迅與陸游離得這樣近。他們的婚姻,過(guò)程是如此不同,結(jié)局卻如此相似,都是悲劇,而且都是因?yàn)槟赣H,陸游不得不與心愛(ài)的女人分離,而魯迅卻終生不能拋棄母親留給自己的“遺產(chǎn)”。
在沈園內(nèi)部的一道圓門(mén)口,遇一美麗導(dǎo)游,與她注目數(shù)次。后來(lái)聽(tīng)她講陸游與唐婉,聲音清越,美目盼兮。在魚(yú)池邊,她的講解結(jié)束了。她說(shuō),我走了。幾個(gè)游客也要跟著回去,她說(shuō):我送你們出去。我留在了那里。抬起手指,像風(fēng)一樣,輕輕翻動(dòng)掛在樹(shù)上的密密匝匝的許愿鈴,忽然讀到“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離”,頓生傷感。我默然穿過(guò)木橋,走上假山,然后下來(lái),也離開(kāi)了。正所謂:傷心之地,不宜久留。
紹興不大,路也不寬闊,人們熙熙攘攘,卻并不匆忙,處處顯露著熱鬧與和樂(lè),這是過(guò)日子的本色。從火車站到魯迅故居,很多三輪車夫拿著景點(diǎn)介紹,招攬著外來(lái)的客人:“要不要去看紹興古街?”每拉上一個(gè)游客,便會(huì)邊踩著車,邊大聲講述著紹興的名人古跡,言語(yǔ)里充滿自豪。然而,紹興的夜晚,卻有一種濃烈的黑與沉,一鉤黃月懸在這黑而沉的天幕上。這時(shí)候,魯迅故居是寂寞的。游客已消散了,民俗街上的店鋪也早早收?qǐng)隽恕_@里很久就沒(méi)有居民居住,陰森森的一片,有些怕人。百草園里那條美女蛇,會(huì)在這時(shí)候出來(lái)誘惑書(shū)生么?
已經(jīng)沒(méi)有了祖父。沒(méi)有了母親。沒(méi)有了壽先生。沒(méi)有了長(zhǎng)媽媽。沒(méi)有了兄弟。沒(méi)有了閏土和“老爺”……都沒(méi)有了。只有這片土地還在。他們的文字還在,他們的故事也還在被我們斷斷續(xù)續(xù)地講述著。
上海:在魯迅最后的居所
魯迅故居是寂寞的。
問(wèn)了幾個(gè)人,折幾個(gè)路口,才看到“山陰路”。看到山陰路,我就知道,離魯迅故居不遠(yuǎn)了。盡管來(lái)時(shí)經(jīng)過(guò)魯迅公園,我并沒(méi)有立刻進(jìn)去,執(zhí)意要先找到魯迅故居。公園不屬于魯迅,故居才是他的。
然而魯迅故居是寂寞的。寂寞到只有我一個(gè)游客。工作人員打開(kāi)門(mén),引我進(jìn)去。一樓擺放著兩張老桌子,一個(gè)牌子上用中、英、日三種文字寫(xiě)著“待客廳”。工作人員說(shuō),這些都是按照魯迅當(dāng)年的布置擺設(shè)的。我問(wèn):“它們都是魯迅當(dāng)年留下來(lái)的東西嗎?“工作人說(shuō):“是的,都是他當(dāng)年用過(guò)的。”
客廳的后面是廚房。
上二樓,首先看到一間小房子,是雜物間。雜物間前面一間便是魯迅的臥室兼書(shū)房。房間里亮著燈。一張簡(jiǎn)陋的鐵床擺在那里,床上折成長(zhǎng)條的被子顯得很單薄。盡管是夏日,看到它一股寒意便向我襲來(lái)。大概是它在那里放得太久的緣故,陳舊了,泛著冷光。靠窗的位置是書(shū)桌,書(shū)桌旁邊有兩張椅子。還有一個(gè)專門(mén)放置茶杯的小桌子——擔(dān)心茶涼了,許廣平就做了一個(gè)罩子。
作為故居當(dāng)年的見(jiàn)證者,梅志先生在《胡風(fēng)傳》中有過(guò)詳盡的描繪:“進(jìn)門(mén)里手有一張方桌,離先生睡的中式鐵床不遠(yuǎn)。那鐵床還掛有蚊帳,上有繡花帳簾,顯得樸實(shí)而又美觀。另外就是靠窗的一張大桌,上面堆滿了書(shū),桌前有一張木制輪椅,是先生寫(xiě)作時(shí)的座椅。桌旁有一張已很舊的藤椅,這時(shí)鋪著毛毯,可能是先生疲倦時(shí)用來(lái)休息躺一會(huì)的。靠墻一個(gè)小半柜,上面也是書(shū)和幾個(gè)小鏡架,多半是他喜愛(ài)的木刻或別的畫(huà),沒(méi)有個(gè)人及全家的照片。這房間不算大,但不顯得擁擠,而令人感到很協(xié)調(diào)和諧。”
工作人員說(shuō),從33年到36年,魯迅就在那張桌子上寫(xiě)作。我一下子想到魯迅在一篇文章中所寫(xiě):“我先前往往自負(fù),從來(lái)不知道所謂疲勞。書(shū)桌面前有一把圓椅,坐著寫(xiě)字或用心的看書(shū),是工作;旁邊有一把藤躺椅,靠著談天或隨意的看報(bào),便是休息……”
這圖畫(huà)還在,只是少了畫(huà)中人。
窗外的世界亮著,房間里的燈也亮著。窗戶玻璃上的光,亮過(guò)了室內(nèi)的燈光,對(duì)比下來(lái),房子里的光線中彌漫著昏黃。寂寞襯著昏黃,昏黃籠著無(wú)邊的寂寞。
先生就是在這間房里逝世的。
“我醒來(lái)了,喊醒了廣平。
‘給我喝一點(diǎn)水。并且去開(kāi)開(kāi)電燈,給我看來(lái)看去的看一下。’
‘為什么?……’她的聲音有些驚慌,大約是以為我在講昏話。
‘因?yàn)槲乙^(guò)活。你懂得么?這也是生活呀。我要看來(lái)看去的看一下。’
‘哦……’她走起來(lái),給我喝了幾口茶,徘徊了一下,又輕輕地躺下了,不去開(kāi)電燈。
我知道她沒(méi)有懂得我的話。”
因?yàn)槲乙^(guò)活,你懂得么?然而現(xiàn)在,寂寞襯著昏黃,昏黃籠著無(wú)邊的寂寞。
我要看來(lái)看去的看一下。然而先生早已不在人世了。
我又問(wèn):“這些東西都是魯迅當(dāng)年的東西嗎?”
工作人員說(shuō):“是的,都是的。”
他還說(shuō):“最好的房間在三樓,魯迅讓兒子和保姆住。”他這么說(shuō),我一點(diǎn)也不奇怪。魯迅是中國(guó)反封建反傳統(tǒng)最激烈的知識(shí)分子,然而又是真正堅(jiān)守傳統(tǒng)人倫的一個(gè)。他對(duì)母親、對(duì)原配朱安、對(duì)兄弟周作人、對(duì)妻子許廣平、對(duì)兒子海嬰所做的一切,都可以證明。
三樓的房間果然最好。一邊是雅潔的客房,就在這里,當(dāng)年魯迅掩護(hù)過(guò)瞿秋白、馮雪峰等人。蕭紅、蕭軍、胡風(fēng)他們當(dāng)年就在這里留宿過(guò)吧?客房前的大房子,便是海嬰的臥室。房間里有藤編的桌子。最引我注意的是那張木床。床看起來(lái)很短,然而寬闊,兩頭有高高的擋板。工作人員說(shuō):“這床本是魯迅睡的,后來(lái)為了方便保姆照顧孩子,就把床給了海嬰。” 可以想象,多少個(gè)夜晚,魯迅在樓下寫(xiě)作;而海嬰趴著擋板,跟保姆嬉鬧著。
我問(wèn):“海嬰后來(lái)常來(lái)這里嗎?”
工作人員說(shuō):“以前常來(lái),后來(lái)年紀(jì)大了,就不來(lái)了。聽(tīng)說(shuō)十幾年沒(méi)來(lái)了。”
然而,魯迅唯一的孩子——周海嬰,也已離開(kāi),到無(wú)窮的虛無(wú)中尋找自己的血親去了。
“周作人、周建人的后代來(lái)過(guò)嗎?”
“好像從沒(méi)有來(lái)過(guò)。反正我在這里工作的四五年,沒(méi)有看到過(guò)。”
我再次問(wèn):“這些都是魯迅當(dāng)年的東西嗎?”
“都是的,都是真的。我不是說(shuō)過(guò)嗎?”工作人員不耐煩了。
然而,下去的時(shí)候,我突然拍著樓梯拐角處的石頭柱子,再次問(wèn)了同樣的問(wèn)題。
“我不是說(shuō)過(guò)嗎?都是魯迅當(dāng)年用過(guò)的,都是真的。”但我知道,魯迅逝世后,許廣平就從這里搬出去了,房子幾易主人。這些東西是怎么保存下來(lái)的呢?
工作人員終于耐心給我解釋:許廣平搬出這棟樓的時(shí)候,也把所有東西都搬走了,寄存在淮海路的一間房子里。因?yàn)樗溃斞甘且恢袊?guó)人紀(jì)念的。1950年,恢復(fù)魯迅故居之時(shí),許廣平把所有東西都捐獻(xiàn)給了國(guó)家。這房間的擺設(shè)都是按照許廣平的回憶布置的。不僅里面的東西都是當(dāng)年魯迅用過(guò)的,就連這樓房,也是當(dāng)年的房子,不是重建的。我們每年只不過(guò)做一些維護(hù)工作。
魯迅逝世后,除過(guò)撫養(yǎng)兒子海嬰,許廣平做的最大工作就是想方設(shè)法保護(hù)好魯迅的遺物。
確認(rèn)這一切都是魯迅用過(guò)的原物,我心里一下子舒坦下來(lái)。
沿著山陰路,前往魯迅公園。路邊還是一個(gè)弄堂接著一個(gè)弄堂。我估摸著,這里民居的格式還是當(dāng)年的樣子吧,只是這些房子都是后來(lái)重建的,唯有魯迅故居除外。買票參觀時(shí),我問(wèn):“魯迅故居怎么這么偏僻啊!”售票人說(shuō):“正因?yàn)槠В斞覆艜?huì)選擇在這里居住。”他沒(méi)有明白我的意思,我想說(shuō)的其實(shí)是,為什么到了今天,魯迅故居這一帶還是如此偏僻、冷清。在路上,如果你不仔細(xì)搜尋,幾乎難以找到一個(gè)指示牌。
我想著魯迅的夜晚,想著他最后的夜晚:
“街燈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顯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識(shí)的墻壁,壁端的棱線,熟識(shí)的書(shū)堆,堆邊的未訂的畫(huà)集,外面的進(jìn)行著的夜,無(wú)窮的遠(yuǎn)方,無(wú)數(shù)的人們,都和我有關(guān)。我存在著,我在生活,我將生活下去,我開(kāi)始覺(jué)得自己更切實(shí)了,我有動(dòng)作的欲望——但不久我又墜入了睡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