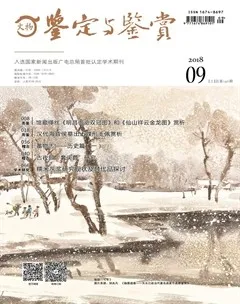“假司馬印”與“軍假司馬”印考釋
周舟 鄭媛媛 秦欣欣
摘 要:新鄉市博物館館藏有“假司馬印”與“軍假司馬”印兩枚印章,兩者皆為兩漢時期的官印。“假司馬”應為“軍假司馬”的簡稱,二者為同一官職,但“假司馬”有時也是其他司馬類官職副職的簡稱。
關鍵詞:新鄉市博物館;假司馬;軍假司馬
新鄉市博物館館藏數枚漢代的軍印,這些軍印對于研究漢代軍事制度有著重要意義。其中館藏的漢代“假司馬印”和“軍假司馬”印雖然僅僅只差一字,但在學術界引發不小的爭議。而“假司馬”與“軍假司馬”這兩個官職,又在漢代的軍隊中廣泛存在。因此,筆者查閱大量歷史文獻,結合新鄉市博物館館藏的相關文物,對此問題進行探討。
1 “假司馬印”與“軍假司馬”印概況
“假司馬印”,銅質,帶孔半圓鈕,方形,保存完整,通高1.9厘米,印面每邊長2.4厘米,重51.6克。陰刻“假司馬印”四字,四字從左至右分兩列,兩列分別為“假司”“馬印”,四字大小基本一致(圖1)。“軍假司馬”印,銅質,帶孔半圓鈕,方形,保存完整,通高1.95厘米,印面每邊長2.4厘米,重51.2克。陰刻“軍假司馬”四字,四字從左至右分兩列,兩列分別為“軍假”“司馬”,四字大小基本一致(圖2)。這兩枚印章印面布局嚴謹工整,造型簡單,渾厚豐腴,雕刻刀法粗獷豪放,具有漢代印章的典型特點。同時,兩枚印章大小、規格和字體基本一致,鑄造時間不會相差太遠。
2 “假司馬”應為“軍假司馬”的簡稱
《后漢書·百官志》載:“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軍司馬一人,比千石。部下有曲,曲有軍侯一人,比六百石。曲下有屯,屯長一人,比二百石。其不置校尉部,但軍司馬一人。又有軍假司馬、假侯,皆為副貳。”[1]由此可知,“軍假司馬”應為大將軍賬下的屬官,為“部”的主官“軍司馬”的副職,俸祿應在一千石至六百石之間。漢軍作為一支強大的軍隊,“軍假司馬”在漢代的軍隊中應該較為普遍,但這一官職在兩漢的史籍中卻很少出現,反而“假司馬”一職卻在史書中多次出現。《漢書·趙充國傳》載:“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為虜所圍。”[2]《后漢書·班超傳》載:“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為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于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3]《后漢書·西羌傳》載:“任尚又遣假司馬募陷陳士,擊零昌于北地,殺其妻子,得牛、馬、羊二萬頭,燒其廬落,斬首七百余級,得僭號文書及所沒諸將印綬。”[4]
面對歷史文獻中的“假司馬”和“軍假司馬”,二者究竟有什么關系,史料記載比較模糊,許多學者便給出了自己的答案。賀官保和陳長安在《洛陽博物館館藏官印考》中指出:“軍司馬下設四個軍假司馬,軍假司馬下設八個假司馬。”[5]兩位先生將“假司馬”認定為“軍假司馬”的屬官,并具體指出“軍假司馬”秩比六百石,“假司馬”秩比二百石。王獻唐的《五鐙精舍印話》認為:“殆所謂假司馬者,本與軍假司馬同官,初時但名假司馬,因亦照此刻印,后以隸于軍中,恐其通名易溷,仍依軍司馬名,于上加軍字為別,知軍假司馬印,仍由假司馬印演進而出者也。”因此,“凡假司馬印,類出西漢,西漢本名假司馬故也。軍假司馬印,則出東漢,東漢改名軍假司馬故也”[6]。王獻唐判斷“假司馬”和“軍假司馬”為同一官職,只是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稱呼。面對前人的觀點,筆者對此有著不同的判斷。《漢書·韓延壽傳》記載:“五騎為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轂。”[7]可見,在西漢也有“軍假司馬”的稱謂。同時,由前文可知在《后漢書·班超傳》《后漢書·西羌傳》中也皆有“假司馬”。因此,王獻唐的觀點不太準確。再根據新鄉市博物館館藏的“假司馬印”和“軍假司馬”印形態結構,兩枚印章尺寸、重量、大小基本一致,“假司馬”和“軍假司馬”應該也不是俸祿相差四百石的兩個官職。
筆者結合《后漢書·班超傳》的相關內容,推斷出“假司馬”應為“軍假司馬”的簡稱。《后漢書·班超傳》記載班超以“假司馬”之職出征匈奴,后出使西域。在出使鄯善過程中,突襲匈奴使團,迫使鄯善王歸漢。漢明帝贊嘆:“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為軍司馬,令遂前功。”[8]班超升任“軍司馬”后,“平陵人徐干素與超同志,上疏愿奮身佐超,五年,遂以干為假司馬,將馳刑及義從千人就超”[9]。后徐干也立軍功,“以徐干為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10]。從上述引文中,我們得知班超和徐干皆因軍功由“假司馬”升任“軍司馬”,又徐干以“假司馬”的身份輔佐“軍司馬”班超,可證此“假司馬”應是僅次于“軍司馬”的官職,與“軍司馬”是正副職的關系。再結合前文,“又有軍假司馬、假侯,皆為副貳”,“假司馬”和“軍假司馬”應是同一官職,“假司馬”是“軍假司馬”的簡稱。又據《宋書·百官志》對漢代官職的描述,再次談到“軍假司馬”,“若不置校尉,則部但有軍司馬一人。又有軍假司馬、軍假侯,其別營者則為別部司馬”[11]。這與《后漢書·百官志》記載基本相同,只是存在“軍假侯”與“假侯”的區別。可見,“假侯”應是“軍假侯”的略稱,這進一步說明“假司馬”應是“軍假司馬”的略稱。
雖說“假司馬”是“軍假司馬”的略稱,但筆者在查閱史料過程中,也發現一些特殊情況。《后漢書·段颎傳》載:“颎乃分遣騎司馬田晏將五千人出其東,假司馬夏育將二千人繞其西。羌分六七千人攻圍晏等,晏等與戰,羌潰走。”[12]“騎司馬”在史書中不常出現,史書中的《職官志》也沒有對其記載,推測應為主騎兵的軍官,實物有印章“騎司馬印”[13]。那么,文中出現的“假司馬”是否還是“軍假司馬”,筆者存在疑問。又據《漢書·西域傳》記載:“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為斥候,屬校尉,事有便宜,因騎置以聞。”[14]“騎假司馬”的出現,應是《段颎傳》中“假司馬”的有力解釋,《段颎傳》中“假司馬”應是“騎假司馬”的簡稱。可見,“假司馬”在史料中不僅是“軍假司馬”的簡稱,還會是其他司馬類官職的副職簡稱,但這種情況出現極少,“假司馬”往往還是以“軍假司馬”的簡稱出現。
參考文獻
[1]范曄.后漢書·第12冊[M].北京:中華書局,1973.
[2]班固.漢書·第9冊[M].北京:中華書局,1964.
[3][8][9][10]范曄.后漢書·第6冊[M].北京:中華書局,1973.
[4]范曄.后漢書·第10冊[M].北京:中華書局,1973.
[5]賀官保,陳長安.洛陽博物館館藏官印考[J].文物,1980(12):57.
[6]王之厚.文字與錢幣[M].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2002.
[7]班固.漢書·第10冊[M].北京:中華書局,1964.
[11]沈約.宋書·第4冊[M].北京:中華書局,1974.
[12]范曄.后漢書·第8冊[M].北京:中華書局,1973.
[13]羅福頤.秦漢南北朝官印征存[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14]班固.漢書·第12冊[M].北京:中華書局,1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