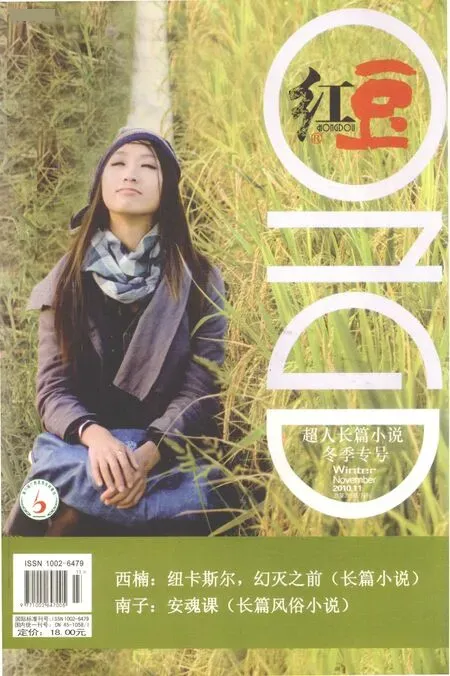黑天鵝之死
李欣,女,廣西南寧人,生于20世紀70年代,現供職于廣西交通科學研究院有限公司。
那只黑天鵝大概沒有想到,它的死亡竟會如此狼狽和意外。法國作曲家圣桑在組曲《動物狂歡節——天鵝》里用大提琴和鋼琴描繪了一個高貴嫻雅的生靈,它在幽靜的湖面上慢慢游弋,自由而又從容;俄國芭蕾舞蹈家巴甫洛娃則將這一曲子演繹成了一段哀婉悲情的舞蹈,那是一只天鵝在絕望中的求生。從《天鵝》到《天鵝之死》如此相同,又迥然相異。
黑天鵝在自己家門口悠閑地散著步(如果公園也能稱之為“家”的話),它從未意識到早有兩雙貪婪的眼睛盯住了自己。2017年5月的某個凌晨,一只半歲大的黑天鵝被人從上海徐家匯公園偷走,之后它死了,原因不明,很有可能是因為窒息。它大概是被包裹在衣物或者塑料袋中,由于害怕被保安和路人發現,黑天鵝一定是被緊緊地捂著,在不斷地掙扎、扭動和嘶叫中死去。
天鵝,國家二級保護動物。因為體型優美、儀態高貴而深受人們喜愛,它們對于伴侶的忠誠被認為是愛情的象征。這樣美麗的生物,激發了多少藝術家的創作靈感:柴可夫斯基的《天鵝湖》是一曲愛情的頌歌;安徒生的《丑小鴨》是一則關于天鵝純真本質的童話;巴甫洛娃演繹的天鵝縱然瀕臨死亡,卻依舊用優雅的姿態來面對。
然而這只黑天鵝卻得不到那樣的期許和贊嘆了。它尚未成年,沒來得及體會到愛情的滋味就被偷走;它的羽翼還不夠豐滿,估計還沒嘗試到展翅翱翔的快樂;甚至連最后的挽歌它都未能及時吟唱就忽然死亡了。而后它的肉體,一部分和一根廉價的蘿卜燉在一起,成為了人類的下酒菜;另一部分因為“口感不好”被當作垃圾丟棄了。
結局竟會是這樣。在大多數人的眼里,天鵝應當和《紅樓夢》里的林妹妹一樣“質本潔來還潔去”才對,它理應帶著銀白的光環和動人的音樂慢慢從人們的視野里消失,然后在一處寧靜而且水草豐茂的地方迎接死神到來,這才是人們賦予天鵝的正常死亡。如果在弱肉強食的自然界里,它極有可能喪生在一只狡猾的狐貍或者兇殘的豺狗口中。那些兇猛的動物是不會嫌棄天鵝肉的,它們肯定饑不擇食,此等美味的食物可不會時時都有,所以它們絕不會暴殄天物,說不定心里面還在暗暗感謝上天饋贈。這是自然的法則,屬于動物的天性和本能。
可是在這個人類構建的文明社會里,被視為高尚珍稀的天鵝卻給盜殺了,理由僅僅是因為要“改善伙食”。這算是寫給人類自己的冷幽默吧。
俗語說“癩蛤蟆想吃天鵝肉,癡心妄想”,這是對圖謀不軌的最佳寫照。可吃天鵝肉并不是癩蛤蟆的本性。癩蛤蟆居住在潮濕的草叢和泥地里,以甲蟲、蝸牛、蠅蟻等小生物為食,它的食譜里絕不會有天鵝這種高等物種的,癩蛤蟆與天鵝的糾纏完全是出自人類自作聰明的想象,最終它成為了滑稽可笑的形象。其實,真正想吃天鵝的是人類本身,只不過人類將自己的貪欲投射到動物身上,讓癩蛤蟆被莫須有地羞辱了一把。
人們談論此事都是語帶嘲諷、面露不屑的樣子。我聽到一些媒體評論員在用一種調侃的口吻在做點評,當然他們主要是批評兩個賊居心不良,并借此呼吁要提高公民的道德素養和改進對公共財物的保護等等。那只天鵝呢?即便談論起它,也只是將之視為起襯托作用的背景板,沒有人留意到它曾經歷的苦難,時間一久,不會再有人想起那一攤融化掉的腐肉。
人類是萬物之靈,是世界的主宰。我們勝于其他動物的地方在于會創造和使用工具。老虎和獅子能用尖利的牙齒和爪子撕碎獵物,我們則用子彈和匕首擊倒對手。老鷹和大雁可以在云層穿梭,我們則能借助飛機和熱氣球在天空飛翔。我們崇拜猛獸的勇敢和威嚴,也為鳥類的自由飛行而著迷。可惜它們離我們太遠,不便于近距離欣賞,所以我們建筑了動物園。豺狼虎豹、蛇蟲鼠蟻被從自然界里捕獲而來,它們被局囿在裝有電網、鐵絲和玻璃幕墻的有限空間里,而我們則在欄桿外欣賞著它們的進食、便溺、交配。有人自認為是征服者而感到沾沾自喜,于是沖著籠子里的動物大聲嚷嚷:“蠢貨,有本事出來呀,來咬我呀!”他們并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安全是依靠了一些設備,如果在自然界里,只怕他們早已是肉食動物的口糧。當然,更多時候我們是在表現出人類的憐憫和慈悲:我們理解失去自由的痛苦,所以我們給動物設計了各種娛樂活動來舒緩身心;再用特意調制的營養品和飼料將動物喂養得胖乎乎的,以此來證明人類的善意和愛心。
人之初,性本善。這是個很多人都明白的道理,然而有人卻不愿將這份善良贈予動物,尤其是鳥類。和猛獸相比,鳥兒過于纖細和小巧,所以被欺凌是常有的事。就像那只黑天鵝,不過如平常般散步,卻無意招來殺身之禍,究其原因,無非是因為它很弱小,根本無力反抗貪念滋生的人類。
細看近幾年的新聞,發現黑天鵝被侵害的事件并不少見:2017年3月,揚州市瘦西湖公園內,一個游客不僅腳踢黑天鵝,還踩碎了兩枚天鵝蛋;2017年2月,泰安市泰山天鵝湖景區5枚天鵝蛋被盜,導致黑天鵝夫婦絕食;2015年12月,湖州西山漾城市濕地公園2只天鵝和5枚天鵝蛋被盜……
在芭蕾舞劇《天鵝湖》和電影《黑天鵝》中被引喻為機敏、充滿反抗精神的黑天鵝在現實中卻成為了受害者,是創作者誤解了黑天鵝的真實形象嗎?依我之見,并不是。城市里的公園需要有動物的點綴,所以引進天鵝來飼養是常有的事。黑天鵝繁殖數量多,當然成為了關注的重點。正如小說里的情節一樣,美麗的角色往往很容易招致邪惡的垂涎,黑天鵝的靈動與優美同樣也引來了竊賊的注意。
何止是黑天鵝,許多鳥類也都面臨著危險的境遇。
春節過后,一個溫暖的下午,我在江北大道散步。一棵枝繁葉茂的大樹下面有一個魁梧的男人拿著彈弓瞄準了樹上的某處。樹梢上傳來了鳥兒歡快的鳴叫,高高低低、細細碎碎地交織在一起,仿佛一首奏鳴曲。不用猜也知道那男人想做什么了。我站在一旁留意了很久,那男人似乎很專注,盯著目標一動不動。我們有些膠著,像是在比賽耐心,最后我還是沒能堅持下來,只好離去。走出一段路后,我聽到身后傳來鳥群的一陣嘈雜聲,好像有撲打翅膀的聲音,但很快又安靜下來,這之后,再沒有一絲鳥兒的動靜了。我回頭望去,樹蔭擋住了視線,那男人好像不見了,我不知道他是否命中了目標,也不知道他為什么要這樣做。可終究那一樹的鳥兒是緘默了。
小時候就常看到調皮的男生用彈弓去打樹上的鳥兒。如果打中了,男孩們就歡呼一片,拿著受傷或者死去的鳥兒四處炫耀,好像完成了一件了不得的杰作。隨著年歲漸長,慢慢地男孩們不再打鳥兒,一則是因為接受了老師的教育,知道鳥兒對人類的益處;二則是后來能讓他們開心的游戲太多了,所以他們放棄了彈弓。真不知道為什么時至今日還有人喜歡打鳥取樂。是因為鳥鳴驚擾了他的美夢嗎?還是小鳥惡作劇將糞便拉在了他的衣服上?這二者似乎都不是很好的借口。我猜想,他們純粹只是為了娛樂而已。他們帶著不懷好意的笑臉,眼神里閃動著殘忍的光芒,猶如自然界的野獸一般注視著獵物,一旦時機出現立即動手。野獸是為了果腹才去捕食其他小動物,而他們是為了在獵殺中尋找快感。在人類的社會里,排遣休閑有很多種方式,不知道為什么他們非要選擇了與野獸相似的那一種。
我的工作是要在野外開展的。鄉野之地,應該如文學作品中描寫的那樣恬靜安逸,可這其中卻常摻雜了許多的不和諧。好幾次我在密林和沿江邊發現了一種網,是用透明魚線織成的,掛在半空中讓人難以察覺。魚線被繃緊后會變得如刀片般鋒利,不小心被刮到,必定會出血。幸虧請來當向導的村民及時發覺才使我免于受傷。聽他們說,這是當地人用來捕小鳥的,小鳥飛到半空中一頭扎入網眼里就再也無法逃脫。我打量著這些網,雖然是透明的,但細細看還是能看到上面暗褐色的污跡和一片片細細的絨毛;湊近了,還能聞到一陣腥臭的味道,這和清新的自然氣息是那樣格格不入。
前些年我到一個縣城出差,一條江水連接了各個小村莊,村道蜿蜒在山間。沿著江岸走,一路都掛著網,如果不是一團團不同顏色的羽毛在微微抖動,不會有人留意到這無形的殺器。抬起頭,立即看到一只死去的小鳥,它張著嘴,一雙黑黑的小眼睛瞪得圓鼓鼓的,一副驚愕突兀的樣子。這樣死去的小鳥有很多,它們小小的身軀不再動彈,變成了懸掛在半空中的一個個黑點。向導說,每年入冬和初春的季節有很多小鳥打江上飛過,這里每天都能纏住不少鳥兒。被網住的鳥吱吱地叫著,不停地扇動著翅膀,但是越用力就纏得越緊,漸漸地叫不出聲來了,只能偶爾撲騰幾下。傍晚時候拉網的人會來查看,死了的鳥被扔在地上,晚上野狗山貓會來叼去吃了;還活著的被扯下來關進籠子里賣到夜市去。一只小鳥價值一元錢。
人類總是喜歡將自己幻想為鳥:我們渴望插上鷹隼般強有力的雙翼,這樣就可以翱翔在天空之上;我們希望能擁有黃鶯似的悅耳歌喉,這樣就可以打動聽眾的心房;我們期待像天鵝那樣對愛情忠貞,一生一世真誠到老。于是我們用各種藝術形式來贊美、歌頌它們;而另一方面,我們又借助了由“智慧”所產生的工具來捕抓它們,褪去羽毛、折斷雙翅,又或者偷走它們的卵和幼雛,讓它們在痛苦和絕望中哀嚎甚至死去。慈悲和冷酷,憐憫和殘忍,這是人類情感中的對立面,一方面出自貪婪的野心,另一方面源于潛在的人性。我們就在矛盾中彷徨苦悶,不得安寧。希區柯克的電影《鳥》中描繪了一個看似不可能發生的故事:平日里溫順可愛的鳥類對人類發起了一場又一場襲擊,它們尖利的爪和喙讓人類倉皇失措無所遁逃。當人們藏身在電話亭和閣樓中時,那種恐懼和失落能否讓你想起被囚禁在籠中的鳥兒?希區柯克沒有在電影中揭示鳥群為何會失控,人類又是怎樣脫離困境的,但最終我們都知道:在突如其來的災難當中,人類和鳥類一樣都是如此弱小和無助。我們是否可以設身處地想象一下,如果將鳥兒承受的劫難施加于自己身上,那可會是一場歡愉的經歷?
五象湖公園里有好多水禽:黑天鵝、白天鵝、鴛鴦、野鴨。水鳥們并不怕人,常飛到木棧道上歇腳,有時游人湊近來跟它們打招呼,它們就會轉動著小眼睛歪著脖子左右打量來人,樣子十分逗趣。三月份的時候黑天鵝增多了,是一只小寶寶,那時它還沒有披上黑袍,還是灰不溜秋的樣子。它浮在湖上,兩只腳蹼不停地拍打著水面,努力地跟在父母身后。大天鵝緩慢地游著,偶爾回過頭來望一下小天鵝,如果孩子游得慢了,大天鵝就會彎下頸子,伸嘴去啄它一下。太陽底下常常傳來天鵝高亢清亮的叫聲“昂昂昂”,不知道這是天鵝歡樂抑或悲傷地呼喚。權當它們是在開心地歌唱好了,至少在這個溫暖的城市里它們還沒有受到傷害。
朱光潛先生說:“殘酷的傾向,似乎不是某一個民族所有的,它像是盲腸一樣由原始時代遺留下來的劣根性,還沒有被文化洗刷凈盡。”我們的文化和教育,較之以前早已是大步地前進,也該把那種殘忍的劣性拋棄了。不論是圣桑的《天鵝》還是巴甫洛娃的《天鵝之死》,都不應當是無奈的絕唱。
責任編輯?? 練彩利
特邀編輯?? 張??? 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