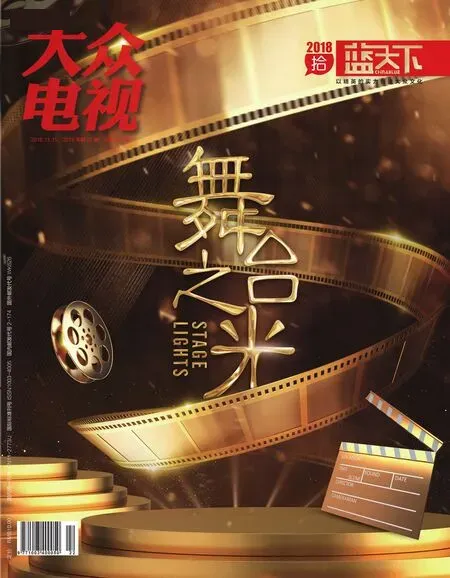中國村落第二集 建構
總導演 撰稿/夏燕平


一
依山傍水,錯落有致。中國的村落,于風景如畫之中充分體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宇宙觀:『天人合一』。
安徽黟縣西遞村村民胡時濱:“通過天井啊,能夠看到外面的萬千世界。飄浮過來的白云啊,太陽啊,月亮啊。你坐在這個廳堂上面,會很愜意的。
但是它為什么不叫天窗叫天井呢?告誡住在這個房子的人們,絕對不能像井底之蛙那樣,外面的世界大得很。”
中國村落的建房設局,就有很多這樣的講究。
不過,第一步要講的,便是選址。選擇如桃花源一般的宜居、生養之地。所以,能僥幸留存至今的古村、古鎮,無一例外,都可以、或者早已經成為旅游觀光的景點。
依山傍水,錯落有致。中國的村落,于風景如畫之中充分體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宇宙觀:“天人合一”。
因勢象形,不喧賓奪主,依勢造景,不橫行霸道。自然的材料,自然的開展,一個個村落仿佛是從土地上自然地生長出來一樣。
不過,村落的最初建構,并不完全是自然而然,而是花了一番心思的。這番心思,叫做“風水”。

中國村落文化研究中心教授胡彬彬:“它在形成這個建筑之前,第一件事就是要去看我要建的建筑跟自然山水之間的關系,跟我們當地勞作的、賴以生存的土地之間是一種什么關系。它的最基本的一個通識的考慮是什么呢?那就是,人、建筑和自然一定要協調,人只是自然里的一份子,而并非凌駕于自然的。”
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一峰獨聳,這叫華表;兩山對峙,日月捍門……其實就是,背有大山,面朝沃野。所謂“風水”,就是一處特別適合“成家立業”的地方。
安徽黟縣西遞村村民胡時濱:“風水學用現代話講不是迷信,它是研究與自然的關系。做到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比如坐北朝南,有利于采光,前面有水,有利于調節氣候,北面有山,可以擋住西伯利亞來的寒流。”
同濟大學教授阮儀三:“我們現在風水異化了。認為是賺錢啊、發財啊、致富啊,這種是不對的,它是人和大自然和諧相處的一種默契,心靈的感受,一種跟當地的小氣候和大氣候形成的交匯。”
“風水”,是中國古人通過觀察自然萬物的變化而總結出的建構法則,是一種更讓人適宜居住和生產的科學,使中國人在“天人合一”的思想統攝下認真地生活。
元朝至正九年,公元1349年,浙江武義縣的俞源村,剛剛成熟的莊稼又遭受了一場洪水的襲擊。
浙江武義縣俞源村村民俞俊浩:“我們俞源村以前常常發洪水,也有人發瘟病。”
村里人請來了一個叫劉基的風水師。
風水師認為此地溪流太直,容易將村落里的氣數泄盡,于是將溪流設計成“S”形,整個村的格局看起來像一幅“太極圖”。
浙江武義縣俞源村村民俞俊浩:“我幫你改個太極,你這個河流太直,住不起人。”
說來稱奇,曾經飽受旱澇肆虐的村子,從此安然無恙,富甲一方。這個劉基就是后來輔佐朱元璋的明朝國師劉伯溫。
浙江武義縣俞源村村民俞俊浩:“后來瘟病也沒有了,洪水也沒有了,再后來越來越發展越來越發展,幫我們俞源村排了一個輩分:敬衛恭儀像,權衡福壽昌,榮華成禮義,富貴隨賢良。排了一個輩分,我現在是二十四代。”
其實,這是建立在科學基礎上的水利改造工程。“S”形的溪流意在使河道變長,容積加大,減緩流水的速度。同時


建村設寨,水是命脈。因而,水,也是財富的象征。為了鎖住財富的出口,人們在這里種樹、蓄水、造橋、供奉……以期讓水流、也是財富緩緩地流出。劉伯溫借黃道十二宮之說,把環繞俞源的山崗變成了“神山”,禁絕砍伐山林,消除了山洪下瀉、溪流泛濫的誘因。又在村里按北斗七星狀挖了七口池塘,作為蓄水、抗旱、救火之用。
整個村莊表達了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堪稱中國古村落生態建設的典范。
中國的村落,風水無處不在。而最為緊要的風水所在,是我們和村莊的初次相見,這便是村口。村口,常常也是水口。
浙江武義郭洞村。四周層巒疊嶂,只在這里有一道狹小的出水口,這讓山坳里的村莊,看起來猶如洞天福地。
建村設寨,水是命脈。因而,水,也是財富的象征。為了鎖住財富的出口,人們在這里種樹、蓄水、造橋、供奉……以期讓水流、也是財富緩緩地流出。
浙江武義縣郭下村黨支部書記何曉宏:“我們邊上的樹木,龍山上的樹木,為什么有這么好呢?因為我們祖宗一直流傳下來有和嚴格的家規家訓。”
浙江武義縣郭洞風景區經理何惠:“你上山撿柴火者就要拔其指甲,如果砍小樹者就要剁其手指,砍大樹者就要剁其手臂,聽起來是非常殘酷,但的確是把我們整個龍山完整地保護下來了。”
層層疊疊的古樹圍住了郭洞村的水口、草木、橋梁、廟宇……有識之士選址建村,必重視森林和自然的屏障,以及由此而組成的美麗風光。
中國村落文化研究中心教授胡彬彬:“這個就是敬畏,因為人,過去我們先人有一個非常樸素但是非常科學的道理,就是人是自然衍生出來的這樣一份子,所以,人和自然的關系,人是從屬于自然的。”
中國的村落,無論大小,不避奢儉,都會因地制宜,設置水口,它是一個村的“形象代言人”。是他們交流、休閑的公共地帶,是他們引以為傲的故鄉地標,也是他們安放鄉愁的永遠空間。
許多有歷史的大中小城市,它們的最初,可能就是幾戶人家,一個小村。
小到一個家,家的門口;大到一座城,城的入門,都有它的水口所在。
風水學的源流,可以追溯到兩晉時文學家郭璞的身上,他在其著作《葬經》中提出了“藏風得水”之說。不僅有立言,浙江溫州古城的選址布局,便出自郭璞的手筆。
晉明帝太寧元年(公元323年),文學家郭璞流落浙江溫州,郡守請他設計溫州城。今天的這一處公園,江心嶼,就是當年郭璞指定的溫州城水口所在。俯瞰溫州的入海口,有三座島嶼鎖鑰江海之中,這是一個天造地設的絕佳水口:它們可以緩沖雨季時上游下泄的山洪,也可以阻擋海潮對沿岸的沖擊。一方城池,永保安瀾。
因為地形、氣候和材料的不同,同是客家,卻也是一方水土,一方民居。形成了圓形的土樓、半圓形和方形的圍屋。
二
中國歷史上數次由北而南的大遷徙,形成了漢族人民中一個特有的族群:客家人。也因此創造了一種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觀:客家民居。
既為客家,當然不能喧賓奪主,選擇的定居點多是山高水遠之地。為了能夠抵御野獸、盜賊的騷擾,為了能夠完成聚族而居的需要,一種巨大的可以容納百人甚至千人居住的單體民居建筑,在中國東南沿海蔚為壯觀。
福建龍巖市永定區振成樓林日耕:“我們在河南一代,避難,往南遷,當地南方這邊,居住著土著人,當地的土著人因為人口少、土地多,你來了不反對,叫客人,叫習慣了才叫客家人。”
福建漳州南靖縣曉春樓張民泰:“為什么土樓它可以耐受到這么長的時間呢,關鍵是土樓它是用生土挖起來建造的,這個生土不但不會風化變質,而且它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牢固。”
福建龍巖市永定區振成樓林日耕:“客家土樓方形的土樓歷史上最早的遺址1200多年。圓樓歷史才不到600年,常有人提問,客家的方樓好好的,你為什么改圓樓呢,方樓不好嗎?方樓和圓樓有很多差別,圓樓可以抗震,方樓不抗震。因為圓樓下面大,上面小,上面傾斜,地震倒不出去更倒不進來。第二個,圓樓可以防風,方樓不行。方樓壓力大,大風一來方樓一推就倒掉了,圓樓沒有受力面。”

因為地形、氣候和材料的不同,同是客家,卻也是一方水土,一方民居。形成了圓形的土樓、半圓形和方形的圍屋。

廣東河源市和平縣博物館館長吳更生:“我們客家人都是從福建、梅州遷徙到我們這里,我們和平就是這樣,按照客家的建筑,都是圍屋啊全圓的土樓啊,只有我們和平才有四角樓。”
廣東和平縣林寨古村村民陳仰天:“一個是潮汕文化,一個是廣府文化,一個是西方文化,還有更重要的是我們客家文化。它的這個四角樓的特點,一它起到防洪的作用,第二呢,防那個兵匪,這個地方官宦人家多經商的有錢,所以它有炫富的那種感覺,你建的房子這么好,我建的比你還要高大,還要更堂皇。”
盡管造型各異,但功能如一:防備外敵。
廣東五邑大學教授張國雄:“……到了這個地方來以后,它一定是結合了三省交界地區的山區的地形,和它作為一個外來的人口,在當地為了自保聚族而居,形成了這樣一種封閉性的民居形式。”
不僅是客家民居,防御,是絕大多數中國村落的共同要求。最確鑿的證據莫過于長城。
是的,長城不是村落。不過,長城不是孤立的一道邊墻,它的依托是從山海關到嘉峪關,與長城唇齒相依、共同承擔防御任務,而修建的一系列軍事堡壘。其中,尤以明朝設置“九邊”軍鎮時期最為繁重。這九大“軍區”分別是:遼東鎮、薊州鎮、宣府鎮、大同鎮、山西鎮、延綏鎮、寧夏鎮、陜西鎮、甘肅鎮。
清朝以后,沒有了游牧民族的威脅,這些個屯兵城逐漸荒涼,其中許多,成為了老百姓居住的村落。當年的軍屯,今天依然還是農田;當年的城墻,今天仍舊還是屏障。
即便不是軍事重鎮,沿線的商業城鎮,巨賈大戶,一樣是城門城墻,壁壘森嚴。
三
當一個不需要設防的村莊,便會有更自由的想象和寄托。
浙江永嘉蒼坡村已有八百多年歷史,今天依然存留著宋代的寨墻、古道、老房……不過到此一游者,往往“心不在焉”,他們重點是奔著“文房四寶”而來的。
不是說這個村里展示著古玩的筆墨紙硯,而是這個村的建構,是按著文房四寶的形制和布局設計的。
這條筆直的石板街道縱貫全村,盡頭指向筆架山,這是筆;街道兩側的池塘,是為硯;池塘邊的巨型石條,這是墨了;而整個呈正方形的村子就是一張鋪展開來的紙。

以筆墨紙硯的形,作為村落設計的魂,無疑是在表達蒼坡人的理想追求:讀書致仕,心懷天下。他們的關鍵詞是:“一等人忠臣孝子,兩件事讀書耕田。”
巧合的是,在后來的八百年里, “讀而榮身,耕而致富”者,蒼坡村代有人出。
楠溪江沿岸,坐落著許多個這樣的優雅村落。它們不設徽派民居的高墻和精巧,沒有晉中大院的豪華,沒有閩西土樓的霸氣,當然,也沒有了這些建筑的封閉和局促。
它們是敞開的房屋,低矮的圍墻,看得見青山和田野;房屋之間的間距,讓每棟房子保持獨立的形體和品格,村落因此顯得更為疏朗。
當然,它們更重要的特點是,耕讀傳家,詩書繼世。所有的這些村落,都可以如數家珍,排列出歷史上列祖列宗的輝煌。
浙江永嘉縣蒼坡村村民李三珍:“當時出了好多名人,我們宋朝的時候,是一個駙馬,駙馬有九個兄弟,他有三個京都當官的。”
浙江永嘉縣芙蓉下村黨支部書記陳曉芙:“司馬帝大屋總共有108間房子,都連在一起的,前前后后是三進。在宋朝的時候,以前是有18進士,三元連中那就是狀元。我們芙蓉村出過一個狀元,其他都是進士。”
這些村落融合了楠溪江的清純靈秀,賦予了文人雅士的儒雅散淡和農家的樸實坦誠,構成了和諧寧靜的鄉土建筑風格。
四
對于不同凡響的人事,我們喜歡給他們編排一些個“天生異象”。村落也未能免俗。其實,許多村落在神奇的“風水”說和世代傳說之下,就是一個個因地制宜、科學治理的生態典范。
遠方的雷崗山是牛頭,村口的兩棵大樹是牛角,這半月池和南湖是牛的胃,穿梭在家家戶戶門口的水圳是牛的腸,這家家戶戶,當是牛的身體了,牛要站立奔走,依靠的是這四座橋,這是牛的腳。
安徽黟縣宏村村民汪瑞華:“這是一種情感寄托。因為在古代農耕文化中牛是家中的寶貝,是家當,就把它說成牛。我們宏村它不是像我們現在有人講什么從開始到最后有一個整體規劃的,這不可能。因為古代的自然村,它是因形就勢、隨其自然發展起來的,說白了就是任何一個地方,建筑、規劃它是環境決定格局,形式追隨功能,金錢影響規模,文化提升品位。
我們是1131年來的,住在村后雷崗山臺地, 1275年因為用火不慎,把雷崗山腳上叫十三樓燒了,1276年就把東北大概一個三角地帶建了。1403年到1426年有一個短期規劃,就是一個叫胡重的女人,她丈夫出去當官了,宗族里因為她有才華,就讓她來行使丈夫權利。就帶著全族人花了23年,一個是做了一個鐘池,第二在鐘池前面一個半圓形的河灣,因形就勢隨其自然,挖這個半月塘。第三把村中的一條1200多米的老河,改成今天我們看到的這個人工水系叫水圳。”
這種穿梭到家家戶戶的水圳,是一種古代的自來水供給系統。后人把它比作是宏村的“牛腸”。
六百多年前,宏村人在村落上首攔河建壩,在原來的河灘上擴建村落,利用河道沖毀后變成的小溪,讓它穿堂過屋,建立了我們今天看到的水圳。
水圳沿途建有無數個小渠踏石,飲用、浣洗都在這“牛腸”里,每天早上八點之前,“牛腸”里的水為飲用之水,八點之后,村民才能在這里洗滌。
水圳九曲十八彎,流過了家家戶戶的門口之后,經月沼,入南湖,灌農田,澆果木,最后匯入繞村的河流。
安徽黟縣西遞村村民胡時濱:“水渠修通之后,隨著村子越來越大,人越來越多,一直到萬歷年間,當時姓汪的一共有十七個,頭頭面面的人物,大家一起聯合倡議,就把村子原來南面的,一些水沼啊、水塘啊、水渠啊,以及一些深腳田把它通過深挖連成一片,仿造西湖的平湖秋月,把它修成南湖,宏村水系自此基本成形。”
六百多年前,宏村人在村落上首攔河建壩,在原來的河灘上擴建村落,利用河道沖毀后變成的小溪,讓它穿堂過屋,建立了我們今天看到的水圳。

安徽黟縣宏村村民汪瑞華:“功能,風水,景觀,它為什么挖成一個類半圓的,因為古代講大自然只有規律沒有規矩,你太圓太方叫太過規矩,這個直線叫剛線,弧線叫柔線,叫剛柔并濟。而且造型上像硯臺裝水的一塊,叫硯池,表示文運昌盛,前面有山,那邊看過來也有山,蘇州園林怕我們一覽無余,要做個墻擋一下叫障景,像文學的欲揚先抑,我們全是高墻,你看幾米十幾米高,它要是不留個口,你可以想象一下,沒有遠山,你這個湖再美,因為被房屋包圍的水面,根本就沒有情調,你看現在它留了一個口,要是不留一個口,風水上不允許的,叫窒息,就是不通氣。現在留了一個口,風水叫氣口,環境叫對流,美學叫留白。”
假如你要“按圖索牛”,你是拼不出牛形圖來的。
所謂牛形的村落,其實是一種勤勞致富,耕讀傳家的心理暗示。果然,宏村從此人事興旺,走過了六百多年的風光。在無需牛耕的時代,這頭“牛”,依然“牛”。
水圳除了飲用、洗滌、灌溉,還可產生水力、用于防火;調節小氣候,凈化空氣、美化環境。
在許多建構有序的古村落,都可以看見這樣的人工水系。
不過,有一種人工水系,是個例外。
浙江的開化縣所處,是錢塘江的源頭。引源頭清水筑塘養魚,是這里的奇觀,更奇的是,有的人家把魚塘筑在了家里。
浙江開化縣禾豐村村民汪良清:“有這個房子的時候,他就挖了這么一個魚塘,當時造這個房子的時候,它造地基呢里面挖出了一股泉水,所以開始慢慢地把它搞了一個塘,再養魚,那個水還是不夠,所以再把河里的水引一部分進來,再從這里出去。”
清水養魚,只是喂食青草,生長期長。生長期長了,主人往往不舍得食用,有的魚已經養了二十多年了。
以這樣的方法引水,用這樣的清水養魚,想是漁翁之意不只在乎魚了。


『炊煙會從田野上裊裊升起,而在人的視野里卻見不到任何房子』。『這樣的土地,發揮著雙重職能—— 地下住所,地上良田』。
五
“炊煙會從田野上裊裊升起,而在人的視野里卻見不到任何房子”。“這樣的土地,發揮著雙重職能——地下住所,地上良田”。上世紀三十年代,域外的地理學家這樣描述他們在中國的驚人發現。
其實,中國的窯洞建筑,四千多年前就已經存在了。
河南陜州區曲村村民李貴良:“這地坑院的歷史從原始社會就開始了,就是地坑院了,一直就住到現在,姥爺、老姥爺都住這地坑院里。老祖先就是種地,種苞米小麥,主要是依靠種地,現在有果樹,有桃樹、葡萄樹、梨樹、柿子,現在就是經濟作物多。”
《史記》和《詩經》都記述了周朝的奠基人,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帶領族人遷徙到陜西的岐山下,掘地挖穴,重整基業的故事。
黃土高原冬季十分寒冷,植被稀疏,缺乏足夠的建筑用材和取暖用材。但黃土的松軟度和多孔性,使其容易開挖并具有良好的保暖性能,先民們據此創制了這種冬暖夏涼的居住方式。
大多前來觀光的外人都會問到,他們不會掉下去嗎?院子里會不會積水呢?

房檐上這一圈青磚砌起的欄馬墻,就是為了防止地面雨水灌入,同時保障了地面勞作和兒童玩耍的安全。
在地坑院中心,設計低于周邊約三十厘米,并在偏角一處挖掘四到六米深,直徑一米左右的水坑,用來積蓄雨水和污水排滲。由于地處相對干旱地區,這樣的防護設施,足以抵擋雨水的侵襲。
就地取材以及環境、氣候和技術的因素,是村落建筑形式的重要成因。但最終決定建筑形式非此不可的,則是社會文化的因素。這種社會文化的因素,便是先民們精神的追求和智慧的結晶。
六
在土地稀少的地方,石頭支撐起一片王國。
天津薊縣西井峪村村民周志華:“人家磚房啊,和咱們石頭房不一樣,咱們這個石頭房呢冬天暖和夏天涼快,經過1976年唐山大地震,我們這個連房帶墻都沒有躺的。(沒有水泥為什么還這么牢固呢?)沒有水泥,這種石頭呢,是壘的層次感,你要不說這個石頭吧,地震的時候它是搖晃是吧?它一搖晃這石頭往里去了,是吧?再一回來,這石頭又回來了,原位。如果你這個要是使水泥的話,假如說咱們這兒使的水泥,它一搖晃就裂口了,再一搖晃就酥了,就躺了。”
500年前,民族英雄于謙,以石自喻,托物言志,寫下了廣為流傳的《石灰吟》:“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閑;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500年間,26代于家后裔在這里以堅韌不拔的品格,開山鑿石,用石頭書寫了一部村落史詩。
這些建筑,大都以天然石料為基礎,用干打壘的技術,僅用雙手使塊塊石頭之間錯落咬合,拔地而起。
始建于明萬歷九年的清涼閣,下兩層為全石結構,不挖地基,由一塊塊巨石壘砌,有的巨石重達萬斤。
河北井陘縣于家村村民于翠田:“第一個特點它沒有根基,第二個特點,沒輔料,第三個特點呢,它的東南西北方位,四正,第四個特點呢,石頭你橫看它也并不成線,豎看也不壓個縫,一塊石頭一堵墻,一根柱子一匹梁,一塊石頭一平臺,一塊石頭搭成房。完全用石梁、石柱、石門、石窗、石龕、石欄、石頭臺階,雖然它已經過了436年的風侵雨蝕,顯得吧,鬼斧神工,它就聳立在我們村的村東首。”
石頭街道、石頭房墻、石頭四合院、石頭樓閣、石桌石凳、石碾石磨、石橋石欄……于家村,實打實的石頭村。500 年前,民族英雄于謙,以石自喻,托物言志,寫下了廣為流傳的《石灰吟》:『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閑;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河北井陘縣于家村村民于翠田:“咱們這個村子啊,就是于謙的長孫于有道逃難來到這兒,在成化年間,也就是530來年吧,那時候這里是一片深山,他就與木石居,與鹿豕游,開荒種地,在這兒生了五個兒子,我們現在全村啊就分五鼓,現在已經發展到了六十二代,四百戶。現在在家居住的是一千六百口人,這個村百分之九十五是于氏家族的人。”
在現代建筑材料豐富的今天,于家村的人們依然愿意使用石頭疊砌自己的家園。除了為延續于家村的民居特色,更在于,這塊塊壘石,仿佛篇篇錦繡文,這幢幢石屋,好像座座紀念碑,是對祖先、對民族英雄于謙的最好敬獻。
無論夯土圍墻、石頭壘砌,或者木頭結構,中國的村落都可以找到它的傳承。不過,眼前的這一幢幢碉樓,一時難以尋祖歸宗。
奇特的造型、先進的材料、混搭的裝飾,這種“四不像”的建筑,恰恰是中國村落建筑與近現代文明結合的成功示范。
廣東五邑大學教授張國雄:“廣東江門,五邑僑鄉這個地區,他是大量人開始往外走,尤其是19世紀60年代以后,50年代60年代大量地向東南亞、向北美、向大洋洲移民。那么移民以后,他們把海外的文化傳播進來了,五邑僑鄉這個地區,他的鄉村景觀發生了很明顯的一種變化,一層樓那種傳統祖屋,低平整齊的那個主屋的情況下,在村后開始出現點式的別墅、碉樓,它的建筑材料、建筑技術都是從海外來的這么一個情況,所以這個啊它又是移民把海外的建筑文化帶到了五邑僑鄉。”
奇特的造型、先進的材料、混搭的裝飾,這種『四不像』的建筑,恰恰是中國村落建筑與近現代文明結合的成功示范。


廣東開平縣僑鄉李日明:“當時的華僑是很愛國愛鄉的,他們好多華僑啊,在外面賺了錢以后啊,就回來光宗耀祖,建設自己的家鄉,建這個碉樓,他希望以后啊,年老的時候啊,就回到家鄉來。”
四川丹巴藏羌民族的碉房,是中國建筑“疊石奇技”的最早見證。
據古遺址和石棺葬墓群的發掘,早在5000年前就有土著先民在這里生息繁衍,并掌握了較高的石砌墻技術。
面對這幢幢形似堡壘的建筑,人們首先想到了防衛的功能。確實,丹巴碉樓在歷史上和戰爭有著密切的關系,并據此起到了保護藏、羌人民利益的重要作用。
不過,它的出發點本不在此。
這種“依山居止,累石為室”的建筑,漢書稱之為“邛籠”。“邛”是藏地本教崇拜的一種大鵬鳥,邛籠的原始形態是用以表達“邛鳥”崇拜的祭祀性建筑。
至于后來的這些民居碉樓,初衷也不為防御,而是因為生育。
丹巴村寨的居民,凡生一子,必要建立一處碉樓,這樣孩子才能得到保佑成長,孩子每長一歲,碉樓就要加修一層,直到十八歲。千碉之國,那就是千家香火。
今天,人們已不再建碉,但是在房屋的頂部,都有一個四方形的帽形頂層,代表著建造高碉的位置。四角呈月牙形,角頂安放著白石,這是諸神的象征。

建構起這些家園的,是村落的每一幢房子,每一個布局,每一處設計。這建構里,包含著日月星辰、山川河流、風雨雷電、花草樹木,更有,歷史文化和風土民情。
所以,放眼望,我們仿佛看見,這一座座碉樓就是一座座佛塔,這一幢幢民居就是一幢幢廟宇,它們象征著眾生匍匐大地,仰望天空。
中國村落文化研究中心教授胡彬彬:“我們說中國傳統村落,是最能代表中華民族的歷史建筑文化,因為這些建筑,它有非常明確的地域性和民族性,長江以南講的是徽派建筑,你到福建看土樓,你到云南去看它那個竹寮子,你再到湘東地區,去看府第式莊園,到河套平原去,到黃河走廊里去,它不是這樣的。你看苗族的建筑,漢族人把它稱之為飛檐,但是你到苗區去,沒有人說是飛檐,說是裾檐,裙裾,那個線條非常優美。它的審美特征非常的多樣化,非常的具有民族個性。正是這種文化的多樣性,它的獨特性和它的特質性,準確地講,所以我們過去常常說的有一句話叫做,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村落的建構,受制于地理,但因為它是人類在生活中重要的角色,而使村落逐漸演變為聯系歷史與未來,原始與現代一個文明因子。
天地之間,中國人用自己的觀察方法和智慧,總結了四時與百物的規律,并據此,營建著自己的家園。
建構起這些家園的,是村落的每一幢房子,每一個布局,每一處設計。這建構里,包含著日月星辰、山川河流、風雨雷電、花草樹木,更有,歷史文化和風土民情。
中國村落,在“建”與“構”之間,生養著一代代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