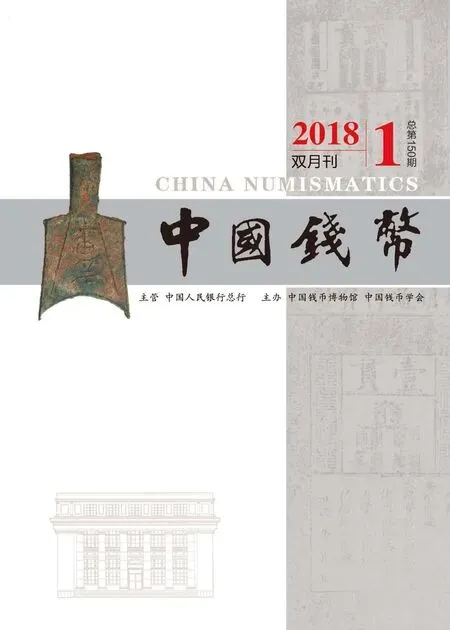東北九省流通券述評
董 昕 (遼寧大學歷史學院) 毛 帥 (河南信陽農林學院)
1945年8月9日凌晨,蘇聯軍隊攻入東北地區,短短數周占領東北全境。日本投降前夕,國民政府一方面派員與蘇俄談判、交涉;另一方面則籌劃接收東北地區。9月底,國民政府發布由曾擔任中央銀行副總裁的張嘉璈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東北行轅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負責對東北地區的經濟接收與金融政策規劃。在經過反復思量,向多方征詢意見后,張嘉璈決意發行東北九省流通券,東北境內的一切稅賦繳納與資金往來、商業貿易等,皆以流通券為交易單位,法幣則不許流通于東北地區;同樣的,此流通券也不準在東北以外的地區使用,成為一種區域性貨幣。
對民國時期貨幣的研究,關于法幣的研究著作和論文較多,而東北區域的貨幣,特別是對東北九省流通券的研究相對較少。戴建兵的《淺論抗日戰爭勝利后國民政府對戰時貨幣的整理》[1],對抗戰勝利后東北地區的貨幣整理進行了介紹。潘連貴的《中央銀行東北九省流通券個案研究》[2]對東北流通券的發行情況進行了介紹。在論著方面,一些涉及東北地區的貨幣金融史著作中,如畢鳳鵬主編的《中國東北地區貨幣》(中國金融出版社1989年版)、朱建華主編的《東北解放區財政經濟史稿》(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等,對東北九省流通券的發行與流通情況亦有簡要介紹。此外,該券的發行是在東北光復后,由東北行轅經濟委員會主持發行的,從對于主持者張嘉璈的相關研究中可略窺東北九省流通券發行的意圖及行使與流通情況,如(日)伊原澤周所著的《戰后東北接收交涉紀實—以張嘉敖日記為中心》(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等。
一 東北九省流通券的籌發
自九·一八事變始東北全境淪陷后,直至抗戰勝利前,東北境內流通的最主要的幣種是由偽滿洲中央銀行發行的偽滿券。偽滿洲中央銀行成立于1932年,依據同年6月頒布的《舊貨幣清理辦法》,強行收兌了此前市面上流通的各種貨幣。其中,東三省官銀號、邊業銀行和中、交、奉行發行的各種貨幣由偽滿洲中央銀行直接收兌,其它幣種由發行機構自行清理。1935年6月末時,對上述舊幣的回收率已達到93.1%,到該年8月,回收率進而達到97.2%[3]。至此,偽滿券已完全在東北地區貨幣流通中占據主體地位。偽滿券與日幣等值流通,也不可避免地淪為日幣勢力的附庸。
在偽滿洲國存續的后期,受第二次世界大戰戰事的影響,偽滿券的發行額不斷攀升新高。尤其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偽滿券的發行額度更是一日千里,1945年7月時的發行額增至80余億元,比1932年時的額度增長52倍。及至日本戰敗,最后發行額高達136億元[4],為偽滿央行開業初期發行額的90倍。同時,偽滿券的印制也屢有變化,前中期均在日本境內印制,為便于發行,于1944年3月改在偽滿政府印刷局就地趕印,以求簡求快,并由原來的七色印刷改為三色印刷。同時,一角、五分的硬幣變為了紙幣;其后,一元的紙幣還出現了無號碼券。隨之,東北地區的金融形勢也陷入高倍通貨膨脹中了。
在偽滿洲國時期,東北地區的行政區劃由原來的奉、吉、黑、熱四省增為19省。抗戰勝利后,東北地區的主權重新回歸國民政府手中,國民政府意將東北地區重新劃分為九個省區,大體上是“將偽滿兩省并為一省,意在便利接收,減少紛爭”,以便利軍事防御與調度,這也成為1947年最終方案的雛形[5]。在著手開展對東北各地的接收工作時,國民政府欲對金融行業進行專門整頓,并成立東北行轅經濟委員會,以為主管部門。
東北光復之后,國民政府如何接收經濟狀態、幣制都與關內迥異的東北地區,將東北與飽受戰爭損害的關內地區進行連接整合,頗為復雜且具挑戰性。加之當時東北的局勢呈現出不穩定的勢態,國民政府進入東北后的軍政開支急需大量資金,不具有先整頓金融,待金融形勢穩定后再發行流通貨幣的條件,因而執行了一邊整頓一邊發行的政策,以發行東北九省流通券(亦簡稱“東北流通券”)作為區域法定貨幣行使。財政部在呈遞國民政府行政院的呈文中稱,“茲查東北九省淪于日人亦已十四載,當地經濟與內地亦多不同。為適應當地環境起見,東北收復后流通之貨幣,似亦有參照臺灣辦法辦理之必要。茲擬由中央銀行發行東北流通券,為東北境內流通之法幣。”[6]1945年11月2日,國民政府正式公布了《中央銀行東北九省流通券發行辦法》,“泛凡東北九省境內完納賦稅及一切公私款項之收付,均使用之”;同日公布的《東北九省匯兌管理辦法》規定:東北九省與內地的匯兌業務,和東北流通券與法幣的兌換業務,僅能由中央銀行及其委托行經營[7]。時任經委會主任的張嘉璈在致財政部長俞鴻鈞電中稱,凡一切公私款項之收付,均可使用東北流通券。至蘇聯紅軍在東北所發行的貨幣,準與中央銀行發行的東北流通券等價流通[8]。
中央銀行長春分行于1945年12月21日開業后,即開始發行東北九省流通券,按照1:1的比率收兌原偽滿券。按原定發行辦法,東北流通券與內地的匯價,應由中央銀行掛牌公告。但在發行之初,中央銀行并未馬上對內地使用法幣與東北流通券的匯價正式掛牌,市場上的非正式價格在1:13左右。各地銀行也多按此比率收兌。
二 對雜幣的收兌
東北九省流通券得以正式發行以后,為統一東北地區行使的貨幣,并應付軍政機關的開支,需要收兌曾允許在短時期內使用的偽滿券和蘇聯紅軍發行的軍用票。同時,在東北九省流通券未正式發行之前,出關接收的國民政府部隊還攜帶并使用了部分法幣,也需要兌換為東北流通券。其具體過程大致如下。
1.對于蘇軍票的處理
對于東北區金融形勢的整頓,首先是從對蘇軍票的整理開始的。蘇軍票是蘇聯于1945年8月9日出兵東北后發行的,以支付駐東北各地的陸海空軍部隊所需的各項費用,亦與偽滿券等值使用,且其發行數額事前并未約定。至1946年6月才得到蘇方通知,共發行97.25億元,且沒有蘇軍票的票版與號碼。國民政府東北行轅經委會遂做出蘇軍票的初步兌換辦法:十元券及十元以下之小券,可繼續使用,另定收兌辦法[9];百元券即時停止流通并向指定銀行登記,繳存時準予先兌換一成的東北流通券,余做存款,另定兌換日期,唯此項存單可向中中交農四行配作押款[10]。
從1946年8月1日開始登記之日,大額蘇軍票即不準在市面流通,以免民眾將其脫手,換取物資,而引起物價上漲。因民眾對國民政府凍結蘇軍票的措施普遍心存疑慮,物價依舊上漲。而對于蘇軍票百元券的停用和登記兌付的期限之短,一般民眾也多有不滿。各地的同業工會亦向政府提出各種資金融通的辦法。后經中央銀行改以只收不付的方式收回此券,民眾才予以接受。東北行轅經濟委員會于同月31日發出布告:凡長春、沈陽、四平、永吉四市登記的蘇軍票自9月3日起,其余各地自9月5日起,總額五千元以下者全數兌現。其間,經濟委員會復電商財政部,所有登記的蘇軍票全數兌現,財政部亦復電表示同意。沈陽的金融機構中存有蘇軍票較多。至1946年7月底,沈陽各商業銀行的庫存現款約占存款總額的25%,而蘇軍票約占庫存總額之半;至于各國家行局的庫存現款,約為存款總額的12%,蘇軍票約占庫存的三分之一。沈陽是東北的金融中心,存款戶中軍政機關的比例相當大,地方當局為了穩定金融起見,對于當時的庫存蘇軍票,一律準向中央銀行兌換東北流通券;自8月1日起,凡是銀行存款,也可完全兌換流通券。同時,為了救濟不能利用銀行的小戶貧民,決定凡登記數額在千元以下者,可向指定銀行免息押借,其押借數額可特別提高,幾乎等于全額兌現。
從整體上看,東北各地對于蘇軍票的收兌工作較諸平漢京滬各地兌換偽幣的情形,迅速良多。但因先期登記收兌的僅為大鈔百元券,至1948年中,蘇軍票的登記總額僅為228153萬余元,兌付204551萬余元,余者多仍遺留在人民解放軍控制的區域,“聞在大連區域者最多。現有許多地區經常有拉據式的戰斗,因而登記之后未及兌換的,竟有兩億余元”[11]。
2.對于包封法幣的處理
1945年10月始,國民政府開始派出軍政人員出關接收東北。由于蘇軍禁止相關人員從營口和葫蘆島登陸,接收的先頭部隊只能由山海關倉促出關。因先頭部隊未能事先領到偽滿券以供使用,東北流通券又尚未發行,乃將法幣攜帶出關,按1:1的比率與偽滿券混同使用,購買副食等。嗣有關內投機商人見有利可圖,乃尾隨國民黨軍隊,用法幣套購關外物資。及東北保安司令杜聿明抵達錦州后,便開始使用蓋印法幣;已流入到市面的未蓋印法幣,由當地縣市政府會同各地商會登記封存保管,靜待處理。這些法幣即被稱之為“包封法幣”。
待東北九省流通券正式發行后,軍政府機關服務人員匯款至關內,依照的匯率是一元東北流通券折合法幣十三元辦理,在黑市上兩者的匯率也盤旋于十三元左右。但是,包封法幣的持有人很希望以1:1的比率兌換流通券,因為他們收來包封法幣時是按1:1的比率同偽滿券兌換的,而偽滿券與流通券是等值發行的。如按實際匯率,則無形中使包封法幣的持有者損失巨大。東北行轅經委會亦感到比率相差過于懸殊,擬定了新兌換辦法,于1947年3月12日電請財政部審議,請求將包封法幣兌換為等額的東北流通券,由中央銀行錦州分行代為收兌。財政部起初拒絕,在經委會以東北行轅的名義一再請求下,方于同年7月16日復電準辦。包封法幣在各地的數額為:錦州17818060元,錦西1037120元,興城1429115元,綏中2000萬元,合計4026萬余元[12],兌換所需費用由“蓋印法幣”收兌余額項下撥支。
3.對蓋印法幣的整理
1945年11月,東北保安司令杜聿明接收錦州后,鑒于關內不法商人利用法幣套購關外物資,于是決定發行一種加蓋“東北”字樣和司令長官杜聿明名章的法幣(包括部分關金券),限在東北與偽滿券等值行使,以維持金融[13]。東北各市縣政府設立臨時兌換所,負責發行及收兌事宜。
法幣的“蓋印”是由綏中和錦州兩處的印刷局完成的,所蓋鈔票號碼均有記錄。票面所蓋“東北”二字,在綏中加蓋的四周無邊框,在錦州加蓋的有邊框。這種由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指令加蓋印記的法幣和關金券[14]即被稱為“蓋印法幣”。據統計,共蓋印838579500元,其中五十元關金券18870000元,一百元關金券291104000元,一百元法幣券970000元,伍佰元法幣券83833500元,一千元法幣券102000000元,兩千元法幣券341802000元[15]。蓋印法幣的流通地域不廣,主要集中在錦州一帶。因面額較高,商民無法找零,錦州地方金融委員會利用光復前銀行所余的空白支票加蓋“一百元”的字樣,編列號碼,共制1200萬元,名曰“臨時流通券”,作為小額鈔票使用。在開始辦理蓋印法幣的存儲業務后,錦州地方金融委員會又用蓋印法幣將大部分臨時流通券收回。
1945年12月29日,中央銀行錦州分行正式開業。官兵商民即到該行,迫切要求將蓋印法幣兌換為東北流通券,以便使用。1946年3月7日,東北行轅經委會發布了《東北蓋印法幣存儲收兌辦法》:持有蓋印法幣者“得向錦州中央銀行立戶存儲”,憑存折可支取百分之十的東北九省流通券,余額在一個月后按月憑折支取5%[16]。按照這個收兌辦法,蓋印法幣的兌額需要十八個月才能提完。在東北經委會主任張嘉璈的主持下,擬定將兌清期限縮短至六個月。1946年6月時,蓋印法幣在中央銀行的登記總額已達7億余元,已總付流通券約1億元,余款擬在當年年底前兌清[17]。但兌付工作實際一直進行到次年6月,才基本完成。此項蓋印法幣的登記額為77035.55萬元,未兌余額僅為219萬余元。
4.對于偽幣的收兌
日本投降前的偽滿券發行總額為80.85億元。日軍戰敗崩潰時,發給各機關人員大量遣散費,偽滿央行庫存又遭蘇軍清理,致發行總額達136億余元。整理時,沒有采取在華中與華北對于偽中儲券及偽聯銀券采用的公開定期收兌方式,只是暗中收兌,由各地中央銀行只收不付。至1947年4月30日,已收回496120萬余元。5月間,人民解放軍在東北各地發動大規模攻勢,中央銀行鈔券運輸困難,為濟眉急,曾又動用一部分已收回的偽滿券,致預定之收兌計劃暫停。到8月31日,偽滿券收回額為664672萬余元[18]。在國民政府控制區域內的偽滿券,絕大多數已被中央銀行收兌。余者半數散落在解放區內,或許也有一小部分是由日人帶回國去了。
三 東北九省流通券的流通與通脹
東北流通券發行并流通一段時間后,使用區域漸廣。從東北接收后到1947年11月間,東北的物價雖然也在上升,但如同關內的物價水平相比,東北物價則保持著相對穩定的態勢。1947年12月時,較1946年12月的一般物品[19]平均漲幅為沈陽37%,天津69%,上海77%[20],沈陽物價的平均水平及漲幅可以說是低于關內的。但是,隨著戰爭局勢的發展,國民政府也不得不發行東北流通券大鈔以應軍需急用了。
至1947年冬為止,東北流通券的發行額僅為3100億元,且此間的東北流通券與法幣的比值并無硬性規定,僅以匯價相聯系,是為東北流通券發行與使用的前半期。隨著戰局的變換,1947年冬時,沈陽對外的海陸交通幾乎完全限于隔絕,至物價隨升,原有的鈔券面額便嫌過小,中央銀行庫存亦無法應付巨量需求。于是,為了吸收鈔券回籠,以緩和物價漲勢,并解救鈔荒,地方當局乃決定放寬匯兌管制,自1948年1月9日開始。同時,發生因東北“局勢危殆”而出現的游資內流問題,據天津金融局統計,僅當月的東北入關游資總額即達8508億元[21]。同年3月14日,財政部公布了《東北流通券行使及兌換辦法》,規定了流通券與法幣的固定比價,但這一比價是遠遠高于實際比值的,東北流通券的貶值速度甚至超過了進入惡性通脹發行階段的法幣幣值,可見東北流通券的貶值之快了。此為東北九省流通券使用后半期的明顯特征。迨至7月間,平津“各有一千億東北游資每日流入,而東北方面對此仍感不足”[22]。如以1946年1月間東北流通券的發行指數為100計,則1948年7月間的發行指數為2403508,其實際發行額也從13230萬元增至319185890萬元[23]。
東北九省流通券流通的第一階段,為以匯價關聯法幣之階段。
此階段中,其特點之一為東北流通券與法幣之間沒有硬性規定的比值。依當時經濟金融界人士的意見,比值可按市場價格定為流通券1元對法幣13元,隨經濟發展之趨勢調整。特點之二為關內外匯兌受到嚴格管制,流通券的價格不受法幣的直接影響。東北流通券發行后數月內,先行收兌蘇軍票,繼而調換蓋印法幣,其后又逐漸吸收偽滿幣,漸成松南各地之唯一通貨。但東北流通券發行之初,“有其消極的不刺激物價之效用,但無積極地穩定物價之基礎”[24]。
由于抗戰期間關內地區的經濟生產遭到巨大的破壞,物價上漲劇烈。相對而言,東北地區的經濟則保持著相對穩定的形勢。所以,東北地區物價在抗戰勝利后為全國物價水平最低的地區,發行東北九省流通券,使東北的金融態勢獨立于全國大波動之外,形成一種具有區域性質的貨幣體系,在發行之初,確實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沈陽零售物價指數環比月增長率的波動值明顯小于天津[25],達到了國民政府當局擬穩定東北地區局面的最初目的。東北與關內的津匯,由中央銀行隨時牌告。1946年9月16日,中央銀行公布,東北賣出津匯為流通券每元合法幣11元5角,買入津匯為流通券每元合法幣12元5角。自1947年5月12日起,買入津匯改為每元流通券合法幣12元,賣出津匯同前。依財政部頒行的匯兌管理辦法,由中央銀行指定中國銀行等國家行局負責辦理,凡工業匯款款項數額在流通券100萬元或商業匯款數額在流通券50萬元以上者,須報四聯總處東北分處核處后,方可結匯[26]。據統計,自1946年9月16日至1947年底止,從東北的匯出款項數額折合法幣為2036億元,匯入數額為22億元[27],出超嚴重。
早在1947年10月間,已有研究者提出:東北流通券與法幣的比價,若從東北經濟的發展著眼,則幣值“宜貶不宜提”,為計算簡便計,“一比十之定價最為理想”,并可以五百元以下之流通券充任“法幣的輔幣”。如是,則“可節省統一工作上不必要之消損”[28]多矣。但是,局勢的發展并未盡如人意。隨著東北解放區戰爭局勢的發展,東北流通券也不得不陷入以不斷增發來維持軍政開支的泥沼中。
局部內戰的爆發,也成了促成財政性發行的催化劑。1947年11月,人民解放軍發動冬季攻勢,北寧鐵路被切斷,交通不暢,東北物資供應奇缺。就在物價狂漲的時候,為了支付數額龐大的戰爭經費,東北地方當局仍向中央請求撥發巨量的東北流通券。自1947年11月起,東北的物價上升率開始超過華北地區,因軍事活動而增撥的東北流通券的信譽也開始一落千丈了。從解放軍的冬季攻勢發動后至1948年初,東北流通券已被戰事排擠集中到沈陽及長春周圍數十里地的范圍內,自動跌價。1948年2月27日,行政院電財政部,要求加速印制面額五千元與一萬元的流通券出關,沈陽央行應付未付的各種款項約3000億元,所存現鈔僅200億元,“供需相去懸殊”[29],東北流通券的發行與幣值實際上已進入失控狀態。
東北九省流通券使用的第二階段,為以比價關聯法幣之階段。
隨著發行額的攀升,直接導致東北流通券開始一天比一天貶值,其與法幣的比值也逐月下降。解放軍的冬季攻勢發動前,市面上流通券與法幣的比價尚能維持在官價1:10的比率左右;其后,則東北流通券貶值嚴重,中央銀行公告牌價的匯率(1:11.5)在戰爭期間根本無法維持,黑市交易的價格由法幣十元左右兌換流通券一元一路下跌到三至四元。此時的東北流通券,已不能平抑物價并保障人民生活的安定,在“關金化”后成為與法幣并行使用的幣種了,自然也逃脫不了屬于它的“厄運”。
面對金融形勢的惡化,1948年初,東北各界要員向南京政府提出整頓流通券的要求,并提出可允許法幣出關使用,使東北流通券“關金化”,即將流通券變成與法幣保持固定兌換比率的變相大鈔,兩者可“自由通匯,平行使用”[30]。但因東北流通券的實際幣值已大跌,時評亦認為這“只是便利東北官僚富戶的資產移入關內而已”[31]的意見罷了。
在東北耆宿與東北行轅經委會主任張嘉璈與政府各要員斡旋后,1948年3月13日,財政部呈準行政院正式公布了《東北流通券行使及兌換辦法》,其核心內容為:“東北流通券與法幣兌換比率,定為流通券一元合法幣十元”;“自本辦法公布之日起,法幣準在東北九省與流通券按照兌換比率行使”[32]。事實上達到了所謂的東北流通券“關金化”的目標。上述辦法公布后,東北各界人士對其內容仍不甚滿意。3月18日,東北各省市參議會及人民團體代表召開了東北各界代表聯席會議,提出流通券改革的六項建議,并以聯席會議的名議致電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要求停止繼續發行流通券并限期收兌,限制中央當局發行巨額本票,流通券與法幣的比價應改為發行之初的1:13,公營事業仍按1:11.5計算等[33]。3月25日,中央銀行開始發行東北流通券的五千元大票[34]。隨著發行總量的增加和大額券的發行,流通券的幣值開始急劇貶低,反過來又進一步地加劇了物價的上漲幅度。面對東北各界人士表現出的強烈不滿情緒, 5 月4日下午,俞鴻鈞,張嘉璈等同東北全體國大代表兩百余人商談了兩個小時,達成要點數項:同意停止繼續發行東北流通券并限期收兌,法幣出關行使,流通券可在各地中央銀行無限制兌換,流通券與法幣的比值恢復至1:11.5等。而且,這些辦法將在總統就職之日起施行。這也成為同年5月31日財政部公布的《修正東北流通券行使及兌換辦法》的要點[35]。而在實際上,東北流通券與法幣的購買力比率遠低于此,以同月沈津的零售物價指數的變動計算,“一元流通券僅應等于法幣二元二角”[36],這也帶來了后續的一系列“游資”入關的問題。
在《東北流通券行使及兌換辦法》出臺之前,國民政府當局鑒于解放區經常用東北流通券套取關內物資,所以對流通券向關內的匯兌額度嚴加限制。1948年2月時,東北流通券向平津兩地的匯兌額合計為法幣9517億元,而在該修正辦法出臺后的同年5月至6月,出現了東北“游資”大量涌向關內的情形,五月份匯入平津的流通券折合為法幣總計達107425億元,六月份為110526億元。短短的三個月間,月均匯兌額上漲了十倍多。同時,天津物價波動劇烈,各類商品的零售價格上漲最多者達到一倍以上,即是一般物品也在百分之五十左右。6月當月的食物類商品,如白糖、高粱米、黃豆、花生米等的零售價格較前月分別上漲113%、86%、72%、74%[37]。究其主要原因,則是因為東北流通券的幣值被人為的高估過多,又可在關內各處兌換法幣,匯款額亦予放寬,故囿于一處的流通券以大批“游資”的方式涌入,看似緩解了東北地區的金融形勢,實則加劇了華北地區的金融危機。
從1948年1月到6月,從東北流入關內的資金則累計高達法幣30萬億元以上[38],主要集中于平津兩地。對于東北流通券的持續涌入,激起華北地區民眾的強烈不滿。為此,華北“剿總”司令傅作義于6月17日公布了《限制兌換流通券辦法》和《限制東北匯款暫行補充辦法》,要點為各行局限號兌現東北流通券,兌換兩億元以上者須嚴格審查,分期支付[39]。此項辦法的出臺,無異于宣布財政部于5月末頒布的修正東北流通券行使與兌換辦法的暫時失效。在此期間,平津地區的黑市交易異常活躍。在局勢不利的情形下,應平津參議會的請求,華北“剿總”曾于6月27日一度宣告停止兌換東北流通券,兩日后又宣布“學生或難民每人兌換不得超過二億元”,由東北匯入款項合法幣2億元以上者,“每人每日提現額為法幣兩千萬(元)”[40]。此時,三大戰役中的遼沈會戰已在醞釀之中,國民黨軍隊集中于沈陽、長春、錦州等幾個城市內,東北流通券也大量匯集于此。因物價暴漲,各行局門前擠滿“匯寄贍家費入關之軍公教人員”,受匯款兌換提取額度的限制,“每人須分數次始克匯完,故辦理手續恒達數日之久”[41]。在券料不敷的情況下,中央銀行東北區行籌劃以發行定額本票的辦法來解決搶購秋麥的資金問題,面額為五百萬元、三百萬元兩種,初擬加印一萬億元。7月,中央銀行東北分行副主任寧嘉風在致電總行的電報中稱,東北鈔荒嚴重,當月的行政機關與事業機構的費用與補貼、軍糧款、民食調節款與其它軍費墊款等,需款總計56700億元,“墾乞迅籌大量券料,火速由滬直接運沈”[42]。至8月初時,長春駐軍以“需款購糧萬急”為由,要求中央銀行長春分行每日備足本票六千億元,不得不加發二千萬元、五千萬元的定額本票[43],局勢已經失控了。
同時,關內的法幣也面臨著同樣的窘境。無奈之下,國民政府再度尋求從幣制改革中找到出路。1948年8月19日,國民政府公布了《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規定自即日起發行金圓券,法幣與東北流通券則停止發行,分別由國家行局代為折價收換[44],金圓券一元合東北流通券30萬元,前頒東北流通券每元合法幣11元5角的規定,“自應即同時廢止停兌”[45]。這也宣告了東北流通券存在合法性的中止。
四 與根據地流通券的競爭
在收兌各類雜幣和與法幣關聯的同時,根據地金融機構發行的各種紙幣也與國民政府發行的東北流通券同時流通在東北的大地上。
以“接收”為名出關的國民政府軍政人員可攜帶法幣出關,而從關內挺進東北的八路軍、新四軍和中共選派黨政干部攜帶的關內各根據地銀行發行的貨幣,卻無法使用。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政權急需自己的金融機構發行貨幣進入流通領域。1945年10月,中共中央東北局決定成立東北銀行,同年11月15日正式宣告在沈陽[46]成立。東北銀行成立之初的任務是:發行鈔票,集中解決部隊供給和行政經費等急需費用,支持戰爭。首任總經理由東北人民自治軍后勤部部長葉季狀兼任[47]。東北銀行成立之初發行的幣種為東北銀行法幣[48],因鈔版在奉令撤離沈陽時丟失,該幣種在流通僅兩個月后停發,共發行1924萬元,“為軍政費用支出解決了一大難題”[49]。東北銀行隨即改版發行了東北銀行地方流通券,并陸續收回東北銀行法幣。
東北銀行地方流通券籌備發行之時,正值重慶和談之際。借國共兩黨剛剛簽署停戰協議的短暫和平契機,東北銀行趕印改版的地方流通券,面額為一圓、五圓、十圓、一百圓四種,由1946年1月成立的東北銀行通化分行代理總行向社會發行,初期發行額為26億元。東北銀行地方流通券與偽滿券等值流通,并以該券十元兌換東北銀行法幣一元。東北銀行地方流通券發行之初,國民黨軍部隊正對東北解放區大舉進攻,并相繼占領了東北南部地區的一些城市和農村,東北解放區處于被分割的局面,很難建立起統一的貨幣體系。因而,各地方政府還先后發行過一些以流通券為名的地方幣種,圖案與顏色不一[50],作為東北銀行地方流通券的補充,以解決各根據地的財政困難。4月,哈爾濱解放后,東北銀行總行轉移至此,并以哈爾濱為投放東北銀行流通券的重點城市,向四周擴散發行,先后統一了綏寧省、嫩江省、黑龍江省的貨幣流通。隨之,東北銀行地方流通券的發行量不斷攀升,發行額由1946年時的164億元升至1947年時的1309億元。至1948年6月30日止,除冀察熱遼和內蒙外,全東北解放區共發行東北銀行地方流通券4759億元[51]。
在1946年上半年和談之時,東北民主聯軍同國民黨軍隊停戰,松花江一帶被劃為中立地帶,沒有正規的東北民主聯軍和國民黨軍隊駐守。來往于松花江南北兩岸的多是小商人,販運解放區與國統區各自所需要的物品,從中獲利相當豐厚。如馬匹,在解放區內的價格是東北銀行地方流通券12萬元,在國統區的價格則為東北九省流通券8萬元。當時,兩者的兌換率是4:1,從解放區販運一匹馬到國統區,就可以凈賺東北九省流通券3萬元,折合東北銀行地方流通券12萬元[52]。在松花江以北,由隸屬于東北民主聯軍的保安隊駐守,在北岸的大小渡口都設立了農事會,專門辦理東北銀行地方流通券和東北九省流通券的兌換事宜,以方便商旅,且在實際兌換中執行的比率是3.5:1,以刺激物資流通。1946年下半年時,東北銀行地方流通券與東北九省流通券的比值演變為1:0.9。自1947年5月起,東北九省流通券的幣值狂跌。到1948年11月遼沈戰役結束前夕,東北九省流通券幾乎已變成廢紙,一元只頂東北銀行地方流通券3厘了[53]。
對于東北九省流通券, 東北各解放區采取了“禁止流入,堅決取締”的方針。解放戰爭時期,東北解放區與關內根據地的情況不同,它不需要把貨幣作為外匯來同國統區進行貿易往來。即使在1946 年底前的最困難時期,東北解放區從國統區購買一些急需品,也是用偽幣及蘇軍票來支付的。由于國民政府禁止東北九省流通券入關,東北解放區民主政府制定了逐步將其“趕”回國統區的方針:在根據地老區,堅決禁止東北九省流通券的流通;在剛剛解放的新區,由于距離國民黨統治區域較近,同時為了照顧人民的利益,規定東北九省流通券限期流通,并按1:1的比例兌換東北銀行地方流通券。1947年下半年,隨著軍事上的節節勝利,新解放區不斷擴大。在新區內東北流通券的處理問題上,東北解放區民主政府采取了積極的排擠政策,對國民黨政權將該流通券限定于東北九省流通的做法進行廣泛宣傳,使群眾認識到持有東北九省流通券的時間越長,損失越大[54],將其迅速“擠”出解放區。
隨著解放戰爭中東北地區戰局的發展,1948年時,國民黨軍隊集中在沈陽、長春、錦州等幾個城市中,大量的東北九省流通券也集中在這個狹小的地區里。趁著有利的比價發展趨勢,吉林人民政府明令禁止東北九省流通券在市場流通,銀行亦不兌換,動員持有東北九省流通券的人們到國民黨統治區內購買物資[55]。很快地,除延邊地區外,吉林市場上的貨幣完全為東北銀行地方流通券占領。同時,東北九省流通券的幣值幾乎每天都在下跌。為了穩定解放區的金融,規定在剛解放的新區里,對東北九省流通券“只公布敵我幣制比價,但不兌換、吸收,以便向外驅逐敵幣”[56]的貨幣政策,有利的推進了解放戰爭的進程。
五 結語
東北流通券于1945年12月21日正式發行,至1948年8月19日再次實行幣改時廢止,存續使用約二年半有余。在此期里,東北流通券的發行與流通對于東北地區的金融形勢和老百姓的生活以及東北戰場的軍事形勢等,都產生了相當的影響。
就其發行原因的初衷來看,東北地區的經濟形勢和通貨使用具有相對的獨立性是主因。抗戰勝利后,東北各地經濟的破壞程度相對較小。相對于關內而言,東北地區的物價水平相對穩定,物價漲幅倍數相對較低。就零售物價指數而言,以沈陽新舊統一零售物價指數來看,如以1937年的價格指數為100,則1945年時的價格指數為8864,物價指數的漲幅約為89倍[57]。而同時期國統區的物價指數的漲幅度則更加驚人,達933倍有余[58]。東北流通券發行的目的之一,即為穩定東北地區的金融形勢,使之免受關內經濟波動的影響,至少減少相對的關聯度。而且,受通貨膨脹率不同的影響,關內外的利率差異較大。若東北的資金受關內高利率的吸收而大量入關,則不利于當地生產的恢復和工商業者的復業。如果發行東北九省流通券,就可以通過匯兌管制來限制并調節關內外資金的流動。東北光復之初,國民政府委任張群推薦的熊式輝為東北行轅政委會主任,張嘉璈為經委會主任。張嘉璈向財政部建議:因蘇聯在東北已經發行軍用票,其票值必與法幣有差別,而東北財政經濟情形勢必異于關內。在中央對法幣未有整理辦法以前,“東北(區的貨幣)發行宜暫獨立”[59]。張嘉璈的建議得到了行政院長宋子文和財政部長俞鴻鈞的認可。當時,在國統區流通的法幣與偽滿券一時未有確定的比價,為避免接收之初金融紊亂,擬先期發行東北流通券,使之與偽滿券等價使用,以使國民政府獲得一個較充裕的時段來調查東北經濟金融的實際狀況,并確定新幣種(在實際上相當于原偽滿券)與法幣的兌換比率,以便加以進一步地整頓或治理。就東北流通券發行后的實際效果來看,也具有雙重效應。從積極的一面講,東北流通券以貨幣的形式,充當著一種貨幣屏障,使抗日戰爭勝利后較為穩定的東北經濟,不致驟然受到關內經濟波動的影響。從消極的一面講,東北流通券在進入通脹階段后期的幣值下跌比法幣的幣值下跌幅度還快,且由于多重原因由國民政府明定了明顯高估的與法幣的比值,加速了國民政府在東北區敗亡與退卻的腳步。
在流通券與法幣的兌換比率上,國民政府起初是隨行就市地按照關內外物價的比率確定東北流通券與法幣比價的。但是隨著戰事及經濟情事的發展,關內、關外的物價也在不停的發生著波動。在東北流通券向關內的匯兌過程中,黑市交易始終呈現出“繁榮”的景象。1947年11月以前,關內關外物價的比值維持在1:10左右,中央銀行的公告牌價亦如是,基本上可以得到維持。北平與天津的匯兌黑市交易自東北九省流通券發行后就一直處于活躍狀態。天津黑市上東北流通券與法幣的交易價格一直在1:7至1:9之間波動[60]。隨著戰事的發展和貨幣發行額的上升,東北流通券與法幣之間的兌換比值不斷下降,最低時(1948年5月)降至1:2.2[61]。面對形勢波動,國民政府與東北地方當局本應考慮各方面因素的影響,更訂東北流通券與法幣的比價,但為自身利益計,東北地方當局仍力求維持官方比價,必定難以為繼。東北流通券的匯兌開放后,中央銀行牌價始終未隨行就市,沒有發生過根本性地變動。北寧鐵路被切斷的時候,官匯不通,曾導致錦州一帶匯兌黑市猖狂。國民政府對于黑市的存在一直表現出無能為力的狀態,黑市交易的猖狂也使本已混亂的金融形勢更加糟糕。1948年五六月間,東北流通券以“游資”的形式,一瀉千里般地注入平津,不僅表明其在東北地區的貨幣市場上已無立足之地,也使其發行初衷被徹底拋棄。
在東北九省流通券的發行過程中,還大量存在著國民政府官員的舞弊現象。在匯兌管制時期,關內的流通券處于貶值狀態,百萬法幣可換十六七萬流通券。于是就有行政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在關內大量收購流通券,用飛機帶到關外,再從關外以法定的匯率匯入關內,輕而易舉的牟取利益。時任中華民國經濟部部長的陳啟天對此事評論道:“政府只想到共產黨是政府的敵人,其實是政府的官員專門拆政府的臺。”[62]
在東北光復之初,各工廠企業是急需資金恢復與發展生產的。但是,國民政府向東北撥發的流通券大部分都用于了軍政開支,很少用在恢復經濟建設上。對于東北九省流通券的發行與流通,以張嘉璈為代表的政府當局的立場是,將東北經濟與華北經濟統籌考慮,以溫和的幣制改革的形式將東北“接收”工作平穩過渡至常態下;而東北地方當局的要求則更多的考慮的是地方政情與財政支出。東北九省流通券發行之初對穩定東北金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其在流通后期財政性發行的速度與法幣的惡性增長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加之幣值被人為的高估,反而成為加速國民黨軍隊在東北戰場敗亡的有效催化劑了。
注釋:
[1] 戴建兵:《淺論抗日戰爭勝利后國民政府對戰時貨幣的整理》,《中國經濟史研究》1995年第3期,第141-146頁。
[2] 潘連貴:《中央銀行東北九省流通券個案研究》,《中國錢幣論文集(第五輯)》,中國金融出版社2010年,第449-454頁。
[3] 偽滿州國政府:《(偽)滿洲建國十年史》,偽滿州國政府1943年出版,第96頁。
[4] 吉林省金融研究所編:《偽滿洲中央銀行史料》,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5頁。
[5] 謝國富:《抗戰勝利后國民政府劃東北為九省述評》,《民國檔案》1990年第4期,第115-118頁。
[6] 財政部呈行政院文,1945年10月10日;中國人民銀行總參事室編:《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第二輯1924-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7頁。
[7]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印:《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七編 戰后中國(一),(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1年版,第109-110頁。
[8] 東北行轅經濟委員會主任張嘉璈致財政部長俞鴻鈞電,1945年12月25日;《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第二輯),第689頁。
[9] 后來,1947年4月8日,另訂紅軍票小額券收兌辦法,以一個月為限,隨時收兌。此時,東北政局混亂,戰事頻發,東北各地對于此項規定,都未能積極辦理。
[10][12][18]滕茂桐:《東北幣制整理之回溯》,《經濟評論(上海)》第四卷第二期,1948年10月23日。第四條規定:沈陽、四平、長春、永吉四市,自8月1日至8月10日辦理;其它鄰近各縣市,自8月6日起至8月20日止辦理。
[11] 周舜莘:《戰后東北幣制之整理》,《東北經濟》第一卷第一期,1947年4月出版。
[13] 財政部檔(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關于發行蓋印法幣的布告,1945年11月);《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第二輯),第684頁。
[14] 1931年5月,中央銀行正式發行關金券,作為繳納關稅之用。1942年4月,國民政府財政部規定按關金一元折合法幣二十元的比價,兩者并行流通。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國民政府變相增發的法幣大鈔,關金券公開地行使流通功能,變成真正的紙幣。1948年8月19日,國民黨政府頒布“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實行所謂“幣制改革”,宣布廢除法幣和關金券,發行金圓券,并以1元金圓券兌換15萬元關金券的比率收兌,同年11月21日停止收兌。至此,關金券正式作廢,共流通17年半。
[15] 財政部檔(東北行營經濟委員會主任張嘉璈致財政部長俞鴻鈞函,1946年6月);《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第二輯),第685-686頁。
[16] 財政部檔(東北行營經濟委員會公布東北蓋印法幣儲存收兌辦法,1946年3月7日);《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第二輯),第684-685頁。
[17] 財政部檔(東北行營經濟委員會主任張嘉璈致財政部長俞鴻鈞函,1946年6月;)《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第二輯),第685頁。
[19] 一般物品指大米、高粱米、豬肉、棉布、煤塊等五項。
[20] 楊綽庵:《東北物價變動及其與津滬臺三地比較》,《物調旬刊》第5期,1947年3月下旬出版。
[21] 《東北局面危殆游資紛紛內流》,《經濟通訊》,1948年第3卷第6期,第207頁。
[22] 《東北游資流平津日各達一千億元》,《銀行周報匯編》,1948年第32卷第34期(總第1557號),第40頁。
[23] 中國銀行總管理處:《中國銀行統計叢書·外匯統計匯編(第一集)》,中國銀行總管理處1950年出版,第265頁。《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第二輯),第698頁。
[24][28]楊明正:《論統一東北幣制》,《銀行周報》第31卷第41期,1947年10月13日。
[25] 具體數據可參見滕茂桐文《東北幣制整理之回溯》,《經濟評論(上海)》第四卷第二期,1948年10月23日。
[26] 狄超白主編:《中國經濟年鑒(1947)》,(重慶)太平洋經濟研究社1947年版,第195頁。
[27] 中國銀行遼寧省分行等編印,《中國銀行東北地區行史資料匯編(1913—1948)》,1996年,第194頁。
[29] 財政部檔(行政院致財政部電:催運流通券出關并規定與法幣比價,1948年2月27日);《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第二輯),第689頁。
[30] 《東北耆宿見張嘉璈商東北流通券存廢》,《申報》,1948年2月28日。
[31] 《東北流通券入關問題(北平特約通訊)》,《經濟通訊》,1948年(初)第3卷第10期。
[32] 財政部檔:財政部呈行政院文,訂定流通券行使及兌換辦法,1948年3月13日;《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第二輯),第690頁。
[33] 高超:《法幣出關與流通券貶值所激起的波浪》,《觀察(上海)》第4卷第6期,1948年4月3日。
[34] 《東北流通券五千元大鈔發行》,《銀行周報》1948年32卷17期,1948年4月26日。
[35] 中央銀行檔案(財政部致中央銀行代電:修正東北流通券行使及兌換辦法,1948年5月31日);《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第二輯),第691頁。
[36] 滕茂桐:《東北流通券的厄運》,《經濟評論(上海)》,第3卷第16期,1948年7月31日。
[37] 《天津物價及物價指數》,《天津經濟統計月報》第二十八號,1948年6月20日,第12頁。
[38] 王崇馨:《半年來之天津物價》,《天津物價及物價指數》;《天津經濟統計月報》第二十九號,1948年7月20日,第3、11頁。
[39] 《平津開放流通券匯兌》,《金融周報》1948年第19卷第4期,1948年7月27日。
[40] 《金融消息:平津停兌東北流通券》,《銀行周報》第32卷30期,1948年7月26日。
[41] 報道:《經建一旬》,《物調旬刊》1948年第44期,第23頁。
[42] 中央銀行檔(中央銀行東北區行副主任致總行急電,1948年7月5日);《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第二輯),第696頁。
[43] 中央銀行檔(中央銀行東北區行副主任致總行急電,1948年8月3日);;《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第二輯),第690頁。
[44] 洪葭管:《中央銀行史料》,中國金融出版社2005年版,第1280頁。
[45] 財政部檔(中央銀行致財政部函,1948年8月26日);《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第二輯),第706頁。
[46] 設于老遼寧省博物館舊址內(沈陽市和平區十緯路二十六號)。
[47] 趙錫安等主編:《東北銀行史》,中國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1頁。
[48] 東北銀行在籌備過程中就已準備發行貨幣。適逢蘇聯紅軍撤離,人民政權從蘇軍手中接收了日偽留下的全部工廠和大量物資,有較高的物資保證。東北局最后決定,把東北銀行紙幣與偽滿幣比價定為1:10,向社會發行,稱為東北銀行法幣。東北銀行法幣于1945年11月首發于沈陽,流通于沈陽周圍地區,信譽較高,流通順暢,東北銀行法幣與偽滿幣的比價一度曾達1:11或1:12。但是,由于蘇聯紅軍很快又返回沈陽,明令禁止東北銀行法幣在沈陽市流通,使東北銀行法幣的信譽急劇下降。
[49] 周逢民:《東北革命根據地貨幣史》,中國金融出版社2005年版,第44頁。
[50] 計有嫩江省銀行幣、黑龍江省克山縣流通券、黑龍江省銀行黑河地方流通券,合江省銀行合江地方經濟建設流通券、牡丹江實業銀行幣、東安地方流通券、吉東銀行幣、東北銀行遼西地方流通券等多種。
[51] 《東北革命根據地貨幣史》,第49、118頁。
[52] 潘子明:《松花江畔的陰陽界》,《觀察》,1947年第2卷22期。
[53] 朱建華主編:《東北解放區財政經濟史稿》,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12頁。
[54] 《東北革命根據地貨幣史》,第144頁。
[55] 吉林省金融研究所:《吉林解放區銀行史料》,中國金融出版社出版1990年版,第30頁。
[56] 《東北解放區財政經濟史稿》,第513頁。
[57] 《沈陽價格通訊》、《沈陽商業經濟》編輯部編:《沈陽價格資料》(上集),1985年發行,第186頁。
[58] 見“抗戰八年國統區物價指數(以1937年1月至6月為基期)”,孔經緯:《關于抗戰時期國民黨統治區經濟》,《中國經濟史研究》1989年第2期,第139頁。
[59] 姚松齡:《張公權先生年譜初稿(上)》,(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426頁。
[60] 黃鴻森:《內戰下的東北通貨》,《大公報》(天津版),1948年4月4日。
[61] 可參考“沈陽與天津零售物價指數變動”情況。見滕茂桐:《東北流通券的厄運》,《經濟評論》1948年第3卷第16期。
[62] 特約記者:《爛污東北》,《觀察》1948年第4卷第7期,1948年4月10日,第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