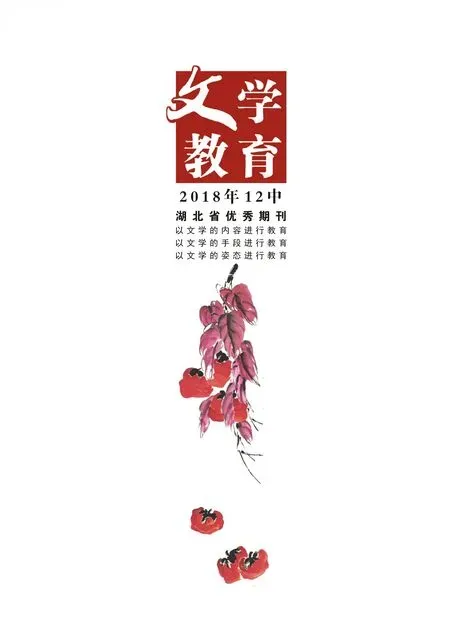《儒林外史》士人形象分析
朱冠宇 孫 鈺
一.引言
“士”通常指我國古代的知識分子和讀書人。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稱:“中國史上的‘士’大致相當于今天所謂的知識分子,但兩者之間又不盡相同。”[1]魯迅曾說:“讀書人及所謂士子。”士人代指古代的讀書人,經過長期的發展逐漸成為了古代知識分子的總稱。早在先秦時期,“士”就有多種含義,最初是指成年男子,后來商周實行分封制,“士”成為了社會中的一個階層,憑借著自己的才能和智慧在行政機關任職,逐漸成為統治者身邊重要的幫手,統治者也越來越重視“士”的選拔。自從科舉制度建立,士人大多都以入仕為自己的理想,官員也主要從讀書人中選拔。于是,中國古代的士人通過科舉制努力向權力中心攀爬,不知不覺成為統治者忠仆。[2]
二.士人形象分析
(一)醉心科舉、執著功名的士人。科舉制度自隋朝出現,就成為最重要的選官制度,它縮短了過去九品中正制中的階級差距,大大增加了普通士人向上層社會流動的可能,因而深得讀書人的追崇。有些人甚至傾其一生奔走在科舉考試的路上。《儒林外史》中最為典型的兩個代表人物就是周進和范進。小說中周進六十多歲還在執著于科舉考試,渴望從中謀求出路,改變自己的貧苦現狀。一直“不曾中過學”的他地位低下,只能以教書糊口,生活困苦,但他早已麻木,接受自己的悲慘人生。新進秀才梅玖對周進冷嘲熱諷,取笑他是“吃長齋”,周進不敢發怒,悶不做聲。舉人王惠傲慢無禮,用“貢院鬼神”之事來刺激周進,說自己是靠鬼神幫助中的舉人,天命如此,“該有鼎元之分”,不得不中。言外之意就是說周進沒有這個中舉的命,吹噓完自己就將周進揮之即去。周進教書被辭退,跟著姐夫參觀貢院,竟然直接撞昏在號板上,等到蘇醒之時,又“滿地打滾,哭了又哭”,“直哭到口里吐出鮮血來”,[3]直到出了貢院,“猶自索鼻涕,彈眼淚,傷心不止[4]”。這一場鬧劇,將其大半生所郁積的辛酸、痛苦和屈辱一下子傾了出來。這是他人生的轉折點,商人們同情他出錢給他捐了一個監生,讓他參加鄉試,順利中了舉人,商人們好人做到底,又籌錢讓他參加會試,結果又中了。然后便是“升了御史,欽點廣東學道”,開始飛黃騰達。
范進也是如此,一考就是幾十年,家里窮得揭不開鍋,后來巧遇周進當學道,出于同情便讓他中了,結果得知自己中舉的消息后便瘋了,這一瘋和周進“撞號板”竟有異曲同工之妙,都讓人感受到八股制對讀書人心靈的催殘。可憐其母面對突如其來的富貴,興奮過頭,“痰迷心竅”,沒享受幾天好日子,便昏倒在地上,匆匆離世。范進裝模作樣的做了孝子,為母親隆重舉行了葬禮,在守孝期間是“如此盡禮”,卻被一個“大蝦元子”露出馬腳。有一次,別人拿蘇東坡開他玩笑,卻沒想到范進己經中了進士了,居然還不知道蘇軾是誰,可見他平常只會死讀經書,視野狹隘,也反映明清八股文對讀書人毒害之深。
這些醉心科舉、執著功名的士人被科舉扭曲了靈魂,麻木不仁,讓人感到荒唐可笑,但他們內心也充滿著悲涼和無奈,又讓人感到十分可悲。
(二)道德敗壞、欺壓下層民眾的士人。道德敗壞、欺壓下層民眾的士人以嚴貢生為代表。作者一直稱呼他為“嚴貢生”,那何謂“貢生”?據中州古籍出版社所編的《中國考試管理制度史》中的記載:“貢生選拔考試是從府、州、縣學生員中選拔優秀學生獻給朝廷或入國子監學習的考試。只有通過廷試合格錄取才能稱為貢生。”從以上記載可以得知,貢生也算是社會的優秀人才了,但是他品質惡劣,種種惡行令人發指。嚴貢生出爾反爾,已經賣出去的豬還說是自己的,不僅敲詐錢財,還理直氣壯的把人打傷,拿不到錢就強行拿值錢的抵。他在鄉里橫向霸道,在有權勢的人面前百般討好,得知剛中舉的范進跟著張鄉紳來高要縣“打秋風”,早就做好準備迎接恭候兩位大人。趁知縣下鄉不在,自作主張大擺宴席去款待剛剛到來的張靜齋和范進,為的就是找機會和大官搞上關系,他恬不知恥的介紹自己,“小弟只是一個為人率真,在鄉里之間,從不曉得占人寸絲半粟的便宜,所以歷來的父母官都蒙相愛。”[5]他這一場出色的表演,不僅沒有拉近與知縣的關系,還被湯知縣所鄙視。當自己的惡行被告到官府時,直接一走了之。
他的弟弟嚴監生膽小有錢,花了大錢幫哥哥了解了官司,可他并沒有痛改前非,反而變本加厲。自己兒子結婚也舍不得花錢,克扣鼓手工錢,鼓手罷工不來,隨便找兩個吹手頂湊,引得眾人笑話;回家時坐船,還利用“云片糕”來敲詐船員以賴掉船錢;弟弟死后還妄想霸占弟弟家產,強逼弟媳改嫁,甚至將事情告到京里,真可謂是心狠手辣。科舉考試考出來這種無恥的貢生,雖能言善辯,卻橫行鄉里,欺軟怕硬,甚是科舉制的可悲之處。但嚴貢生這一形象描繪的的確生動精彩,作者通過一系列細致的動作、語言和神態的描寫,活靈活現的展示出一個能言善辯,顛倒黑白的地主鄉紳形象。
(三)理想的賢士。在《儒林外史》中,還塑造了王冕、虞育德、杜少卿等淡泊名利的士人。王冕,歷史上實有其人,作者對其形象進行了加工,小說中的王冕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既不在意功名,也不喜交友,平時就自己一人閉戶讀書。他不畏強權,像危素這種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派人請他時,他都避而不見,他心中忍受不了那些財主老爺們飛揚跋扈,作威作勢,不愿再為其作畫。但朱元璋上門請教如何治理天下時,王冕卻與其促膝長談。王冕無心仕途,不愿追求功名富貴。他認為是八股這條“榮身之路”使得讀書人看輕了學問的積累和品行的修煉。王冕在小說開頭出現,受到了作者的高度評價,也表明了作者對八股取士,對癡迷科舉的士人的批判態度。
《儒林外史》中還有一個被作者高度評價的真儒——虞育德,位列書末“幽榜”第一甲第一名。作者還為虞育德的出生設置了奇特的現象,以彰顯他的特別,虞育德的母親做夢夢見文昌給了她一張字條:“君子以果行育德。”“當下就有了娠”,后來便生下了虞育德。在此后的篇章中也證實了他是個以德行為重的讀書人。虞育德有著平靜而順利的一生:六歲開始讀書;十四歲就可以教祁太公家兒子讀書;十七八歲跟著云晴川先生學詩文、學地理、學算命;二十四歲進學回家;二十七歲結婚;之后便以“做館教書”為業,偶爾替人看看風水掙錢改善生活,直到四十一歲才去鄉試,中了舉人;然后便是考兩次都未中,到五十歲考中進士;后因如實報了年紀,被朝廷嫌棄年紀大本來想讓他進翰林,最后讓他去南京當了個國子監博士,是個閑職。但是虞育德不僅不抱怨,反而還十分開心,和別人說“南京是個好地方,有山有水,又和我家鄉相近。”說罷,便帶著妻兒上任去了。[6]可見科舉考試并沒有成為他生活的重心,少年時中了秀才之后卻在四十一歲才去鄉試,可見他對科舉十分淡然。但是他也不像王冕,反對科舉的態度也并不那么激烈,對科舉,他始終是抱著一種“隨性”的態度,不刻意強求,也不會刻意拒絕。
虞育德跟多數人都只是泛泛之交,但與莊征君、杜少卿相見恨晚,正可謂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他們彼此傾佩,杜少卿說虞育德是“不但無學博氣,尤其無進士氣。”[7]虞博士也覺得杜少卿“風流文雅,俗人怎么得知。”[8]虞博士喜愛莊征君的恬適,莊征君稱贊虞博士的淡雅。這三個人都是吳敬梓推崇的“真儒名賢”,在“幽榜”上都位列頂端。虞博士為人正直,淡泊名利,踏實本分,樂于助人,做事恰當穩重。他不像杜少卿那么“鋒芒畢露”,也不學莊征君“逃避隱居”。前生平淡,后生也無爭。初來做官,對紛至沓來“拜見”的門生,他也不拒絕,只談論一些讀書人的事情;兩個幫閑勸他借生日騙人送禮時,他義正言辭的拒絕了;他助人時還會講究恰當的方法,為了幫助沒有固定收入的杜少卿,常常把別人托自己做的事轉托給杜,讓杜的生活有所改善;他對考試夾帶的考生保持寬容,考生來答謝,他也“推認不得”,希望考生有廉恥之心,能自覺醒悟;幫助含冤受屈的士子,他也能不圖回報,幫人申冤。這樣的賢士堪稱完美,受到作者的大力推崇,但實在過于理想化,削弱了形象的藝術感染力。
三.結語
中國古代文學作品是中華文明尤其是儒家文化的重要載體之一,其中的士人形象具有豐厚的文化意蘊,并折射出儒學的興衰。《儒林外史》中的士人大多缺乏遠大的政治理想和信念,沉浸在對物欲和權力的追求中,但小說中也塑造了不少賢士,作者將自己的理想追求投射到這些形象之中,透露出作者心底的一絲希望。《儒林外史》塑造了眾多文人形象,突出了人性的復雜,并從各個方面描寫人物,使人物形象血肉豐滿,躍然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