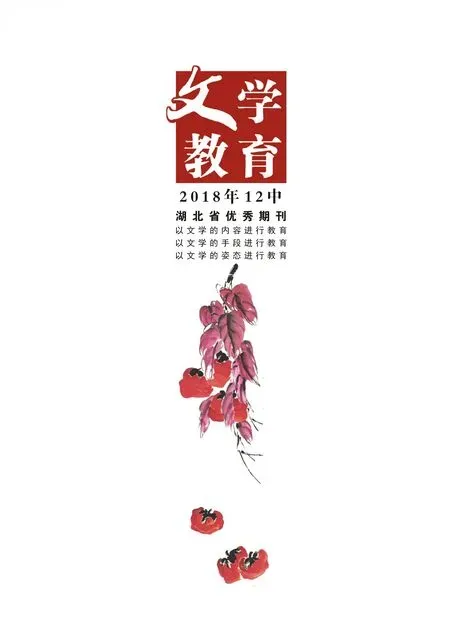高僧傳中人物形象淺析
耿朝暉
三朝高僧傳一般是指梁釋慧皎《高僧傳》、唐釋道宣《續高僧傳》和宋釋贊寧的《宋高僧傳》等三部僧人傳記作品,梁釋慧皎《高僧傳》記載了從東漢明帝十年(公元67年)至梁武帝天監十八年(519年)四百五十三年間,約二百五十七篇高僧事跡。《續僧傳》記載了從梁代初開始至唐麟德二年(665年)一百六十四間約四百八十五位高僧的事跡,《宋僧傳》所載時間始于唐麟德二年,終于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年),記載了約五百三十一篇高僧的事跡。其中描寫了大量的獨具風范的高僧形象,這是文學書寫的核心魅力所在。同時,也寫到眾多異僧及其他人物,他們共同構成了高僧生活的大的背景,展開了時代的畫卷,也為傳記的文學特色增添了光彩。
一.高僧風度
高僧之傳的本就意在記錄“高”德之僧,故而在美好的儀容、智慧的談吐、超然的氣度、離俗的棲居、圓寂的從容外,更強調德的重要性。“慧遠在《沙門不敬王者論》一文中,表明佛門在承續玄學以來,理義辨析的智慧化顯示的同時,仍欲申稱‘釋迦之于堯孔,發致不殊,斷可致矣’的德性自覺。這雖有辯解沙門不敬王者的意味,然佛理續承玄學,其教義又含勸善化俗之意。故在哲學趣味上仍極近于前者的宗旨。佛教哲學的這種成圣的崇高智慧化的內在自覺,恰為其波蕩士人精神世界力量所在”。
與名士的俊朗、風流、談玄不同,高僧風度重在道德力量的表現,如佛心慈悲、度化眾生等,在《曇摩羅剎傳》中,對高僧之美德能感化清泉之感應加以贊美:
護以晉武之末,隱居深山,山有清澗,恒取澡漱。后有采薪者,穢其水側,俄頃而燥。護乃徘徊嘆曰:“人之無德,遂使清泉輟流,水若永竭,真無以自給,正當移去耳。”言訖而泉涌滿澗,其幽誠所感如此。故支遁為之像贊云:“護公澄寂,道德淵美,微吟窮谷,枯泉漱水。邈矣護公,天挺弘懿,濯足流沙,領拔玄致。
傳主能將因人污穢而斷流的泉水感化再出,是自然與人之間感應的一個顯例。魏晉名士“清風朗月,輒思玄度”的人物品賞,是把人的境界、人格美物化,對象化,視為與眼前景物相同的、并列的。而《高僧傳》中“微吟窮谷,枯泉漱水”的高僧,則是升華了人與自然的關系,不僅是一種融合和對等,更是一種彼此道德與美的呼喚,是山水對人物品格之美的感應。不僅強化了人之美,更強化了自然與人之間的交流,對于以往的融合關系的提升。可以說人與物一境,天人合一。真正的美,一方面合乎自然,一方面合乎理想,能把自己安放在巖壑之中的晉人是美的,而高僧則與自然產生一個呼應。
在《法顯傳》中,慧皎主要截取了渡沙漠雪山一節及對話,于譯經成就反而是略記的。傳記中細節記述生動可感,描繪環境之艱險、道路之坎坷,突出表現了高僧為求法不畏犧牲的精神、求法意念之堅定。另外,與法顯自作的《法顯傳》相比,又多了如下一節:
至夜,有三黑師子來蹲顯前,舐唇搖尾。顯誦經不輟,一心念佛。師子乃低頭下尾,伏顯足前,顯以手摩之。咒曰:“若欲相害,待我誦竟。若見試者,可便退矣。”師子良久乃去。……進至迦施國,國有白耳龍,每與眾僧約令國內豐熟。皆有信效。沙門為起龍舍,并設福食。每至夏坐訖,龍輒化作一小蛇,兩耳悉白。眾咸識是龍。以銅盂盛酪,置龍于中。從上座至下行之遍乃化。去年輒一出,顯亦親見。
梁《高僧傳》與《法顯傳》的材料運用上多一幕黑獅子的情節,少一幕快回達漢地時海上遇險一節。從文化蘊含來看,黑獅子一節更具有佛教文化底蘊,也避免并與之前屢遇險情產生重復之嫌。
二.異僧異能
三朝高僧傳除了著力塑造德、才、學具高的僧人形象外,中還著重描寫了高僧獨特的一面。比如,眾多傳記中都出現了“異僧”,引起人們的注意。首先,異僧的異相令人關注,《宋僧傳》《唐會稽永欣寺后僧會傳》中刻畫了梵僧與眾不同的容貌,極具異域色彩。“至唐高宗永徽中見形于越,稱是游方僧,而神氣瑰異,眉高隆準,頤峭眸碧,而瘦露奇骨,真梵容也。”
另外,高僧巧言善辯寫出其異能。《續僧傳》的《慧凈傳》,寫到與道教徒的辯論與取勝的情景,人物的聲口動作宛如眼前,充分表現了異僧的異能,“大業初歲,因尋古跡至于槐里,遇始平令楊宏集諸道俗于智藏寺,欲令道士先開道經。于時法侶雖殷,無敢抗者。”于是在不公對待面前,傳主決定為佛寺一辯:
凈聞而謂曰:“明府盛結四部,銓衡兩教,竊有未喻,請咨所疑。何者?賓主之禮,自有常倫,其猶冠屨不可顛倒。豈于佛寺而令道士先為主乎?明府教義有序,請不墜績。”令曰:“有旨哉!幾誤諸后。”即令僧居先坐,得無辱矣。有道士于永通頗挾時譽,令懷所重,次立義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令即命言申論,仍曰:“法師必須詞理切對,不得犯平頭、上尾。”于時令冠平帽,凈因戲曰:“貧道既不冠帽,寧犯平頭?”令曰:“若不犯平頭,當犯上尾。”凈曰:“貧道脫屣升座,自可上而無尾。明府解巾冠帽,可謂平而無頭。”令有靦容。凈因問通曰:“有物混成,為體一故混,為體異故混?若體一故混,正混之時已自成一,則一非道生。若體異故混,未混之時已自成二,則二非一起。先生道冠余列,請為稽疑。”于是通遂茫然,忸怩無對。
此處對方無言再對,扭捏神態描述生動,接下來傳主又說:“先生既能開關延敵,正當鼓怒余勇。安得事如桃李,更生荊棘?”以非常形象的比喻說明現在的情況,“仍顧令曰:‘明府既為道助,何以救之?’令遂赧然。爾后頻有援救,皆應機偃仆,罔非覆軌。”反復論辯,都是令對方無法與之抗辯。
此外,“感通”科中還連續三篇傳記都是記述狂僧,分別是《唐陜府辛七師傳》“一日哀號之際,發狂遁去,其家僮輩躡跡尋之。見其入窯灶中端坐,身有奇光,燦若金色。”《唐京師大安國寺和和傳》“其為僧也狂而不亂,愚而有知,罔測其由。發言多中,時號為圣。”
這些個性不一的異僧,或以奇特的外貌令人印象深刻,或以難測的言行使人不測真容,預知未來,發言多中,是高僧形象的另類表現,也是傳記人物的另一側面的補充。
三.人物群像
除了眾多德行高僧外,三朝高僧傳中還塑造了許多個性突出的僧人形象,以及與高僧關系密切的人物,如帝王、居士等,他們或擁護佛法,鼎力相助,或半信半疑,反復無常,形成了以高僧為核心的人物群像。
僧傳中的居士形象多與佛經的早期翻譯有關。因為佛教剛傳入中國時,在中國弘法的高僧多數來自西域,不通漢語,居士的作用是很大的,圍繞這些高僧,出現了相對固定的居士群體。出現次數較多,貢獻較大的如聶承遠、聶道真父子:
時有清信士聶承遠,明解有才,篤志務法。護公出經,多參正文句。《超日明經》初譯,頗多煩重,承遠刪正,得今行二卷。其所詳定,類皆如此。承遠有子道真,亦善梵學。此君父子,比辭雅便,無累于古。又有竺法首、陳士倫、孫伯虎、虞世雅等,皆共承護旨,執筆詳校。安公云:“護公所出,若審得此公手目,綱領必正。凡所譯經,雖不辯妙婉顯,而宏達欣暢,特善無生,依慧不文,樸則近本。”其見稱若此。
其他不同傳記種也有對這對父子的描繪,都是表現其譯經功德的。另如女性居士張普明“咨受佛法,耶舍為說佛生緣起,并為譯出《差摩經》一卷。”傳主為其譯出經卷一部,可見其虔心對傳主的影響。其他對譯經有特殊貢獻的居士還有卷四《朱士行傳》中的竺叔蘭,他由早期游獵到暫死明白因果,因為精通梵漢,故而對譯經貢獻很大,也是一個很有特色的人物。
《續僧傳》中有偉大的母親形象,《釋真玉傳》中描寫了一位堅強而極有遠見的母親,她不僅獨自撫養雙目失明的孩子長大,而且由學琵琶到學成大業,極具犧牲精神,風雨無阻地帶孩子聽講學習:
釋真玉,姓董氏,青州益都人。生而無目,其母哀其不及,年至七歲,教彈琵琶,以為窮乏之計。而天情俊悟,聆察若經,不盈旬日,便洞音曲。后鄉邑大集,盛興齋講,母攜玉赴會,一聞欣領,曰:“若恒預聽,終作法師,不憂匱餒矣。”母聞之,欲成斯大業也,乃棄其家務,專將赴講,無問風雨艱關,必期相續。玉包略詞旨,氣攝當鋒,年將壯室,振名海岱。后遭母憂,舍法還家,廬于墓側,哀毀過禮。茹菜奉齋,伏塊持操,三年野宿,鄉黨重之。后服闋附道,修整前業,覽卷便講,無所疑滯。預聞徒侶,相次歸焉。
此外,還有有一些個性殊異的僧人形象,如“神異”科中的杯度、邵碩等。書中展現其不同尋常的言行,既表現了不拘一格化度眾生的慈悲,又為后世提供了活潑生動的文學素材,如后世人熟悉的濟公形象,很大程度來源于此。有的高僧獨特才華,如《梁僧傳》卷六《釋道祖傳》:
遠有弟子慧要,亦解經律而尤長巧思。山中無刻漏。乃于泉水中立十二葉芙蓉。因流波轉以定十二時。晷景無差焉。亦嘗作木鳶飛數百步。
道祖發明的十二葉芙蓉既能做流水計時工具,又能做獨飛百步的木鳶,其聰慧才思勤巧可見一斑。卷十一中著《出三藏記集》的釋僧祐,“祐為性巧思,能目準心計,及匠人依標,尺寸無爽。故光宅攝山大像剡縣石佛等,并請祐經始準畫儀則。”卷七中的《釋僧徹傳》的傳主僧徹,在學佛之余不僅善著詩賦,而且與魏晉名士一樣,善于長嘯:
又以問道之暇,亦厝懷篇牘,至若一賦一詠,輒落筆成章。嘗至山南攀松而嘯,于是清風遠集,眾鳥和鳴,超然有勝氣。退還咨遠:“律制管弦,戒絕歌舞。一吟一嘯,可得為乎?遠曰:以散亂言之,皆為違法。”由是乃止。
從傳記中可以看到,僧徹雖精通詩賦、長嘯,但后來知道這些不合乎佛法精進修道的宗旨后,就放棄了。這些生動有致的描寫,個性不同的人物,活動在高僧周圍,既襯托了高僧的威儀,又是時代的寫照,是三部傳記又一個可珍貴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