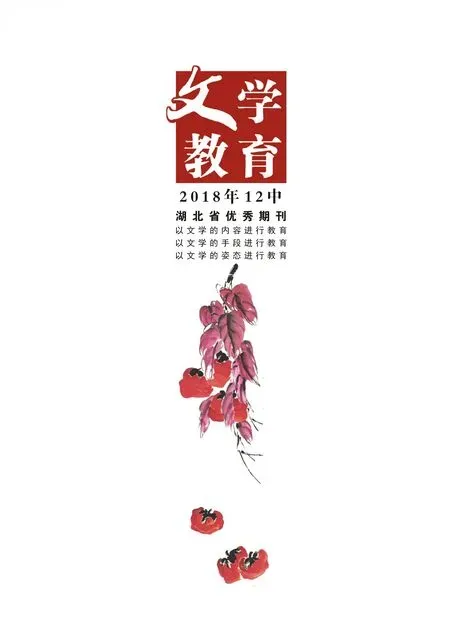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邏輯路徑
張啟發
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作為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發展階段,在經歷過西方馬克思主義危機之后,依然具有強大生命力。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是馬克思主義具有強大生命力的保障。馬克思主義哲學逐漸傳入中國,經過與中國傳統文化的交融,使得馬克思主義哲學已經成為指導中國不斷前行的力量。
一.文化意識的自覺
文化意識的自覺,為馬克思哲學中國化提供條件。“文化自覺”就是是人對其文化的“自知之明”,以加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和取得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馬克思主義哲學本身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和民族性,中國將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就是中華民族基于自身的文化傳統和現實境域作了理論思考、精神追求和實踐探索。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為中國帶來了馬克思主義,而五四運動的爆發,則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奠定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基礎。馬克思主義哲學并非是天然適合中國的,而必須是中國化之后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才是符合實際的。西學東漸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傳播,但本質上卻是中國文化與外來文化之間的內聯性,人化本質的匯通和中國強大的文化底蘊的基奠。另外這種內聯性所表現的中國文化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自愿贊同,本質上就是中國文化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自覺。
首先西學東漸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傳播提供了客觀條件。在西學東漸的過程中,馬克思主義被介紹到了中國,從而使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傳播成為可能,此時主要以傳教士為主,擁有不同背景的傳教士即使目標不同,但是在傳播西方文化的過程中零星的介紹了馬克思主義,使得傳入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的介紹不夠完善和準確,也沒有明確介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內容;隨著馬克思主義哲學傳播開來,并在中國接受鑒別和檢驗,經過“全盤西化”和“全盤中化”兩股力量的較量,使得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自覺地選擇馬克思主義哲學。
其次是中西人化本質的匯通。從人本身來看,人除了是一種類存在而外,還是一種文化的存在。文化在其本意上而言是以文化之,本質上就是化人,文化就是人化。人具有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的雙重屬性。當談及類存在的人的時候,我們所言人的社會屬性,并借此屬性創造一個“文化世界”,人生活在有意義的世界、精神的世界中。卡西爾認為,人并不像動物那樣只能被動的接受直接給予的“事實”,而是能夠發明、運用各種“符號”,創造出屬于自己的“理想”、“可能性”。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歷程,是中華民族追求“理想”和“可能性”的過程,并且別不斷試圖超越趨向“理想”。正是因為中國文化的自覺和中華民族的自覺,才使得馬克思主義哲學能中國化,并在傳統中國與現代中國的歷史連續中,把握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在同一性,結合中國人的生命體驗,從中國傳統文化汲取實現中國化的實踐智慧。馬克思主義哲學有中國文化的因素,而中國文化同樣蘊含著馬克思主義的因素,正是基于二者對于人化的理解,使得中國文化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過程中表現為理論自覺。從這方面而言,馬克思主義哲學之所以能夠在中國扎根,就是其實踐本性與中國人的實踐智慧互通互容,并具有內在統一性。
再次是中國文化底蘊的基奠。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人們往往聯想到馬哲在中國化的運用,即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任何一種哲學、一種文化都帶有強烈的地域性、民族性。事實上,這個方面指向更深層次就是馬哲中國化的文化底蘊,就意味著馬克思主義哲學應有中國意蘊,含有中國“元素”,帶有中國傳統文化的思考方式、價值理念,精神傳統。馬克思主義哲學要中國化就不能擺脫中國的文化傳統。中國傳統文化中獨特的民族文化基因和精神傳統,包含了“天人合一”的思維結構,“天”、“人”對應了形上、形下,“合一”就指天人上下的內外互融、渾然一體。另外,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能迅速傳播開來,還與中國為自身的文化氛圍和文化傳統密切相關,除了哲學上、思想上的切合性而外,馬克思主義中國哲學中國化的文化底蘊還體現了一種文化、文明的連續性。
二.文化制度的自信
文化制度的自信使得馬克思主義哲學能中國化。隨著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傳播,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取得了豐碩的理論成果和實踐成果。但是近年來,隨著國力強大,國家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而反觀中國歷朝歷代,凡其朝代繁榮昌盛,必定是其文化繁榮的年代。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國力的確走向了世界前列,不僅帶給中華民族優厚的物質文化生活,更改變了中華民族在世界行列中地位化話語權力的轉變。我們越發認為不管時代怎么變化,哲學作為時代的精華和核心,其本質不會改變,我們越發認為先人智慧的優越性。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結合,彰顯了強大的“和而不同”的會通觀。換言之,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而不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化”中國,本質上是中國文化制度自信的強大生命力。
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有著民族復興的文化基礎,使得中國文化有選擇性地吸收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是中國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踐運用,致力于中華民族復興的宏偉藍圖。歷經磨難的中華民族,始終以民族復興作為第一要務,而民族復興的核心是文化的復興。馬克思主義本身對于中國而言是“舶來品”,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華民族復興相結合,必然會生產出“時代之精華”。今天我們又重提民族振興的問題,是因為國情已經發生了變化,我們現階段就是要自身的崛起,有意識的探究中國的未來,踐行中華文化的自主性。國家需要自主性,同樣文化也需要自身的自主性,中華文化也要實現文化生命的自我主宰。我們今天更加強調中國的傳統文化,回到傳統文化中尋找智慧,我們需要回歸中國傳統文化。從這個意義而言,馬克思主義哲學能中國化,根本與中國民族復興的內在需求相一致而作出的選擇。而這又是因為中國文化自度的強大生命力所賦予我們時代的自信,同時也給予中國有選擇性地吸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能力。另一方面,“和而不同”的會通觀彰顯了中國文化制度的自信心。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而不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化”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文化,尤其是傳統文化二者不是絕對對立的,而是相互之間的會通。某種意義上可以借助現代的思想資源探討馬克思主義、中國傳統文化以及西方文化三者的結合,會通文化視域之中的中、西、馬哲學,以中國文化的體悟觀解讀西方人的世界觀與價值觀,尋找三者哲學會通的的自洽性。而中國文化中“和而不同”的會通觀就是激活馬克思主義哲學鎖鑰。在中西馬三哲學的匯通中,中華文化的包容性,使得外來文化哲學釋放出更強大的生命力。而中國文化的制度,規定了中國必然吸取外來文化的精髓,這就為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劃定了邊界。由此而言,中國文化制度在吸收外來文化,以便為我所用的基礎上彰顯出制度的優越性,而那些不符合中國實際的文化哲學也將“融合”在強大的中華文明當中。
三.文化觀念的自由
文化觀念的自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最終歸宿。觀念的自由是文化發展的豐富性提供了條件。文化是發展著的文化,文化本身也具有民族語地域的因素,世界文化的豐富性就在于此。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要發展,核心就在于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在發展。正因為如此,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必然要吸收外來文化的的滋養。歷史上任何一個強大的時期,必定是文化繁榮發展的時期,也是文化自由發展的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傳入中國,近一個世紀的繁榮發展,已經形成獨具中國特色的哲學形態,原因就在于中華文化內在的包容性所賦予的自由狀態。這種文化自由的意識釋放了文化的生命力,而任何一種文化想要不斷激發活力,追求文化自由則是一條最有效路徑。然而這并不是說,追求絕對的文化自由。正如此前所言,各民族文化都有其文化的自主性和優越性。文化的強大就是以“立足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的原則,豐富和發展文化。如果說追求文化觀念的絕對自由,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又回重回“全盤西化”或是“全盤中化”的老路。從這個意義而言,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發展,同樣需要遵守“立足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的文化準則,而這本質上就是文化觀念本身的自由,亦即尋求文化身份的認同。因此,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需要堅持中國實際的前提下,注重與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結合,不僅需要從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做研究,而且還需要從西方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做研究,以此豐富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
四.余論
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遵循了從“文化自覺”,再提升為“文化自信”,最終通達文化觀念的自由的邏輯路徑。從最初尋求文化意識自覺性以獲取傳播的條件,到其逐漸彰顯生命力的過程中,中西文化哲學的交融必需堅守的文化自信。再到最后對自由的文化觀念的追求,使得馬克思主義哲學本身的發展自成邏輯。作為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未來的發展路徑必須是“立足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唯其如此,馬克思主義哲學才能釋放出強大的生命力。所以我們在強調復興中國文化、保持文化自信的同時,并非完全拋棄馬克思主義哲學,而是更加將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傳統文化有機結合,產生面向時代的,更加先進的理論成果,為我們社會主義更好地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