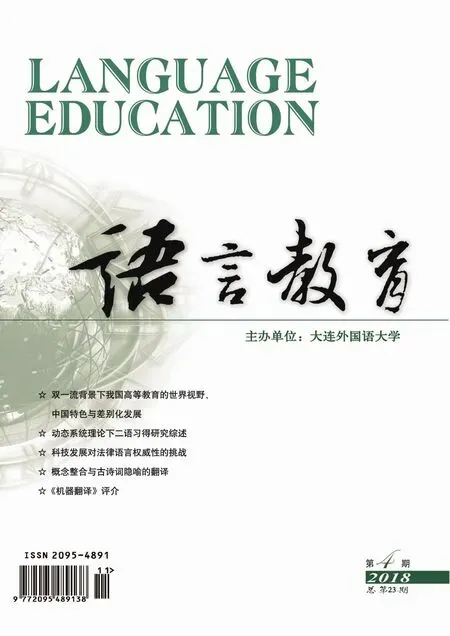“常規化”的反常規敘事
曹麗紅 陳文鐵
(大連海事大學,遼寧大連)
1.引言
近年來,反常規敘事(unnatural narrative)①“Unnnatural narrative”一詞,國內學者大多譯為“非自然敘事”。筆者從“科學性”和“可讀性”術語翻譯原則角度,認為這個敘事學術語應譯成“反常規敘事”更合適。為此,作者專門撰寫了關于這個術語翻譯的原則一文,并期待與讀者見面。研究是敘事理論中令人興奮的新課題(Alber&Heinze,2011∶1)。“反常規敘事學已經成為敘事理論中最振奮人心的新范式,是繼認知敘事學之后最重要的新方法之一”②但是對于成立“反常規敘事學”(Unnatural Narratology)這門學科,學界尚有爭議,“反常規敘事學至少在目前還是一個非常有爭議性的話題”(Bundgaard et.al,2002:15)。(Alberet al.,2013∶1)。以布萊恩·理查森(Brian Richardson)、揚·阿爾貝(Jan Alber)、亨里克·尼爾森(Henrik Nielsen)、斯特凡·伊維爾森(Stefan Iversen)、莫妮卡·弗魯德尼克(Monika Fludernik)等為代表的西方敘事學家們對此展開了大量探討,發表了豐富的研究成果。同時我們需要認識到,反常規敘事依然是一個有爭議的話題。除了對反常規敘事的定義有多種看法外,學者們的研究重點大多是后現代主義文本中“未常規化”的反常規敘事,而對于早期敘事中已經“常規化”的反常規敘事研究甚少。這是因為反常規元素在后現代主義中表現得尤為集中和激進。其實從歷時角度看,“后現代主義的反常規情節和事件并不是嶄新的現象,因為早期的敘事作品中就已經出現了反常規元素”(Alber,2011∶42)。由于早期敘事作品已經成為文類規約,讀者在閱讀時很容易理解其中的反常規元素,所以大多數學者忽視了此類已經“常規化”的反常規敘事。可以說“常規化”的反常規敘事是推動敘事學和文學史發展的一股被忽略的力量,理應得到研究者的重視,因此本文的研究焦點是“常規化”的反常規敘事。那么什么是“常規化”的反常規敘事?什么是“未常規化”的反常規敘事?如何解讀反常規敘事使之常規化?“常規化”的解讀對文類發展有何意義?本文將一一探討這些問題。
2.反常規敘事的定義
首先,到目前為止關于“敘事”的定義均側重于“自然的”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反常規”的元素。“自然敘事”(natural narrative)與“反常規敘事”相對應,莫妮卡·弗盧德尼克將“自然敘事”定義為“自然的口頭故事講述”(Fludernik,2002∶10)。《牛津英語詞典》(OED)將“反常規”(unnatural)定義為“與自然的、常規的、或與期待的不一致;非常規的、奇特的”(尚必武,2015∶96)。
對于“反常規敘事”這一術語的定義,敘事學家們則有不同的聲音。他們認為“反常規敘事學不是同質一元的理論流派。盡管反常規敘事理論呈現國際化的發展趨勢,但它也是多元的、雜合的和多聲的思潮,學者可以從多重研究視角來分析和定義反常規敘事”(Alber&Heinze,2011:1)。
理查森(Brian Richardson)是最早研究反常規敘事的學者之一。他指出小說中存在不同的表現模式,即摹仿、非摹仿和反摹仿。摹仿的作品是指摹仿非虛構作品,試圖通過某種可供辨識的方法來描繪人們關于世界的體驗,例如19世紀的現實主義小說《安娜·卡列尼娜》;非摹仿的作品可能發生在另一個平行世界中,遵循這個世界的規約,或者這類作品把超自然的元素添加到摹仿的故事世界中,比如神話、童話、超自然小說等非現實主義作品;而反摹仿的作品則同摹仿(現實)相悖并產生陌生化的場景、物體和事件等,于是文本中會出現大量不可能的時空現象、因果倒置,以及對抗自然化與常規化要素的敘述行為等等,這類典型作品如貝克特的荒誕派戲劇等。理查森進一步提出,“不同于非摹仿的特質,反常規實際是由反摹仿構成的,因為反摹仿違背傳統的摹仿慣例,并凸顯不真實的本質”(Richardson,2011∶34)。
尼爾森認為反常規是“偏離自然的范式,即口頭敘述”的敘事(Alber et al,2012:373),他認為反常規敘事是虛構敘事的一個子集,其中的敘述時間、故事世界、思維再現及敘述行為等會表現出物質上、邏輯上、記憶上和心理上的不可能性,或是較之于真實世界故事情境的不可信性。
伊維爾森的定義則聚焦于故事和情節之間難以理解的沖突,即“向讀者展示故事世界的規則與故事世界中的情節或事件之間的沖突,這些沖突和讀者的表面理解是相反的。”(Alber et al,2013:6)
而阿爾貝指出,反常規敘事是“在邏輯上、物質世界中和對人力而言不可能發生的場景或事件(Alber,2016:1)。也就是說,反常規敘事違背了統治著物質世界的法則、眾所周知的邏輯準則和人類知識與能力的標準界限等,從而展現的敘述場景在真實世界里是不可能存在的。
從以上定義來看,敘事學家們對“反常規敘事”采用了“多重定義”,這也是強調術語本身的多元性(Alber et al,2012:351)。但是無論如何定義,反常規敘事中包含極端的、怪異的、不真實的、不合邏輯的因素,它是對現實主義范式的越界。
2.1 “常規化”的反常規敘事
“常規化”的反常規敘事,并不意味著“自然化”(naturalized),“常規化”就是解讀反常規使之轉化為讀者認知范疇的一部分,但它們依然含有“反常規性”(Nielsen,2011:85)。只是讀者不再對“反常規”元素感到陌生或疑惑,而是能夠理解這種反常的故事世界。因為“讀者把反常規元素劃入了特定的文類規約中,即把這種異常現象嵌入到合適的話語環境中”(Alber,2016:49-50)。這些反常規的敘事已經轉化到人們的認知領域,成為人們敘述表達時常見的習慣。
“常規化”的反常規敘事在文學史上數不勝數。從話語層面上看,典型的‘常規化’的反常規敘事有19世紀的第一人稱現在時敘事,此外還有全知敘事、自反式敘事、同故事敘事等等(Alber,2010:131)。開始時,這些敘事讀起來似乎令人奇怪,我們也很難下定義。而今天,讀者已經非常熟悉第一人稱現在時的敘事了,從某種程度上講,讀者在閱讀時根本就不會注意到這一點,這種新的形式和技巧也隨著時間變得“常規化”了。
從故事層面上看,我們熟知的有動物寓言中的動物可以說話;史詩、傳奇、哥特式小說以及奇幻敘事中可以出現魔法;我們可以看透現代主義小說中人物的想法;我們還能接受科幻小說的時光旅行等等(Alber,2016:50)。弗魯德尼克所謂的“寓言、魔幻、幻想和超自然”文本,包括上述的早期先驅式的文本都屬于“常規化”的反常規文本。讀者傾向于將這些“常規化”的反常規敘事視為文類規約。
2.2 “未常規化”的反常規敘事
反常規敘事不僅包含“常規化”的敘事,還包含相反的未成為常規化的敘事。盡管隨著時間的推移,反常規敘事中的某些現象成為常規化的敘事,但仍有一些敘事,依然令讀者感到突兀、奇怪。阿爾貝還劃分了極具陌生感并使人疑惑的后現代主義作品的反常規元素,和早期作品中己經逐漸演變為重要文類特征的反常規元素。“未常規化”的反常規敘事,是那些依然令讀者產生奇怪的、不安的認知感受的敘事。按照俄國形式主義者維克托·謝克洛夫斯基(ViktorShklovsky)的看法,這些不可能的場景和現象給讀者造成的疏離感和迷惑感表明“這種文本仍然具有陌生化效果”(Shklovsky,1965:12)。
從話語層面上看,話語本身是為了建構故事或表達故事的,但是在反常規的文本中,話語不再為故事服務,而是為話語自身服務,話語顛覆或消解了故事。例如,敘述者會說,“今天下雨了,今天沒有下雨。”這樣的反常規敘述行為給讀者理解文本帶來了極大的挑戰,由于讀者無法用現有的認知模式理解故事,這樣的敘事仍屬于“未常規化”的反常規敘事。從故事層面上看,反常規敘事建構在物質上或邏輯上不可能的故事世界中,通過展現不可能的敘述者與故事場景、非現實的人物、反常規的時間或擬人化的空間,解構傳統意義上的人類敘述者、擬人化的人物,還有讀者對現實世界的時間和空間的理解。比如先鋒實驗小說以及后現代主義敘事等就是典型的“未常規化”的反常規敘事,它們將不可能元素集中化、激進化,文本中充滿了令讀者感到奇怪、陌生或不尋常的場景或事件,超越了讀者的認知范疇。
2.3 反常規敘事的“常規化”解讀
既然反常規敘事的話語是反常的,故事世界幾乎是不可能發生的,那么對于那些習慣于閱讀自然敘事的讀者而言,不免會有陌生感、新奇感和疑惑感,同時還面臨著解讀這類文本的困惑。那么讀者會如何閱讀這類反常規敘事?
阿爾貝等學者提出了反常規敘事的“常規化”解讀觀點。既然我們始終受到自身認知結構的約束,那么我們也只能在認知范圍和模式的基礎上應對反常規敘事。讀者在閱讀包含不可能存在的故事的文本時,其首要任務在于闡明反常規是如何激發我們創造出超越真實世界知識的認知模式,使得我們認知的模式接受那些不存在的事物,從而讓這些“不可能”成為我們現實中的可能。其次,讀者需要回答反常規是如何看待我們以及我們所處的世界的(袁德雨,2016∶54)。也就是說,反常規敘事是根植于我們真實的世界。文學作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讀者的“認知”就是媒介,解讀尚未“常規化”的反常規敘事就是認識世界、感知世界的過程。正如在阿爾貝看來,大多數后現代主義敘事仍然表現的是故事世界,而不是構建純粹抽象形式的話語、文字或轉向詩歌的封閉式寫作(Alber,2016:46)。在最基本的閱讀模式中,無論敘述的文本結構有多奇怪,它都是有目的、有意義的交際行為中的一部分。簡而言之,就是“某人在試圖表達某事”——不管這個“某事”可能是什么(Alber,2016:46)。他還將人性化圖式應用于文學文本:即使最奇怪的文本,也與人類或人類的關切以及我們生活的世界有關。的確如此,在“未常規化”的反常規敘事中,我們依然能辨別出世俗的元素。例如,在后現代主義小說中,我們仍然可以注意到空間和時間坐標,以及發生在主人公身上的某件事情。因此,反常規敘事仍然會“投射出一個世界,不過是部分的或不連貫的(Mckeon:1987,151)。
那么讀者應該如何解讀反常規敘事使之常規化呢?這就需要讀者的認知充當媒介。一般來說,讀者基于弗盧德尼克的“體驗性”或“‘現實生活體驗’的擬摹仿”,使“反常規”轉化為“常規化”的過程,就是讀者解讀反常規敘事、恢復認知平衡的過程。根據喬納森·卡勒(Jonathan Culler)的說法,讀者在面對費解的文本要素時,可以喚起熟悉的認知模式使這些要素自然化,“如果我們不希望在碑文前目瞪口呆,那么必須要回復和歸化那些奇怪的、正式的、虛構的東西,使其回到我們正常的視野范圍內”(Culler,1975:134)。弗盧德尼克也認為:“通過‘敘事化’(narrativization)的過程,即‘一種通過求助于敘事圖式來歸化文本的閱讀策略’,讀者就可以利用認知要素理解文本的斷裂與奇異之處(Fludernik,2002:43-46)。她還指出,規約屬于文類、社會關系、慣例。闡釋反常規敘事則需要遵循某些文本閱讀的規約,借助于我們熟知的并且大量使用而被規范化了的套話、類別或場景(Fludernik,2012:367)。因此,當讀者在反復接觸文本中的反常規現象時,通常會調整閱讀模式,逐步接受不可能的場景或事件,把“未常規化”的反常規敘事解讀轉化成“常規化”的反常規敘事。
當然,有些學者對于常規化的反常規敘事提出異議。尼爾森、伊維爾森、理查森等學者不贊成解讀反常規敘事。尼爾森認為,許多文本經過自然化的解讀后,其中蘊含的含混而獨特的意義都消解殆盡了(Nielson,2014:256)。他提出“反常規化閱讀策略”(unnaturalizing reading strategies),建議不要一味訴諸真實世界的闡釋模式,而是應該將目光轉向虛構藝術本身。但我們得承認,常規化還是未常規化,都是反常規敘事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是密不可分的。“常規化”和“反常規化”解讀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而是兩者皆可的選擇(尚必武,2016:5-16)。
3.解讀“常規化”的反常規敘事的意義
阿爾貝指出,“當物質世界或邏輯上的不可能性轉化為一種新的感知模式時,那么一種新的文類就誕生了”(Alber,2011:43)。文類意味著“種類或類型”,“一種文類就是一種文學”(Mikics,2007:132)。“文類就是有關辨別和分類的問題:把事物組織到可識別的種類中去”(Frow,2005:51)。斯坦尼斯拉夫·萊姆(Stannislaw Lem)認為,“靜態模式下的故事講述屬于文學慣例,違背這一慣例則有助于文類的進化(Lem,1985:123)。從歷時的角度看,在英語文學史上,從古英語史詩到后現代主義,各種文類層出不窮,如史詩、中世紀奇幻故事、18世紀的物件敘事、奇幻的超自然敘事、含有讀心術的現代小說、包含不可能的時間的科學小說等等①本文提到的文類都是阿爾貝意義上的“亞文類”(subgenre)(Alber,2011:43)。,它們的發展都離不開“常規化”的反常規敘事。阿爾貝認為反常規敘事的‘常規化’是推動新文類塑形和文學史進程的一股被忽略的推動力量(Alber,2012:373)。解讀反常規敘事使之常規化將不斷推動文類的創新和發展。
在史詩方面,以古老的基督教詩歌《十字架之夢》(The Dream of the Rood)為例,敘述者通過做夢的形式與十字架對話(Swanton,1970:1-78)。在敘述者“滿懷悲痛/久久凝視救世主之樹”時,十字架竟開口說話。文學的擬人化在古希臘文學中早已出現,而十字架自康斯坦丁大帝后也頻繁出現在文學作品里,但以十字架為第一人稱敘述者,在歐洲文學似乎還沒有先例。詩作的主體部分是十字架的獨白,其中關于耶穌受難的描寫生動深刻,是全詩精華所在(肖明翰,2011:11)。當然無論現在還是過去,物質世界中的十字架都是不可能說話的。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在詩歌中出現會說話的敘述者就逐漸被讀者接受,也促進了這種文類的形成。
而中世紀的奇幻故事,從廣泛的民間故事體裁中脫穎而出,它的特點有“魔幻變形、巨人和侏儒、年輕女性被囚禁或被詛咒、盛大的成年儀式等等”(Mikics,2007:116)。由此可見,它和超自然關系密切,涉及到物質世界中不可能存在的力量,并超越了科學可見的宇宙。當這種奇幻故事出現時,讀者則予以“常規化”解讀,并逐漸接受在小說世界中可以存在的超自然力量。在阿爾貝看來,可以假設這一“常規化”的過程開始于中世紀之前,因為超自然力量早在古英語史詩時期就發揮了重要作用②如古英語史詩《貝奧武夫》(Beowulf),古代阿拉伯、印度、波斯等的民間故事集《天方夜譚》(Arabian Nights),美索不達米亞文學作品《吉爾伽美什史詩》(The Epic of Gilgamesh)等等。(Alber,2011:47)。因此對古英語史詩的超自然場景和事件的“常規化”解讀,推動了中世紀奇幻故事體裁的形成和發展。
還有在18世紀流行的連環小說或物件敘事這一文類中,作者創造的諷刺性敘事大多不是人類敘述者,而是沒有生命的物件。在本文看來,正是動物寓言的常規化推動了物件敘事的發展。馬克·特納(Mark Turner)指出“會說話的動物是一種明顯的融合現象,在兒童文學中十分常見”(Turner,2002:13)。例如早期的伊索寓言包含許多“會說話的動物”,它們談論和嘲笑人類的錯誤。這種會說話的動物早已常規化并轉化到讀者的認知范疇中。當讀者遇到“物件敘述者”時,就會利用已有的認知參數,以動物敘述者為范本,逐漸接受小說世界中的物件敘述者(Alber,2011:50)。所以對寓言故事的“常規化”解讀推動了物件敘事這一文類的形成和發展。
奇幻的超自然敘事這一體裁對讀者來說并不陌生,因為中世紀的神話故事和之后的玄幻小說都充斥著大量的超自然元素。“鬼魂、吸血鬼、狼人、巫師等超自然生物以及預言、符咒、占卜等超自然事件在物質世界中是不可能發生的”(Ronen,1994:55),這都屬于反常規元素。“中世紀的神話故事已經成為文學作品中的“常規化”現象了,讀者已將其轉化為基本的認知模式”(Alber,2011:52)。當中世紀的超自然敘事逐漸成為常規化的敘事時,后期奇幻的超自然敘事則在此基礎上加入反常規元素,并使之集中化、激進化,從而變成新的文類形態,促進了文類的創新。
同樣的例子還有現代小說中的讀心術、科幻小說中不可能的時間等,這些文類都是在常規化解讀之后得以創新和發展。從宏觀來看,后現代主義中的反常規場景和事件的創新和發展也得益于對反常規敘事的解讀,因為后現代主義“把這些‘常規化’的反常規現象集中化和激進化,使得敘事文本再次變得特殊并產生陌生化的效果(Alber,2016:437)。”因此換言之,解讀反常規敘事使之常規化有利于文類的創新,“常規化”的反常規敘事就是推動文類創新和發展的動力。
4.結論
盡管反常規敘事發展相對晚近,但是在引發敘事學界關注的同時,也引發了諸多批評與爭議。學者們對反常規敘事進行了多重定義,并將反常規敘事分為“未常規化”的反常規敘事和“常規化”的反常規敘事。對于“常規化”的反常規敘事,讀者不再感到陌生或疑惑,而是很容易接受它們就是故事世界的一部分。對于“未常規化”的反常規敘事,讀者可以擴展認知范疇,把“未常規化”的反常規敘事解讀為“常規化”的反常規敘事。同時,解讀“常規化”的反常規敘事對文類的形成與發展意義重大,例如史詩、中世紀奇幻故事、18世紀的物件敘事、奇幻的超自然敘事、含有讀心術的現代小說、包含不可能的時間的科學小說等文類的發展都離不開“常規化”的反常規敘事。“常規化”的反常規敘事是敘事領域的重要命題,目前研究還遠遠不夠,由于篇幅有限,本文無法進一步展開,以后再撰文深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