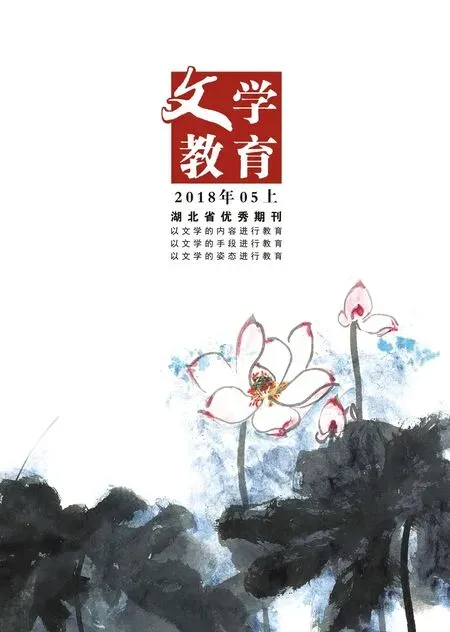新文體派研究
徐月蓉
(作者介紹:徐月蓉,贛南師范大學2015級中國語言文學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古代文學)
一.新文體的內涵及演變過程
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提到了新文體的特點、形式。新文體的最終形成有賴于梁啟超,但是在梁啟超之前已經出現了新文體思想的萌芽。
1.萌芽——桐城派
在桐城派發展的后期,已有不少桐城派學者在創作實踐中提出了新的文論主張,這些新主張可以被認為是新文體的萌芽。其中梅曾亮、馮桂芬及薛福成最具代表性。
梅曾亮的作品大體遵從桐城派理論,但較之其他桐城派作家,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打破森嚴的壁壘,吸收其他文論思想的長處。
馮桂芬指出了桐城派散文理論的弊病,在理論上明確宣說“獨不信義法之說”。,在承認“文以載道”的基礎上對“道”的內容作了新的解釋,突破了“道統”的限制,較之梅曾亮有很大的進步。
薛福成的作品大體上探討的是現實問題;語言上追求樸實自然,語調通暢并且大量采用漢譯新名詞;注重多種修辭手法的運用。
從梅曾亮到馮桂芬,再到薛福成,他們根據社會發展情況不斷提出與之適應的新的文論主張,既是對桐城派固有文學模式的打破,也為新文體的產生創造了條件。
2.形成與發展——從“報章文”到“時務文”
早期的“報章文”寫作有固定的模式:先立論,再舉例論證,最后總結。這種固定模式的寫作隨社會的發展逐漸顯露出弊端,因此被世人所改造,王韜是對這一文章進行改造的代表作家。
王韜在主持《循環日報》時,在報上大肆發表改良革新的文字,由此真正確立了“報章體”文體。順應之后的思想解放潮流,中國的近代報刊業發展迅速,其中最有影響力的報刊是《時務報》,該報討論的是當時社會政治、思想文化所最關心的時代課題,直截了當,觀點鮮明,大處著眼,高屋建領,由此成為中國輿論的中心;在該報上發表文章的,可以稱之為當時中國一流的思想家和報章文作家,其中在梁啟超的示范下,“時務文”在更大的范圍內被推廣接受,大致形成了一時代的文體文風。
3.確立——梁啟超的“新民體”
梁啟超在近代新文體發展史上,具有突出的貢獻。他擴大了“時務文”的影響,更為重要的是對“時務文”的再改造,使近代散文進入又一個具有相對獨立性的“新民體”階段。他晚年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所追述概括的“新文體”的種種特色特點,在他創辦《新民叢報》時期就已經形成,而且各種特色特點也互為聯系,構成一個整體。
二.新文體的特征
1.語言特色——兼收并蓄、推陳出新
新文體中使用的語言,是梁氏在長期的散文創作實踐中,打破一切清規戒律,兼收并蓄、推陳出新的結果,具體表現在:
雜以外國語法。梁啟超1899年發表的《論中國人種之將來》中“仿效日本文體”即是采用日語語法組織詞句。
梁啟超打破了一切傳統的戒律,熔鑄古今、中外、新舊的各種名詞術語、語調句法而集其大成,形成土洋結合、文白摻半的格調,并進而發揮其優長,成為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語言藝術大師。
2.修辭特色——靈活多變、氣勢恢宏
梁啟超常常巧用比喻、排比、設問等修辭手法,使文章酣放自態、縱橫宕蕩,給讀者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
復式比喻。梁啟超擅長用比喻,而且很少單薄的、獨立的使用單個的比喻句,總是將若干個比喻并列連串起來,構成復式比喻。
排比。梁啟超善于運用排比,他有時破奇為偶,用一連串的排偶句來增強筆力氣勢,使人感到文章有一種內在的旋律;有時又奇偶互用,使文章有跌宕多姿之美。
3.筆鋒帶情——情理交織、以情動人
梁啟超善于在筆端傾注充沛的情感,動人心魂,產生極大的鼓動性、說服力和感染力。《呵旁觀者文》合議論與抒情于一體,變現對于“旁觀者”的極端痛恨與仇視,具有極強的藝術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