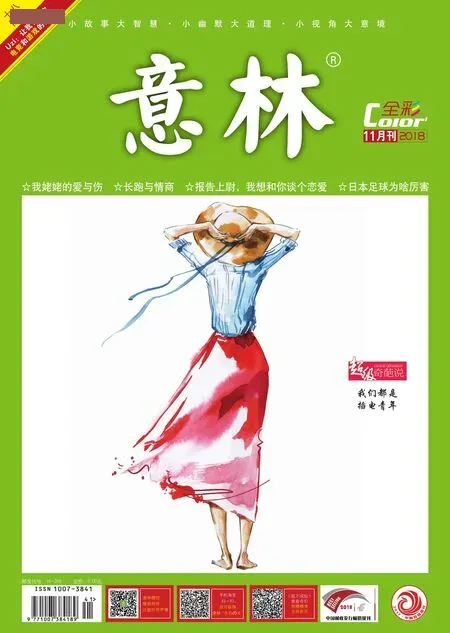雞、餓與鄉愁
□權 蓉

想吃雞,晚上就夢見了。雞是爸爸現殺的,我燒滾了水端去幫著燙毛。準備切塊的時候,刀不應手,去換了把刀,雞讓旁邊的貓叼走了,我舉著刀就奔過去追,結果跑太快,跌了一跤,醒了。迷迷糊糊睡過去,又夢見燉雞,拿著勺在一個大鐵鍋里攪,撈起一塊聞了聞,沒舍得吃,放回去說再燉燉。然后備料,洗了半碗冬筍,泡了半碗春耳,手里在切臘肉絲,想等切完放進燉著雞的鍋里去煨著,然后一刀切了手,又醒了。費了半天工夫,終是一口沒有吃著。
家里的雞是放養的,只有春天剛種上種子怕它們去刨食才會關起來,因為運動量大,活動范圍廣,所以一個個根本沒有市場上的雞肉肥油光,都是顯瘦派的。
家里每次燉雞,老遠就能聞到香味,而且肉咬起來筋道,就連隔夜的雞湯兌上水,新煮把菜都是香的。不像超市里的雞肉,一樣的做法,入口卻是柴的。
在鄉下,如有人去,要給燉只雞,差不多代表最高敬意。因為家里的雞大都是養來生蛋的,而且要殺一只放養的雞,是很費力費工的事。
要捉雞,就得半夜或者天沒亮去抓,否則天稍亮,雞們就起來覓食去了;就算喂食時它們回來,也一個個眼觀六路耳聽八方,一有不對就四散跑了。人們說鄉里的誰吝嗇,就說他每次大中午的要請人吃雞。
春天孵出來的小雞,毛茸茸黃糯糯的,嘰嘰喳喳跟在母雞后面,去田間地頭探險。再長一長,到夏天,毛長出來一襯,大了些,名字也改了,叫子雞。聽說子雞很好吃,摘同樣新結出來不久還不那么辣的朝天椒,加菜油燒熱,辣椒切絲,子雞切丁,爆炒,起鍋。
不過這是我們家的禁菜,子雞歷來是不讓吃的。
書上說雞的壽命有20年,鄉下家養的雞是活不到這么久的,不過聽奶奶講,有只雞是個例外。那家太婆去算命,那算命的說想一生平順,把回家時遇到的第一個湊上來的活物一直養著。太婆回家,她孫子正在攆雞玩兒,一只白母雞跑得急,一頭撞到太婆面前,她剛抬腿想一腳踢過去,想起算命人的話,便放下腳,從此養著這只白母雞。
那雞就一直長,養了十多年,后來死了,在屋后挖坑埋了。誰知讓鄰家的狗給刨出來叼了去,太婆去鄰家吵架,把自己氣著,沒站穩,摔了一跤,沒多久,人就沒了。
這算命的到底靈不靈,還真不好說。
我們管公雞叫雞公,母雞叫雞母,小時候有只紅雞公老啄我,后來我就怕雞。小學同學們做毽子,我也想要一個,卻對雞公望而卻步,怎么都沒勇氣去捉它過來拔毛,最后悻悻地拖了兩只黑白雞母過來。雞母的毛不細,不翹,粗愣愣的,為了好看,我把它倆的毛錯開綁,黑白相間的,自覺比別人的毽子醒目好多。
誰知道學校里沒有一個人是用雞母毛做毽子的,我為此被嘲笑了好久。哭著回去,爺爺問怎么了,說我的毽子是雞母毛做的,別人笑我。爺爺去捉了雞公來,拔了毛重新給我綁了個毽子,我卻再也沒有帶它去學校,也沒有踢過。
給我媽講我的夢,說怎么也沒吃到嘴。她說,你過年時回來多吃兩只。
朋友說,你這是強烈想家,說文藝點,叫鄉愁。
鄉愁嗎?它們是王維綺窗前的寒梅,是余光中的海棠紅,是席慕蓉沒有年輪的樹。
而凡俗如我,可能就是這種想念吃一只燉雞的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