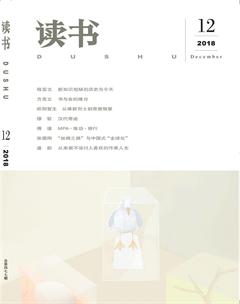東邊用武力,西邊講法律
在一八九八年美西戰爭中戰勝西班牙后,美國迅速成為新帝國主義國家,愈加想擺脫以歐洲為中心的舊世界秩序,創建屬于自己的新世界秩序。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見證了歐洲老牌帝國主義國家的衰落;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二年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則標志著戰后新世界秩序的重新締造。盡管美國參議院最終否決《凡爾賽和約》,拒絕參加國際聯盟與國際常設法院的事實給世人造成了美國缺席的錯覺,但實際上,正是在一八九八至一九二二年之間,美國奠定了其新世界秩序的基礎。博伊爾教授的《國際秩序:國際關系的法律主義進路1898—1922》一書,以法學家的視角重新詮釋了政治學家與歷史學家所引用過或未曾解讀過的國際關系文獻,全景式地凸顯了國際法與國際組織在美國創建新世界秩序方面的關鍵作用。書中并未回避這一時期美國在東西兩個半球區分別使用法律和武力兩種方法來實現帝國崛起,這對思考今日世界格局仍有啟發。
東半球:使用法律阻止武力升級
在東半球,使用國際法與國際組織的新機制來規制國際關系中的跨國威脅和武力使用,成為美國避免歐洲列強之間發生大的戰爭從而威脅到自身利益的重要方式。博伊爾指出,這一進路的選擇與當時美國國際法學家的倡導密切相關,這種防止戰爭的法律主義新機制主要涉及國際仲裁、國際法院、編纂國際習慣法、限制軍備、定期召開和平會議等五項要素。
美國是國際仲裁運動與國際法院計劃的積極推動者。連續兩任國務卿約翰·海伊與伊萊休·魯特代表美國與外國政府簽署了一系列關于強制仲裁的一般仲裁條約,力圖使強制仲裁國際爭端成為戰爭的替代品。由于認為具有司法性的判決比妥協性的仲裁更加嚴格公正,美國代表團也曾以美國最高法院為藍本先后在兩次海牙和平會議提出國際法院方案,只是未被采納。“一戰”后《國際聯盟盟約》與《國際常設法院規約》將簡單的常設仲裁法院演變成復雜的國際常設法院,美國雖沒有加入國際聯盟,但大多數美國國際法學家支持參與國際常設法院。
兩次海牙會議編纂的關于陸戰和海戰的中立公約,連同未被批準的《倫敦宣言》,在“一戰”期間既構成了中立航運和商業保護的基本權利和義務框架,也成為中立國判斷合法與非法、正確與錯誤、正義與非正義的重要根據。博伊爾認為,美國最終放棄中立,選擇對德國宣戰,正是為了維護海戰和中立的國際習慣法和協約法。兩次海牙和平會議基于人道主義的考慮通過了禁止使用某種類型武器的宣言,未能就全面限制軍備采取實質性措施,這一問題直到“一戰”后在美國召集的華盛頓海軍會議上才取得重大突破。
美國國務卿布賴恩在“一戰”前建議第三次海牙和平會議于一九一六年六月舉行,其國際籌備委員會的職責交由從常設仲裁法院理事會成員中自行選出的委員會,由于“一戰”爆發,第三次海牙和平會議未能實現。最終各國定期召開和平會議的法律主義目標以國際聯盟的形式落實。
西半球:使用法律加持武力干涉
上述美國在東半球的防止戰爭方案的五項要素,即仲裁、判決、編纂、裁軍以及定期召開和平會議也被美國推進到西半球。然而十九世紀末美國已成為西半球地緣政治的積極參與者和公認的主導力量,其在該地區的外交政策也因此與東半球存在實質性差異。在東半球,美國運用國際法與國際組織的法律主義新機制來避免歐洲列強之間的武力升級;而在西半球的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區,美國則試圖通過國際法與國際組織來為其帝國主義武力干涉辯護。
自一八九八年開始,美國即將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區納入其勢力范圍,甚至將其等同為殖民地,應對墨西哥、中美洲及加勒比地區政治和經濟不穩定問題時,徑直采取軍事干涉和武裝占領等簡單粗暴的辦法。這種干涉主義外交政策違反了美國在全球國際關系體系內積極推動的普適情感、哲學原則和國際公約,也與其正主動創建的美洲地區內部的國際法與國際組織進程背道而馳。博伊爾直言,帝國干涉主義的惡果長期困擾著美國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區的外交政策。
一八九八至一九二二年間,美國所有外交政策的焦點集中于門羅主義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區的正確解釋。門羅主義本是為了防止歐洲列強幫助西班牙重新奪回拉丁美洲領土的政策,從拉丁美洲的角度來看,其理論的最初界定并不令人反感。真正的問題源于西奧多·羅斯福總統于一九0四年十二月六日在國會的年度咨文中宣布的所謂門羅主義的羅斯福推論,憑借這一推論,美國已成為在西半球執行國際法的“警察”,這招致了拉丁美洲國家的極端厭惡。
博伊爾指出,當時大多數美國國際法學家贊成羅斯福新頒布的門羅主義干涉主義解釋,他們還以“減少國際妨害”和“維護國際法與國際秩序的特殊權利和普遍利益”等似是而非的理由,為美國在拉丁美洲的武力干涉和長期占領辯護。根據美國法律主義帝國邏輯,美國必須幫助美洲其他國家在國際關系和國內事務上向更高層次的文明和自治邁進,然而,在它們到達這個階段之前不能適用使其免于成為美國帝國主義保護國的國際法的不干涉原則。
全球法律主義:為了世界和平
美國在東西半球的外交政策,在原則上不無悖謬,在西半球所謂慈善和利他主義政策背后隱藏的國際強權政治傾向、軍事戰略和經濟利益的考量,卻為許多美國國際法學家選擇性地視而不見。依照“一戰”前美國國際法學家的觀點,始于美西戰爭的美國世界帝國主義,偏離了基于個人不可剝奪的權利、人民自決、國家主權平等和獨立、不干涉、尊重國際法以及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外交政策傳統理想,這是美國面臨的主要哲學困境。正如博伊爾所言,這些美國國際法學家最合適歸類為“法律現實主義者”,這解釋了為什么美國在東西半球都推行國際法與國際組織,卻在法律、強權兩者之間有不同的側重。而隨后的歷史證明,相較于法律外交,強權外交不僅有損于世界和平,也讓美國的國際關系乃至國內政治愈加糟糕。
美國的門羅主義和羅斯福推論可以阻止歐洲重新控制拉丁美洲,其“門戶開放”政策則讓列強在中國維持某種程度的權力平衡。絕大多數美國國際法學家認為,當歐洲發生大戰時,孤立主義將確保不會危及美國在遠東地區新獲得的財產及在拉丁美洲的霸權地位,而國際中立法則將允許美國商人從交戰雙方的貿易中獲得可觀利潤。因此,美國向國際社會成員積極推動國際法與國際組織的外交政策至關重要,這樣可以防止將美國拉入歐洲大戰,保持距離,最安全、最有效地保護自己和全世界,從而在促進國際法與國際組織方面發揮領導作用,并在新世界秩序中逐漸成為主導力量。
世界的和平、安全、正義和公平是全人類共同的目標與福祉,而這些離不開國際法與國際組織的完善,它們不僅可以限制大國強權,也是弱國保護自身利益的武器。美國法律主義者的宏偉目標正是以健全的國際法與國際組織為根基,建立起防止戰爭和確保和平的國際秩序,在一八九八至一九二二年間,美國國際法學家團體也確實比自建國以來的任何時期都更深遠地影響著美國外交政策的形成,并取得了不可忽略的成果。即使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也并沒有退回到華盛頓告別演說以來的傳統孤立主義的外交政策,而是繼續積極促進國際法與國際組織的建設,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國法律主義者努力的結果。
我們需要警醒的是,美國在東西兩個半球不同的外交政策表明,國際法與國際組織有可能淪為強權的工具。當今國際現實中馬基雅維里強權政治的復雜性更是加重了全球法律主義危機。盡管如此,這也不能抹殺國際法與國際組織在維護世界和平方面的必要性與重要性。
(《國際秩序:國際關系的法律主義進路1898—1922》,[美]弗朗西斯·安東尼·博伊爾著,顏麗媛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