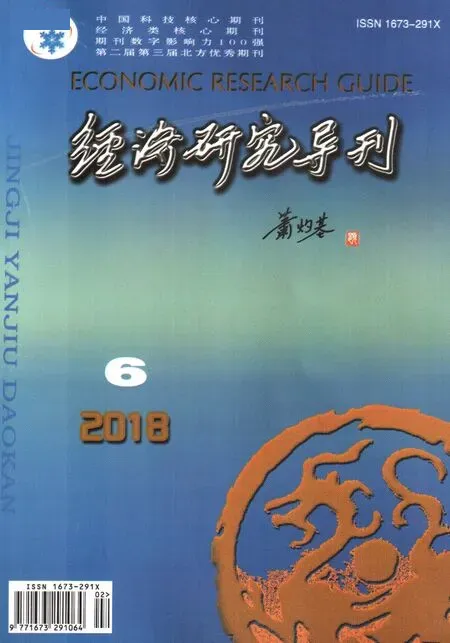全球化與“一帶一路”的差異性探究
吳 偉
(上海財(cái)經(jīng)大學(xué)人文學(xué)院,上海 213000)
全球化是人類社會(huì)歷史活動(dòng)的新形式,打破了以往等級(jí)制社會(huì)的地區(qū)、民族、國(guó)家的限制。一般認(rèn)為,全球化發(fā)源于15世紀(jì)的地理大發(fā)現(xiàn),人類的活動(dòng)由陸地轉(zhuǎn)向海洋。從工業(yè)革命到信息時(shí)代,全球化伴隨著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的擴(kuò)張成為人類社會(huì)的主要發(fā)展形態(tài)。20世紀(jì)70年代凱恩斯主義政策失靈,各國(guó)紛紛轉(zhuǎn)向新自由主義,加速世界經(jīng)濟(jì)政治的全球一體化轉(zhuǎn)向。21世紀(jì)后,全球化取得了巨大的經(jīng)濟(jì)成果,推動(dòng)人類社會(huì)生產(chǎn)力發(fā)展的同時(shí)也帶了全球范圍內(nèi)的社會(huì)問(wèn)題與危機(jī),即全球化的“雙重效應(yīng)”。筆者認(rèn)為,只有正確剖析“什么是全球化?”的深層本質(zhì),才能從本源上區(qū)別“一帶一路”戰(zhàn)略與全球化的不同之處,才能在實(shí)踐中探索解決全球化困境的機(jī)制。
一、全球化的本質(zhì):資本擴(kuò)張
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取代等級(jí)制社會(huì)的生產(chǎn)方式,展現(xiàn)出自身先進(jìn)的生產(chǎn)力。資本的本性是價(jià)值增殖,無(wú)限追逐剩余價(jià)值,資本的發(fā)展趨勢(shì)就是把一切社會(huì)的生產(chǎn)方式轉(zhuǎn)變?yōu)橘Y本驅(qū)動(dòng)的生產(chǎn)方式,通過(guò)不斷擴(kuò)張流通范圍實(shí)現(xiàn)資本的“生產(chǎn)—消費(fèi)”流轉(zhuǎn)。資本的擴(kuò)張成為世界性的解放力量,取消一切地域、民族、國(guó)家的界限,因此,全球化是資本擴(kuò)張的應(yīng)有之義。資本不斷提高和發(fā)展生產(chǎn)力,把自然界變成屬人的自然界,形成全球化的感性活動(dòng)的屬性。
資本全球化擴(kuò)張的同時(shí)也產(chǎn)生阻礙自身運(yùn)行的對(duì)立力量,導(dǎo)致資本擴(kuò)張動(dòng)力的喪失。資本擴(kuò)張依托全球化,以資本、技術(shù)、市場(chǎng)為手段把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拓展到發(fā)展中國(guó)家。資本的全球化分為以下幾個(gè)層次:第一,勞動(dòng)者的自然力;第二,自然資源的自然力;第三,社會(huì)總體性勞動(dòng)的自然力。在全球化的歷程中,發(fā)展中國(guó)家利用外國(guó)資本發(fā)展本國(guó)生產(chǎn)力,僅僅一小部分由于自身?xiàng)l件的不同,完成了資本主義改造,大部分發(fā)展中國(guó)家最終成為資本全球化悖論的承擔(dān)者。發(fā)達(dá)國(guó)家通過(guò)全球化把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的矛盾(經(jīng)濟(jì)危機(jī)、生態(tài)危機(jī)、社會(huì)危機(jī))隨著資本的轉(zhuǎn)移一起轉(zhuǎn)嫁給發(fā)展中國(guó)家。發(fā)達(dá)國(guó)家的資本積累建立在發(fā)展中國(guó)家的“貧困積累”之上,以此支撐發(fā)達(dá)國(guó)家的政府公共開支和社會(huì)保障體系,緩和并延緩發(fā)達(dá)國(guó)家體系內(nèi)部的經(jīng)濟(jì)危機(jī)與社會(huì)危機(jī),換取發(fā)達(dá)國(guó)家的“藍(lán)天白云”。資本全球化擴(kuò)張的同時(shí)也產(chǎn)生阻礙自身運(yùn)行的對(duì)立力量,導(dǎo)致資本擴(kuò)張動(dòng)力的喪失。上述的各種危機(jī)通過(guò)資本全球化網(wǎng)絡(luò)又反饋到發(fā)達(dá)國(guó)家自身,產(chǎn)生了全球治理視域內(nèi)的表象性問(wèn)題。
二、“一帶一路”:對(duì)全球化的否定與現(xiàn)實(shí)性超越
全球化從本質(zhì)上不同于“一帶一路”,兩者的社會(huì)基礎(chǔ)不同,但同時(shí)不能完全割裂兩者的關(guān)系。學(xué)界有這樣一些觀點(diǎn):第一,“一帶一路”等同于全球化4.0;第二,“一帶一路”的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等同于提供公共產(chǎn)品;第三,“一帶一路”只是單純的經(jīng)濟(jì)交往,共商共建共享只限于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不包含政治交往、文化交往,“一帶一路”并非推翻全球化領(lǐng)域下的國(guó)際架構(gòu)、國(guó)際安排和國(guó)際秩序;第四,符號(hào)化的“一帶一路”與古代的“絲綢之路”具有共同的“所指”。以上各種觀點(diǎn)的共同特征是:忽視了“一帶一路”與全球化的社會(huì)關(guān)系基礎(chǔ)。以全球化4.0表述“一帶一路”一方面從理論上消解了兩者的區(qū)別,另一方面在實(shí)踐中必然導(dǎo)致“一帶一路”重蹈全球化的資本悖論。以西方經(jīng)濟(jì)學(xué)的視域把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理解成公共產(chǎn)品,必然把“一帶一路”沿線國(guó)家原子化,最終陷入誰(shuí)提供公共產(chǎn)品的主體性的邏輯悖論。把“一帶一路”局限于經(jīng)濟(jì)交往,必然導(dǎo)致“一帶一路”發(fā)展的片面性,割裂社會(huì)的經(jīng)濟(jì)交往與政治、文化交往的相互聯(lián)系與相互作用,“一帶一路”建設(shè)必然引起資本主義力量主導(dǎo)的全球化視域下經(jīng)濟(jì)、政治、文化等各種社會(huì)結(jié)構(gòu)的變化;不能因?yàn)閲?guó)際社會(huì)上一些反對(duì)的聲音,就龜縮不前,不能因?yàn)椤爸袊?guó)威脅論”,就停滯發(fā)展“一帶一路”,聲稱“一帶一路”只限于經(jīng)濟(jì)合作,這是典型的拋棄中國(guó)社會(huì)基礎(chǔ)、在霸權(quán)主義面前投降的右傾主義路線;中國(guó)社會(huì)主義革命的偉大道路早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shí)期就用實(shí)踐證明了,這條右傾主義道路是走不通的,是被中國(guó)人民的革命實(shí)踐所拋棄的,中國(guó)社會(huì)主義革命的成果也是付出沉重代價(jià)的結(jié)果。在21世紀(jì),這種右傾主義的新表現(xiàn)形式嚴(yán)重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的理論思想,只局限于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必然導(dǎo)致“一帶一路”的發(fā)展被資本力量所控制。“一帶一路”繼承了古代社會(huì)交往精神,但必須從目前國(guó)情出發(fā),發(fā)掘“一帶一路”的異質(zhì)性與時(shí)代性,不能限制于古代海上與陸上“絲綢之路”的固有和傳統(tǒng)模式,深刻理解其符號(hào)性,必須在實(shí)踐中豐富“一帶一路”的新內(nèi)涵,克服全球化的資本擴(kuò)張邏輯悖論。因此,“一帶一路”是對(duì)全球化與逆全球化的現(xiàn)實(shí)性超越。
三、“一帶一路”:人類命運(yùn)共同體的新實(shí)踐
“一帶一路”從我國(guó)國(guó)情出發(fā),具有中華民族社會(huì)活動(dòng)的歷史積累性,是中國(guó)人民實(shí)現(xiàn)自我發(fā)展的新需要。承載著和平共處五項(xiàng)原則、南南合作、南北合作、改革開放的歷史內(nèi)涵,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理解為“五大發(fā)展理念”在國(guó)際領(lǐng)域的延伸和現(xiàn)實(shí)展開。“一帶一路”沿線大部分國(guó)家是資本悖論的實(shí)際承擔(dān)者,共商、共享、共建是對(duì)克服資本力量主導(dǎo)的全球化的社會(huì)普遍問(wèn)題的現(xiàn)實(shí)需要。
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所主導(dǎo)的全球化也形成了人類社會(huì)共同體,其把世界歷史交往的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變成物與物的關(guān)系,逆全球化、民粹主義、保護(hù)主義等是這種社會(huì)共同體的自身悖論與現(xiàn)實(shí)矛盾。實(shí)踐證明,資本擴(kuò)張全球化形成的社會(huì)共同體是不可持續(xù)的。但其積極性是為共產(chǎn)主義力量主導(dǎo)的人類命運(yùn)共同體奠定了一定的物質(zhì)基礎(chǔ),“一帶一路”建設(shè)的核心內(nèi)涵正是探索人類命運(yùn)共同體的新實(shí)踐。
[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4]魯品越.鮮活的資本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