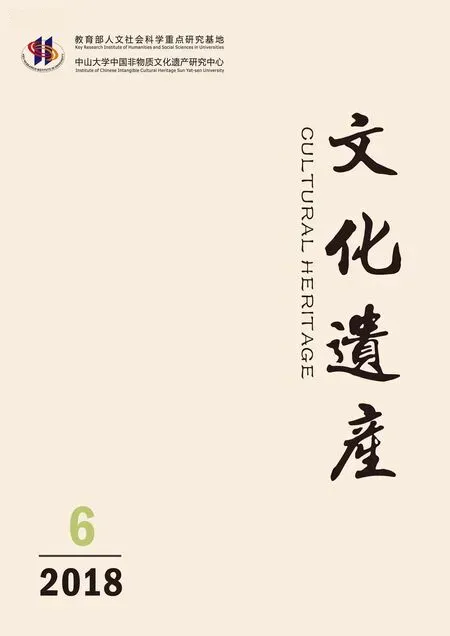“神圣空間”的理論建構與文化表征*
王子涵
當宗教信仰作為文化最高“抽象性”滲透到具象的聚落空間之中,就凝結為一種神圣空間構造方式,它在很大程度同諸多“社會空間”一樣,利用建筑空間的布局與裝飾,超越了純粹的物理空間、審美空間,從而生成為一種“意義空間”。對于“神圣空間”的理解,深刻地關涉如下問題:在宗教文化中,“抽象”與“具象”、“神圣”與“世俗”、“存在”與“虛無”在何種程度上、又以何種方式形成一種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辯證關系?而對于“神圣空間”的理解,不同理論脈絡提供了可資借鑒的“視點”,本文將聚焦于“神圣空間”的宗教學源流,力圖在概念層面勾勒關于神圣空間理解的全面圖景,進而嘗試結合中國宗教文化傳統,對此予以評價與反思。
一、神圣與世俗:宗教學范式下的空間理論
人們對于空間的認知跨越了亞里士多德至牛頓奠定的均質空間、純物理空間,發展為與感知生成高度交融的意義空間。海德格爾基于對“此在”(dasein)的關懷將“空間”論證作為人類生活的基本方式,認為唯有通過空間的建構才得以實現天——地——神——人*馬丁·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陳嘉映、王慶節譯,上海:三聯書店2006年,第126頁。的四元結合,從而將純物理的世界構建為人在其中有所歸屬的世界。梅洛—龐蒂進一步指出*莫里斯·梅洛—龐蒂:《知覺現象學》,姜志輝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140頁。,通過營造,空間結構能夠超越自身所處的天然環境,與人的感知結構形成一種“同構”與“互證”的關系。從社會學視角理解,布爾迪厄提出“場域”可以為神圣空間的生成提供更加富有實踐觀照的理解。他認為,“一個場域可以被定義為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或一個架構。”*皮埃爾·布迪厄、華康德:《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李猛、李康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第133-134頁:“正是在這些位置的存在和他們強加于占據特定位置的行動者或機構之上的決定性因素之中,這些位置得到了客觀的界定,其根據是這些位置在不同類型的權利或資本(占有這些權利就意味著把持了在這一場域中利害攸關的專門利潤的得益權)的分配結構中實際的和潛在的處境,以及它們與其他位置之間的客觀關系(支配關系、屈從關系、結構上的同源關系等)”。具有不同“慣習”*周冬霞:《論布迪厄理論的三個概念工具——對實踐、慣習、場域概念的解析》,《改革與開放》2010年1期。的主體因在場域中位置秩序的差異性而掌握著不同程度的資源。作為擁有社會行為的實踐主體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之下,為了獲取資源而進行競爭或合作,以推動場域的動態發展。以愛德華·索加(Edward W.Soja)*愛德華·W·蘇賈:《后現代地理學—重申批判社會理論中的空間》,王文斌譯,北京:商務印出版社2017年,第120-122頁:在這個框架中一個基礎性的概念劃分就是“空間”(space)與“空間性”(spatiality)的區別。空間性形成于空間,又偶然于空間。索加認為,前者指的是空間本身,是一個既定的自然條件,而后者則是以社會為基礎,由社會組織或創造的空間,它既是各種社會關系、社會結構具體化,而作為空間化的結果,它又是新一輪社會生產與活動的前提與假設。和大衛·哈維(David.Harvey)為代表的文化地理學則不試圖從時間維度、歷史維度去分析一個地方的形成背景,而是將不同的空間因素作為分析的基本框架。
綜上所述,自20世紀以來,純物理性的空間觀念開始不斷地經受哲學與社會學的突破與挑戰,契合這一趨勢,宗教學視域力圖從本質上將空間闡述為人與世界、人與社會互動的中介環節,從而將其視為意義生成、感知生成、社會關系生成的非中立性載體。但是與哲學、社會學不同的地方在于,宗教學視域更加聚焦地從“神圣”與“世俗”的劃分出發去理解空間的中介功能與載體性質。正如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所說:“人在直立行走后對世界的感知就有了上下左右的方位維度,也就是說空間(尤其以人為中心來定位的“空間”)是人們認識和把握世界的重要依據,人們認知神圣與世俗也是如此。”*金澤:《如何理解宗教的“神圣性”》,《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6期。所以宗教學視域在將“物的空間”塑造為“人的空間”的基礎上,進一步將“人的空間”塑造為“神圣/世俗的空間”。在《神圣與世俗》的導言部分,伊利亞德對于“神圣”做出了極為簡潔的定義:即“神圣是世俗的反面”*伊利亞德:《宗教思想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第233-267頁。所以“神圣”與“世俗”首先是一對“異質性”*涂爾干(Emile Durkheim)早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LesFormes ElémenttariesdelaVieReligieuse, 1912) 中便已指出過,“這種異質性極其徹底,繼而往往會形成一種名副其實的對立”;“在人類思想的所有歷史中,事物的兩種范疇還從來沒有出現過如此截然不同、如此勢不兩立的局面”。概念。涂爾干(Emile Durkheim)早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中也已指出,“這種異質性極其徹底,繼而往往會形成一種名副其實的對立”;“在人類思想的所有歷史中,事物的兩種范疇還從來沒有出現過如此截然不同、如此勢不兩立的局面”。*涂爾干(Emile Durkheim):《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敬東、汲喆譯,北京:世紀出版集團2010年,第34-35頁。
進而伊利亞德正面闡述了神圣空間的性質,它既是一種通過人工營造界定的一個相對完整而封閉的“物理空間”,同時又不局限于此,而賦予該空間內的一器一物、一草一木以“神圣性*“神圣”(the sacred)與“世俗”(the profane)這對范疇來自拉丁語,詞源涉及人們在空間上的劃分。拉丁語sacrum意味著屬于神靈及其力量,但羅馬人實際上用它來指謂膜拜儀式極其場所,即它原本關聯的是圣殿以及在其中或周圍舉行的儀式。”的結構化表述。而在從“神圣性/世俗性”的概念語境轉移至“神圣空間/世俗空間”的概念語境后,二者的關系就不再是單純的異質性。伊利亞德認為神圣性是特定場域內所賦有的儀式空間感的一種帶有宗教儀式感的屬性,而構成神圣性的即存在于人類日常的生產與生活之中。這就標識了神圣空間與世俗空間之間并非是固化的、絕對對立的關系,而是一種動態的、辯證的關系。伊利亞德認為,就“空間”本體概念而言并不具有“均質性或同質性(homogeneity)”,而存在于神圣空間與世俗空間的異質性集中表現在這種異質性(nonhomogeneity)上。換言之,非均質的、混沌的世俗空間其本身就具有生成斷裂的本性,“而神圣空間正是這樣一種均質空間的斷裂,并由此確立一個中軸線,建構起不同質的空間秩序”*張俊:《神圣空間與信仰》,《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 年第7 期。。如金澤教授指出的,“平日的世俗空間一旦具備(或布置)了各種儀式要素,在某個特定的時刻或特定的事件中就可以轉換成神圣的空間。”*金澤:《如何理解宗教的“神圣性”》,《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6期。由此,伊利亞德就將對神圣空間的界定為一種基于“世俗空間”非均質性的動態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世俗空間由不一致而產生斷裂,由斷裂產生“異己”的空間,即神圣空間。
除了“世俗空間”的非均質性,“神圣/世俗”的劃分同樣具有一種發生學背景。伊利亞德認為在古代社會,人們會認為“神圣飽含存在(being)”,“圣神”意味著真實的、絕對的、存在的權力(power)。這一認知傾向促使人們試圖通過神圣的“存在”所賦予事物真實可感的靈性獲得神秘的力量,從而為人類的宗教情感提供持久、不朽的超驗感應。由此,人們傾向于向神圣領域靠近,以求獲取神圣的力量并將其攜帶至現實生活之中。可見,“神圣/世俗”的辯證法自人類宗教文化肇始之初就內在于神圣空間,人類對于圣神力量的渴望超越了神圣場域內描繪一個虛幻世界的愿景,而拓展至對現實世界的靈驗渴望。進而我們會看到,“神圣/世俗”這一對辯證范疇,它們的相互轉化也會表現為一系列其他的對立統一的范疇:存在/虛無,實在/幻想,世界/混沌,秩序/無序,等等,唯有在這一延伸的理論脈絡中,我們才能更加全面而透徹地認知神圣空間如何在與非神圣空間的矛盾與轉化中獲得自身的獨立屬性。
二、建構、功能與編碼: 神圣空間的綜合闡述
綜上所述,由伊利亞德奠定的“神圣/世俗”這一對辯證范疇確立了宗教學研究神圣空間的基本范式,隨著宗教學發展,這一范式被更為具體地考察于神圣空間生成的每一個環節,這些環節可以被分解為建構、功能與編碼三個部分,由此形成了對于神圣空間更為全面的理論結構,實現了對于“神圣空間”概念演繹與實踐歸納的綜合闡述。
(一)固化與延展——神圣空間的建構
宗教在儀式踐行的過程中,其長期占據的空間會產生超驗化與結構化的傾向,從而脫離世俗空間,形成神圣空間建構的基本要素:第一,宗教的功能性。神圣空間的構成應具有宗教意義及精神力量,并通過隱喻形成宗教概念的表征。它將作為媒介把人、事、物與信仰關聯起來,為信仰者塑造神圣秩序并生成神圣意涵;第二,空間的多樣性。宗教意義背景下生成的神圣空間與非神圣空間在不同的條件之下具有不同的屬性及意義,而宗教的構成要素是衡量一個空間是否具備神圣性的重要標準;第三,主體回應的神秘性。神圣之地應具有喚醒情感回應的神秘力量。Schleiermacher 所闡述的并由Rudolf Otto發展的傳統,將宗教情感建立在對神圣空間的感知之上,而這一宗教意義生成的力量可以賦予一個地方形態或一個客觀事物以獨特的神圣感,由此在神圣的空間與神圣的情感之間形成一種相互回應、相互印證的共鳴。
通過對神圣空間的建構要素的梳理,我們能夠提煉出神圣空間的建構首先具有固定性特征,但同時也具有延展性傾向。關于固定性特征,宗教學的基本判斷是,神圣空間的建立的核心特征在于它是一個跳脫出人類主觀臆斷、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過程。神圣空間內在的獨特性總是涉及到一個文化的終極背景,因此它不是在任意信念中就能創建的。基于這一觀點,有學者給出了關于神圣空間固定性的具體論證:第一,神圣空間的神圣性往往通過構成傳統社會的整個文化基礎的敘述表達出來;第二,在一個充滿神圣地方或建筑里,神圣空間擁有某種程度上的特征、意義或者某一種物體,使其與周圍鮮明的分離,而具有這種神圣的意象特征是神靈的自我顯現,并非出自于人的創造;第三,神靈通過對某一空間的特定標記傳遞出特殊的神圣性,動物(作為信使)或著事物經常被神靈選擇作為標記的要素;第四,神圣空間具有吸附傳奇經典的故事傳說的屬性,在歷史上曾經發生過具有宗教意義事件的地點,會使其具有神圣性;第五,神圣的遺存也會賦予所處空間以神圣性;第六,地理形態也會賦予其神圣性和意義。神靈出現于多元復雜文化交織下的地方形態,不同的地方形態意味著不同神靈的庇護*參見Lindsay Jones,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Thomson Gale Press 2005(eds), 2nd Ed. Vol.12. p. 7978-7986. 中譯本未出版。。
關于延展性,宗教學研究同樣也展示了,假若確立神圣之地的確定性以及特殊性的趨勢是普遍的,那么也存在一種否定將神圣定點化的趨勢。在宗教學視域中,確立神圣之地固定化與否定神圣之地定點化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同時存在,并進行著博弈,前者基于一種客觀性觀念認為將神靈定位于固定的特殊點才可以保留此場域的神圣性,后者則基于一種主觀性觀念更傾向于神靈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尋得到。例如清真寺建筑就顯示了一個地方的神圣化與否定將神圣化在場地方化之間的張力*參見Lindsay Jones,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Thomson Gale Press 2005(eds), 2nd Ed. Vol.12. p. 7978-7986. 中譯本未出版。。清真寺承載了其他神圣地方的典型價值,在此,建筑作為神圣空間的象征媒介,延展了而非固化了宗教文化的深層涵義。因為在伊斯蘭國家,清真寺只是作為人們祈禱或舉行祭拜的公共空間場所,一般化的裝飾并不使其顯著區別于其他建筑,強調清真寺只是表達有意義的空間,而無法到達賦予該空間不可轉移的神圣價值。
可見,神圣空間的營造絕非只強調地點本身的特殊性,而是神靈賦予此地方某建筑或某載體以神圣的氣息,由此在神圣空間的固定性特征與延展性特征之間形成持續的張力。在此意義上,神圣空間的建構并不具備一個固定的模式,根植于不同地域、不同時期的宗教理念與宗教文化,不同宗教場域中的神圣空間會展現出固化傾向與延展傾向的不同配比,由此形成考察神圣空間建構的一條至關重要的線索。
(二)秩序的共謀——神圣空間的功能
進而,宗教學還考察了神圣空間如何在宗教實踐中強化所屬宗教背景、創造神靈世界以及規制人類世界,由此提煉出神圣空間的三項基本功能,它們在各個宗教系統中都得到了廣泛驗證并成為神圣空間目標設置的基礎。
第一,神圣空間為人類宗教信仰實現的交流之地,是人類與神靈相遇的重要載體。通過空間內的象征,使神靈與現實主體的人進行深度的交流與溝通,這種象征可以被歸納為兩種:首先是各種“垂直的物體”,它們從大地上達天際,諸如山、樹木、欄索、柱子、桿等。例如在拜占庭式教堂里,在圣堂(sanctuary)走向圣壇(chancel)之間會設有作為圣障(iconostasis)的屏風,祭司往來期間,就會被認為是穿梭于不同領域的天使,所以“圣障不是一個‘象征’或‘奉獻的對象’;它是一道門,是這個世界和另一個世界之間的門”(Galavaris, 1981, p. 7);其次是“神靈的意象”,一個神圣空間會包含有神靈的意象(images)或其他象征(tokens),借助這一形式化表述,神靈被認為居住于這一空間,從而將其營造為人與神的相遇之地。例如 耶路撒冷猶太圣殿的至圣所(Holy of Holies)中的約柜(Ark of the Covenant),神道教的圣壇以及日本的房子中的神龕,它們的存在都因授予了神靈的在場而成為神圣空間。
垂直物體或神靈意象制造了神圣之地神靈的存在,而這一區域會通過具象的現世載體(如柵欄或橋)被營造為相對密閉的空間,它在保證了該空間的神圣性的同時也保證了它的潔凈。由于人們本能地認為神圣之地趨于完美,因此也必然潔凈,所以在可見的潔凈與可感的神圣之間,就潛在地達成了在直觀與心靈之間的同構。
第二,神圣空間是神圣力量的展現之地,是神靈賦予人類力量以完善現世生活的一種方式。崇拜者渴望在神圣空間中借助神靈賜予的力量去改變人生及生活境遇,而宗教傳統與神圣力量的性質則決定了神圣空間改變現實生活的方式。宗教學認為該方式可以被分為“治療”與“拯救”兩種。比如在印度教的傳統中,朝圣的地方從bhukti(好處)和mukti(得救)這兩個維度提供了神圣的力量,而“好處”的涵義即為“治療”,得救的涵義即為“拯救”。朝圣與治療密切相關同樣體現在中世紀的基督教中,朝拜者通過虔誠的朝圣儀式試圖見證或獲取神奇的治療,許多神圣之地也滿足朝圣者確保身體康健的目的。獲得拯救則是理解神圣力量的第二個方面,由于神圣之地具有圣潔的屬性,由此可將“凈化”與“拯救”兩者進行關聯。例如在基督教傳統中,基督之血說服朝圣者擺脫罪惡的污點,在干凈的現實生活中得救*英國的社會改革家Hugh Latimer,哀痛Hailes的基督之血的標記,認為它可以說服朝圣者“他們處于干凈的生活里,處于得救的狀態中,而沒有罪的污點”(Sumption, 1972, p. 289)。;而在印度教傳統中潔凈神圣的恒河水也可以令死者獲得永生*在各種印度教傳統中,死于Banaras,在那里火葬,或將死者的骨灰撒在Banaras的恒河中,都能夠確保死者得救。。
第三,神圣之地作為世界結構的隱喻,通過發揮聯想連動機制將具象的空間排列映射為人類的生活秩序。隱喻被視為一種文化現象,在宗教傳統中構成了神圣空間的一種存在方式,這一方式首先可以表現為將空間秩序化,進而將這一秩序投射至整個現實世界。隱喻具有溝通、協調和整合的力量,把混亂整合成秩序、將分裂導向同一,以此將神圣空間予以秩序化的呈現。例如Lakota的簡樸小屋的物理空間就將Lakota世界的其他現實也納入它的形態,而它的中心因此也就成為終極的參考點,空間、一切存在、一切力量最終都在此相匯合。世界隱喻的第二種方式是方向,神圣空間會引導人們朝向圣地,以此形成神圣的意義。例如最早的科普特人和東方教會以及后來的西方教會的神圣空間全都朝向初升的太陽,因為那是基督復活的象征。
綜上所述,神圣空間的功能可以歸納為對三種對象的展現:神的在場、神的力量、現實世界。但是這里更值得關注的是,在這一展現過程中,神圣空間對人的觀感營造與人對神圣空間的信念反饋始終處于一種積極的雙向互動的關系,而非神圣觀感單向度地決定了神圣信念。例如, 當人們進入一個潔凈之地時,進入者會本能地產生一種敬畏之心,而這一敬畏之心又反過來又印證并強化了該空間中物體或意象的象征功能,這一雙向機制就在環境秩序與心靈秩序之間建立了一種“格式塔”式的“同型”。再如,現實世界作為一個秩序空間往往將神圣空間置于核心,而在這一核心內部,又以隱喻的方式“微縮”了這樣的秩序空間。所以神圣空間的隱喻功能,因為得到了整個外部世界的配合,由此就在向外指涉與向內指涉之間也達成了一種“秩序的共謀”。這樣一種秩序的共謀甚至可以達到這樣的地步,即賦予神圣空間以組織社會運行的功能。由于神圣兼備具象與抽象的雙重特性,因此它適于將抽象的人類關系系統具體化,并以此創建了一個可以確認的社會結構中心。正如Paul Wheatley指出,儀式復合體的中心既是“創建政治、社會、經濟和神圣空間的工具,它們同時也是宇宙、社會和道德秩序的工具。”*參見Lindsay Jones,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Thomson Gale Press 2005(eds), 2nd Ed. Vol.12. p. 7978-7986. 中譯本未出版。作為一種顯現在空間的神圣意象,它有時確立了客觀秩序中的政治秩序,有時甚至能承擔生產工具再分配的經濟控制功能。
因此,神圣空間的功能從來不是自足的,而是需要援引外部因素的積極互動、反饋、參與,才能充分發揮自身的效用。而唯有基于這一共謀機制——無論是在主體/客體間還是在神靈世界/世俗世界間——我們才能真正理解神圣空間功能的成立基礎。
(三)時空的凝縮——神圣空間的編碼
進入文化社會層面,我們會發現一個空間越是成為宗教實踐的中心,其涵蓋的象征系統就越龐雜。一個高度神圣化的空間則往往結構化地包含了人體、宇宙、宇宙創造的諸階段的劃分、傳統的神圣敘述以及人類生活的諸領域等諸多組成部分,從而在文化實踐的意義上達成了意義的編碼,豐富了宗教信仰的內涵。
第一,身體本身就有可能被編碼為一個神圣空間。一方面,身體自身通過某種修煉可能具備神圣的意義。如佛教的禪定或印度教的瑜伽,身體作為一個內部空間將被引導向一個神圣空間改變;另一方面,物質性載體也可能因為隱射身體而獲得神圣性。例如印度寺廟就展現了人類身體與空間神圣性之間的密切關聯,寺廟建筑被等同于人體構造,而寺廟最為核心的空間環境又被期待是與神靈相遇、交流的場所,而這一期待也象征性地復制了人們在自己的心中與神靈相遇的境況。通過身體和精神的統一性,被象征為身體的空間獲得了神圣性的功能及特性。正如Silparatna*參見Lindsay Jones,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Thomson Gale Press 2005(eds), 2nd Ed. Vol.12. p. 7978-7986. 中譯本未出版。說,“寺廟作為一個宇宙人而受到崇拜”(cf. Kramrisch 1946, vol. 2, p. 359)。神圣空間內的深層涵義傳遞的是宇宙的意象,而人類通過在其中注入身體的意象從而描繪出微觀宇宙與宏觀宇宙之間的一致與對應。
第二,神圣空間形態范式往往被編碼為宇宙的形態。按照伊利亞德神圣空間的范式,蘊藏在圣神空間內的橫向維度劃分是通過世界重要的縱向劃分而傳遞出來的。這些劃分大致可以歸納為上界、地上和陰間,當然也包括其他一些較為獨特的宇宙論概念。
第三,神圣空間被編碼為世界生成的步驟及秩序。例如在印度教的寺廟中位于寺廟內部最黑暗的中心神龕即象征了創世的起點,由此在空間中向外輻射,也在意義上象征了世界生成的過程。
第四,神圣空間被編碼為重要宗教儀式的操作流程。這里的關鍵在于,由于儀式本身就象征了事物交替、重疊、變更、輪回的有序連接,因此象征了儀式的神圣空間就同時標志著儀式的進行以及由此推演的生命周期、自然周期乃至宗教敘事周期的運行,由此將空間凝華為整體時間的象征。
第五,悠久古老的傳奇故事往往也會成為神圣空間編碼的組成部分。神圣空間是一個記載神圣敘述的地方,它不僅包含自然界所遺留下來的重要印記,同時也描繪出神圣敘述的意象,提醒人們那里曾經發生過的傳奇故事,喚醒人們沉睡的記憶以及激發人們對于現世的思考。神圣空間內的儀式化也會令人回憶起其歷史上關鍵的時間節點所進行的舉動,而將儀式得以確立并最終沿襲下來。而這一編碼過程的深遠意義在于,神圣空間承載的神圣敘事絕不只是一個時間點或一個事件,它必然會跳脫無法回溯的歷史背景,活躍于現代人的宗教文化之中,而實現這一跳躍的就是神圣空間。神圣空間在無形中拉近了崇拜者與歷史事件的距離,因此緩解了先知時代與當下時代之間的隔閡焦慮。
如果說第一、第二類編碼實現了神圣空間對其他空間的投射,那么第三、第四類編碼就實現了神圣空間對時間流程的凝縮,而基于神圣空間對時間與空間兩個維度的象征轉換,第五類編碼實現了神圣空間的“劇場化”——它是“重演”而非“再現”傳奇的故事。正如伯明翰學派文化研究所揭示的,文化是總體生活方式中各要素間關系的組織。在此意義上,神圣空間對時空的編碼、對英雄事跡的編碼,將自身從純粹的宗教場域拓展至與“神圣/世俗”辯證法勾連的更為廣闊的社會場域。總體而言,這一勾連同樣存在于神圣空間的建構與功能之中。宗教學斷言,稱一個地方為神圣的,那就是在斷言這個地方、它的結構、它的象征表達了基本的文化價值和規范。宗教學視域并不試圖將神圣空間描述為一個封閉的結構閉環,就這一閉環來說,世界各地的神圣空間甚至缺乏共通的因素——無論是內容的還是審美的,但正是基于將神圣空間置于更為開放的交互環節與更為廣闊的文化世界,神圣空間超越了神學單純的自我敘事,形成了一個與外界因素交融互動的特征系統(如下圖),而正是這些特征將神圣空間置于 “神圣/世俗”辯證法的核心位置。

神圣空間的建構、功能與編碼示意圖1
三、純粹性與不純粹性的張力:神圣空間的本土化思考
宗教學揭示了,真正實現“神圣/世俗”辯證法的,不是概念性的,而是空間性的。因為只有回歸于空間,“神圣/世俗”的關系才會展現出空間(神圣空間)與空間(世俗空間)的、人與空間、人與社會等三重具體關系,從而呈現出與特定世俗空間交互的特定“神圣空間”。結合中國傳統村落的文化環境,它的神圣空間也必然有其獨特的面向。在中國傳統社會,維系聚落的最主要的精神紐帶不是以神為核心的超驗信仰,而是以宗族為核心的祖先信仰,它構成了中國傳統宗教文化有別于西方宗教文化最為顯著的特征。基于這一特征,在村落社會宗族往往利用時間權威——對于祖先信仰延續性的把控,去獲取空間位勢——宗族祠堂的營造與賦權,并利用這一空間位勢進一步鞏固自身對于祖先信仰解釋、傳承的權威,由此使 “神圣性”成為宗族在時空性、知識性和策略性場域中進行建設的重要手段*勞格文、科大衛編《中國鄉村與墟鎮神圣空間的建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43頁。。而在此背景下,對于中國傳統村落社會的宗教信仰,無論是概念性還是空間性,都不具備在伊利亞德與涂爾干意義上的“神圣/世俗”的截然對立,由此延展而生的神圣空間,也將在 “非純粹性”這一層面有別于西方神圣空間的純粹性特征。
有別于前文宗教學視域下對神圣空間的功能研究,祠堂的功能屬性呈現出更為靈活多變的特征,從而在不同時間段內可以獲得不同的空間意義。在祭祀祖先的時候,祠堂承擔了祖先在場乃至祖先力量顯現的功能,這一點與西方神圣空間差別并不算大。但是除此之外,當宗族成員在祠堂聚集議事時、在祠堂續修族譜時、或者在祠堂開設學堂為族中兒童提供教育時,祖先就從神圣的中心隱退為神圣的背景,祠堂承擔的功能就突破了單純的祖先崇拜,而具有超出西方神圣空間承載程度的世俗意義。此時,與其說祠堂是一個神圣空間,莫如說是一個以神圣為名,延續現世文脈、開展社群聯絡、社群交流的公共空間,而關鍵在于這一功能屬性與祠堂的神圣性是恰當地融為一體的。雖然基于“神圣/世俗”的辯證法,我們能夠理解西方神圣空間與世俗空間的相對關系,但是二者依然會保持一個基本而固定的空間界限,例如教堂或寺廟,它們的神圣性大多基于與世俗空間界線的神圣性,這就從根本上維系了神圣空間的純粹性。但是在中國傳統村落,由于神圣空間的功能是動態的、是依場合而變動的,神圣空間與世俗空間的界線由此也就是模糊不清的。這一方面導致了一個神圣空間同時也可能是世俗的,如此處所述的祠堂,另一方面也可能導致一個世俗空間同時也可能是神圣的,如在家中主廳掛上祖宗像或在內室擺上祖宗牌位。
因此,作為不純粹的神圣空間,祠堂展現了傳統中國神圣空間與西方神圣空間的內在張力,由此也通過編碼環節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文化表征。梁思成曾指出:“建筑顯著特征之所以形成,有兩因素:有屬于實物結構技術上之取法及發展者,有緣于環境思想之趨向者。”*梁思成:《中國建筑史》,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8年,第17頁。對應這兩個因素,祠堂在材質與選址這兩個方面呈現出富有東方特色的編碼方式。首先,祠堂是中國古代木質結構建筑的集大成者*方利山等:《徽州宗族祠堂調查與研究》,安徽:安徽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09頁。,是傳統村落建筑營造技藝的典型代表。在具象層面,祠堂的基本結構往往采用木穿斗架、木梁架與天井、合院形制結構的組合,*王小斌:《徽州民居營造》,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13年,第4頁。使木材成為祠堂“結構美(力的傳遞邏輯)和構造美(構建穿插交合的邏輯性)”*蕭默:《建筑的意境》,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6頁。的載體。由此延伸至抽象層面,“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木材的生長特性向來與中國傳統文化的人生觀照互為映射,這也導致祠堂的木質特性在更為潛在的層面上與儒家文化對人格與德性的要求形成了一種隱喻與互通的關系。
其次,“天馬涌泉之勝,犀牛望月之奇,豐瀅水聚,土厚泉甘”*王小斌:《徽州民居營造》,第4頁。,山水向來就是古民居最為基本的也是最具決定性的環境因素,祠堂也是其所屬村落依山采形、傍水取勢的營建理念最為嚴格的執行對象以及最為充分的標準體現。由外觀之,當我們宏觀地將祠堂視為一個整體的“能指”,而將“神圣性”視為這個能指的“所指”時,那么二者穩定而應然的聯結就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祠堂這一能指與其他諸多能指之間的關系締結,并以此獲得自身“神圣性”的顯著意涵。因之,“山”與“水”就是這個編碼系統中彰顯祠堂神圣意涵的關鍵能指。王小斌先生在《徽州民居的營造》中記錄到:“幾乎所有的聚落都傍水而居,許多古聚落的名稱就是佐證,像皖南的屯溪、花溪、碧溪、棉溪、東源、大源、竹源、深渡、涇川、桃花潭”。*王小斌:《徽州民居營造》,第112頁。由內觀之,縱然是陰雨天散落在房屋瓦片上的雨水也通過高高翹起的墻角流入祠堂的天井中,“四水歸堂”的建構理念進而代表了人氣與財氣的累積。由此對接的文化觀念無疑是中國哲學“中和位育”、“天人合一”的思想,在此思想傳統統攝下,建筑可以與文學、繪畫等其他編碼方式勾連為一個更為宏觀的文化整體。
在從“神圣性/世俗性”向“神圣空間/世俗空間”轉化、結合的同時,“神圣/世俗”的關系從截然對立走向了對立統一。唯有基于這一認識,我們才能說“神圣/世俗”的辯證法提供了理解“神圣空間”的普遍范式。而傳統中國的神圣空間的不純粹性特征也并非是顛覆了上述范式,而是豐富了后者的內涵與可能。村落作為傳統中國社會組織最為基本單元,既是中國人世代棲居的重要載體,更是中國人深層文化訴求的心理歸宿,它的多元空間與人的生存結構、情感體驗有著密切的聯動關系。在這一高度“地方化”的社會場域中,神圣空間的建構、功能與編碼將依托聚落選址所在的自然空間、形成于人與人靈活而高頻互動的社會空間,最終升華為信仰豐盈、符號凝聚的文化空間。而通過對鄉土中國獨有的精神“廟宇”進行全方位解讀,將為我們理解如下宏觀問題提供啟示,即,中國文化能夠如何在一種“在地性”、“此岸性”的世俗空間中,完成一種“超驗性”、“精神性”的文化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