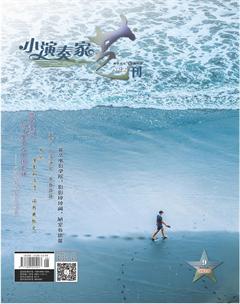旅居澳洲,骨子里不改中國血脈
張悅
于京君 1957年生于北京,1977年畢業于中央音樂學院后留校任教,八十年代初赴日本東京音樂大學跟隨湯淺讓二和池邊晉一郎學習作曲,1985年移居澳大利亞,1988年被美國坦戈伍德音樂中心選為作曲研究員,師從亨策、納森和伯恩斯坦,曾應邀為澳大利亞 ABC 廣播公司、英國BBC廣播公司、法國現代室內樂團等團體創作作品,并多次被國際現代音樂協會主辦的世界音樂節和其他現代音樂節選中,在美國、英國、日本、瑞士、德國、新西蘭等國演出,作品獲獎眾多,其中包括庫賽維茨基坦戈伍德作曲獎、維也納現代大師作曲獎、第五十六屆日本音樂比賽作曲獎、意大利迪利亞斯特城作曲獎、日本全音鋼琴2000作曲獎、澳洲著作權協會作曲獎等,1991年和1994年連續兩屆榮獲保羅·羅因作曲獎,成為澳洲作曲界獲此殊榮的第一人。
不久前,著名作曲家郭文景聽過浙江交響樂團在國家大劇院“交響樂之春”上演的于京君專場作品音樂會后,不禁在微信朋友圈慨嘆:“前些年見到京君患帕金森說不出話、行走困難時深感震驚,甚至覺得他性命堪虞,不想這些年過去了,他不但越活越健康,還不斷寫出精彩的作品,上天終究不棄那些一生在自己尺寸天地中精耕細作的人。”
與郭文景發出同樣感慨的還有資深古典音樂愛好者張克新,他認識于京君已有十年,當年曾請他為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作曲,“因為他住在墨爾本,在國內完全默默無聞,但在專業圈早已聲名遠揚,已經接受過包括國家大劇院、浙江交響樂團、中國愛樂樂團的委約,唯一沒變的就是他的真誠和樸實。”
與國內音樂圈很多大腕級作曲家比起來,于京君確實是個陌生的名字,而在國家大劇院舉行的這場專場音樂會卻將他的創作才華和作品光華徹底展現出來。浙江交響樂團藝術總監張藝向記者介紹道:“于京君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但是在國外生活了三十多年。他其實是中央音樂學院培養的,然后到日本、美國學習,后來在澳大利亞學習生活,在國外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包括在澳大利亞基本把作曲獎項拿了個遍。因為澳大利亞在西方音樂界不是很主流,所以知道他成就的人并不多,但他在日本也很有名。樂迷最熟悉的是他的《小星星主題鋼琴變奏曲》,很多人都是通過它知道于京君的。”
《小星星主題鋼琴變奏曲》采用家喻戶曉的童謠《閃亮的小星星》為主題,通過一些變奏探索、闡釋、找尋和演示發展音樂的可能性,鼓勵年輕作曲者和鋼琴演奏者的創造性。于京君的微博曾經一度很活躍,就是因為這個“小星星”結交了很多國內的樂迷朋友。
耳目一新重塑民族樂曲
雖然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但在國內開作品專場音樂會這還是第一次,于京君毫不掩飾能將自己的作品專場上演的興奮,“我過去的一些個人專場音樂會在墨爾本也有過,但像國家大劇院這么隆重的方式呈現還沒有過。”于京君雖然離開祖國幾十年,但一口京腔京韻一點沒變,笑起來就像一位和藹親切的北京大爺。
這場音樂會上演的三部作品都很有代表性,分別創作于不同時期。上半場演奏的《五彩云》創作于1991年,原是一部無標題的純音樂作品,于京君根據一段即興的鋼琴曲擴展成交響詩,1992年一舉奪得首屆澳大利亞保羅·羅因管弦樂作曲獎,1993年由墨爾本交響樂團首演。張藝說:“這是于京君創作的中青年時期作品,他的寫作技法是非常簡約派的風格,但是非常細膩,用西方當代技法寫的技術含量非常高,但是一聽又是很中國化的東西。很多人聽完都覺得很棒,哪怕是從國外欣賞者或作曲家的角度來說,也是一個很精致的作品。”上半場演奏的另一部作品《新柳水令》,原型是1996年于京君為墨爾本維多利亞藝術學院學生樂團所寫的一首樂曲,原曲是為單簧管和弦樂隊而作,作品演出之后受到了聽眾的熱烈歡迎,由于作品的音樂語言淳樸,又具有濃厚的中國鄉土風,還成為了澳大利亞國家古典廣播電臺經常播放的廣播曲目。
2016年,竹笛演奏家陳悅聽到這首作品后,邀請于京君將它改成竹笛協奏曲,用交響樂隊代替以前的弦樂隊,竹笛獨奏部分也增加了難度,使之成為名副其實的協奏曲。談到創作過程,于京君說:“這首作品最早是我寫給澳大利亞一位單簧管演奏家朋友的,用中國旋律寫了這么一種單簧管曲子,他吹得很高興。澳大利亞古典廣播電臺每到中國新年就播放這首曲子,十年內播了有二十多次。后來,陳悅通過張藝找到我,希望我寫個竹笛的曲子,我就想改編了這首單簧管作品,首先它很民族化,又具有管樂的共同特點。我把這首曲子改完拿給陳悅看,她覺得非常合適。等于說這首曲子是從洋的變成中的,它回家了。”《新柳水令》有三個樂章,于京君說第一樂章是嗩吶曲《一枝花》,由柳子戲的素材而來,第二樂章是《高山流水》的素材,第三樂章是《陶金令》的素材,所以三個樂章就各取這些民間樂曲中的“柳”、“水”、“令”三字,又冠之以“新”。張藝認為這首《新柳水令》用竹笛演奏后特別契合,感覺就像完全是為竹笛所作,“很難想象于京君原來所作的曲子是怎么用單簧管演奏的,可以說移植得非常棒!這個竹笛版本的《新柳水令》寫出來后,北京交響樂團將這個曲子帶到了塞爾維亞去演出,非常受歡迎,可見于京君對作品的移植和改編是非常成功的。”
內行人看門道
音樂會下半場演奏的是于京君近期創作的交響樂《社戲》。它的創作靈感源自魯迅先生的同名小說,是一部以交響音樂為載體講述的典型中國故事,作品以浙江戲曲音樂為主脈,描繪出有機的社會生活圖景和中國文化意象,通過最具浙江特點的紹劇、越劇、婺劇這三大劇種中的元素進行演繹,整部樂曲充滿豐富的變化性,既大氣恢宏,又不失柔美婉約,在精湛的交響樂寫法中洋溢著濃郁的地域風情。尤其是臨近尾聲的四分鐘,在音樂會現場收獲了最多的喝彩與好評,這也是最令于京君得意的部分,他說:“最后就是各種戲曲因素,像唱對臺戲一樣結合在一起,各種節奏全來了,紹劇的《三打白骨精》那種過門來了,越劇的‘天上掉下個林妹妹來了,婺劇的部分也進來了。”為了寫這首曲子,浙江交響樂團老團長陳西泠和創作部主任王天明曾全程陪同于京君去紹興、金華等地,看戲曲老藝人如何表演和演奏,這讓于京君十分難忘。
“《社戲》是我近年來聽到的最偉大的中國作品之一。”張克新如此評價,他表示說它偉大并不是因為架勢上的高大,而是因為于京君總是從最常見的主題出發,他的旋律總是很有歌唱性,他敢于用最中國的和聲,一聽就是中國味兒,并不是佯裝國際化的中國作品,所以很容易被普通人接受,而作曲技法上又極具智慧。“在《社戲》里,他把巴赫的復調變奏手法和地方戲貼在一起。普通人并不會察覺,但于老師為自己干了一件多么較勁的事情,一點都不取巧,他的其他作品又何嘗不是這樣呢?”懂行的人一眼就能看出《社戲》的功力所在:四十分鐘的大部頭純器樂作品全部由交響樂隊樂器演奏,一件民族樂器都沒有用,展現的卻是中國戲曲的內涵和旋律,這在如今已是相當少見。
不用中國樂器照樣傳達中國聲音
沒用一件中國樂器,卻令最正宗的中國聲音響徹全場,于京君是如何做到的呢?長期在國外生活,受交響樂隊編制的限制使得于京君只能為西方管弦樂寫作,“沒有戲曲里常用的小鑼,我就用木管樂器去模仿那種聲音,因為這首曲子要是在墨爾本演奏的話,即使找到鑼也不是那個調,那干脆不要,我就用豎琴撥弦,用雙簧管、單簧管和長笛模仿發音,出來的聲音有點像也不完全像,很有意思。”正如于京君所說,管弦樂曲、管弦樂隊這種媒介非常國際化,如果想寫中國故事、傳達中國聲音,不用中國樂器可能更有說服力。
于京君打了一個比喻:“比如在奧林匹克比賽上,競賽規則都是公平的,但如果讓中國的武術和自由操同場競技,那不是一個比賽規則,也沒法比。”在《社戲》“紹戲敘事曲”三打白骨精那段里有一段老太太的哭腔,這個調如果用民樂演奏的話是斷點不分明的調,西方樂器中都是一個點一個音,而中國民族樂器往往會有這樣一種積習下來的演奏特點。在模仿嗩吶吹奏的段落里,于京君使用了兩個小號演奏,卻極具中國特色。
剛考入中央音樂學院時,于京君對民族樂器課并不是特別重視,在學校期間的一些作品就是當時按照樣板戲學著寫一些唱段,然后拿給老師看。那時他只有十六歲,但是對戲曲的鉆研使得于京君覺得非常受用,“以至于我們后來寫現代風格音樂的時候,還是會受到那時學習的影響,在一些細節上也會想方設法保留我腦子里聽到的最熟悉的東西,所以有時貌似寫了一個所謂的現代作品,實際上那些最基本形態還是中國的。”
即使是寫《社戲》,于京君所運用的還是他的個人感受。“運用戲曲音樂素材創作管弦樂作品,首先得讓管弦樂唱起來,如果把主題切割成很多小段落,再經過變形與發展,表面上看倒是很交響化。但事實上中國戲曲唱段的樂句比較長、大,且參差不齊,卻又非常具有音樂性,如果破壞了這些唱段樂句的完整性,也就破壞了戲曲本身應有的音樂性,這也是聽眾覺得這種類型的管弦樂不好聽的原因。”于京君的話很有現實意義。
與譚盾等一些生活在國外的著名作曲家不同,于京君很低調,與國內的交流不多,但他在網上也能聽到一些國內作曲家的新作品,這其中他對陳其鋼的作品表示欽佩,“他學音樂的路子很正,我覺得現在有些作曲家‘開玩笑的程度大于創作音樂了。”希望這樣的人能為更多人所知,帶我們遠離空洞、重復與快餐式的音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