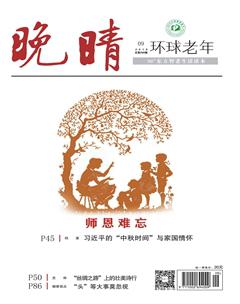盛中國:一曲《梁祝》成絕響
向思琦
2017年1月,76歲的盛中國與妻子瀨田裕子在哈爾濱成功舉辦了小提琴鋼琴音樂會。他們既是夫妻,也是合作30年的音樂拍檔。演出的最后一曲,是盛中國拉奏過上萬次的《梁山伯與祝英臺》。誰也沒想到,未至一載,“盛中國小提琴獨奏音樂會”10月的巡演因他突發疾病被取消。今年9月7日,本還念著復出音樂會的盛中國突發心臟病去世,一曲《梁祝》成為絕響。
上世紀60年代中期,從莫斯科留學歸來的盛中國改編了小提琴協奏曲《梁祝》,這也成為他演奏次數最多、最受歡迎的作品。盛中國錄制的《梁祝》、莫扎特等音樂唱片和CD影口向了幾代人。
琴如知己
“1984年,中國的音樂界出了一件盛事。一個家庭的三代人十二把小提琴,同時出現在一座舞臺上正式演出。這個家庭就是盛氏小提琴之家。”盛中國的母親朱冰在回憶錄《我的故事≯里記述。
朱冰與盛中國的父親盛雪相戀于上世紀30年代戰火中的重慶。小提琴家盛雪也是一位“樂癡”——即使在炮彈轟炸下躲進防空洞里,也堅持拉琴。
作為“盛氏小提琴之家”的長子,盛中國自小便流露出音樂天賦,也成為父親重點的培養對象。
盛中國剛走出襁褓,就能手拿兩支筷子模仿父親做拉琴狀,嘴中競可哼出父親練習的曲調,連父親拉琴的神態也模仿得惟妙惟肖。戰亂年代,境況艱難。朱冰又不愿讓兒子一直以筷子作琴,便用燒火的柴火、納鞋底的麻繩為他做了一把沾著血跡的“小提琴”——出身殷實家庭的母親此前從未做過這樣的粗活,經常把手割破。雖是“啞琴”,卻是幼年盛中國最愛的玩具。
到四歲那年,盛中國終于有了一把真正的小提琴。次年,他就開始了以父為師的學琴生涯。一年中除了除夕夜和春節,練琴一天不能落。
日夜與琴為伴,他從小感覺到“手里的琴是有生命的,它最理解我,也最懂我”。
但視提琴如知己、親人的他,卻賣過三把提琴。“第一把賣了50萬元,給貧困山區捐了25個塑膠操場。第二把賣了100多萬元,捐給了老家的基金會。第三把賣了180萬元,捐給了中國扶貧基金會。”
播撒種子
80年代起,盛中國開始在世界各國大量巡回演出——在澳大利亞的六個城市演奏《梁祝》等協奏曲,與鋼琴家劉詩昆遠赴南美舉辦音樂會……“最迷人的小提琴家”、“中國的梅紐因”,贊譽再次接踵而至。
有一次,盛中國在廣州舉辦演奏會時,主辦方專門派了一位廚師為他準備夜宵。老廚師做飯時對盛中國說:“我聽說你的琴拉得特別好,可惜你演出時我沒機會去聽。”盛中國一聽,馬上說:“那你等一下。”便轉身回到房間將自己的小提琴拿來,為廚師拉起了小提琴。老廚師覺得一位大師級人物專門為自己一個人拉琴,有些不安。盛中國對他說:“你們炒菜炒得好的叫大師,我們拉琴拉得好的也叫大師。你讓我的味覺得到滿足,我讓你的聽覺得到享受。你喜歡聽我就很高興了。”
他也用農民播種來比喻自己音樂的意義:“我開這么多音樂會,定位很明確——不是娛樂的,完全是文化的。我要用我的琴聲,從我的手指中流出的每一個音符,像一粒種子一樣播撒到我聽眾的心田中去。一種什么種子呢?崇尚美的種子,崇尚和諧的種子,崇尚善的種子。”
音樂作紅娘
1987年,盛中國在日本舉行演奏會時,第一次與日本鋼琴家瀨田裕子合作。當時二人語言還不相通,盛中國卻從瀨田裕子的琴聲中聽出與自己相似的音樂見解。一曲《A大調小提琴奏鳴曲》伊始,兩人成為越來越默契的搭檔。
“這首曲子就是專業的鋼琴家,只練習一個星期也是遠遠不夠的。可是裕子能在一周里把這首曲子彈得非常到位,能看出她和我對音樂的理解很相似,所以我當即就決定與她合作了。”盛中國說,“1987年3月28日,我和裕子第一次合作,就非常成功。”
“我們有各自的生活,也有互通的地方。”盛中國說,“兩個人就像是兩條線,能結合在一起,肯定能找到兩條線的那個交叉點,我們的交叉點就是對古典音樂的共同感受。”
在盛中國看來,雖然兩個人來自不同國家,相處在一起卻感受不到對方是外國人。“共同的事業、共同的愛好使我們息息相通。”瀨田裕子說。
30年來,在難以計數的舞臺上,盛中國與瀨田裕子一人著西服,一人著長裙,一人站在前面拉動琴弦,一人坐在后面彈弄琴鍵,純凈的鋼琴聲伴奏悠揚的提琴聲。《梁祝》、《愛的問候》、《流浪者之歌》……這些夫妻二人共同完成的經典作品,留在幾代人的記憶里。(來源:《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