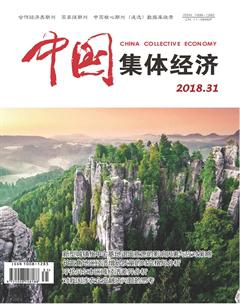水上交通肇事行為是否屬于交通肇事罪保護法益范圍
龍恩宇
摘要:文章以水路運輸中的交通肇事行為是否屬于交通肇事罪所保護的法益范圍為出發點,在明確陸路運輸屬于傳統意義上交通肇事罪法益保護范圍的基礎上,探討水上交通肇事行為是否有參照鐵路、航空兩種交通條件下的單獨罪名另立一新罪名的必要。通過比較水路交通條件與道路交通運輸條件下交通肇事行為在犯罪構成上的異同,結合學界其他學者的不同觀點,思考水上交通肇事行為是否屬于交通肇事罪保護法益范圍。
關鍵詞:水上交通肇事;法益保護;交通肇事罪
一、交通肇事罪保護法益范圍
我國現行刑法關于交通犯罪雖然單獨罪名相對較多,但是其覆蓋的范圍并不周全。毫無疑問,道路交通犯罪的罪名層級設置和覆蓋是最為合理和完善的,形成了一定的梯度。但是反觀空中、鐵路、水上交通方面的罪名卻相對欠缺,實踐中還有許多肇事行為尚未準確歸罪。從空間領域上看,我國交通犯罪的罪名分布于三大方面,即道路交通犯罪、鐵路交通犯罪、空中交通犯罪以及水路交通犯罪。其中,陸地交通安全又分為道路交通安全和鐵路交通安全,而水上交通安全則一般包括海上交通安全與內河交通安全兩類,空中交通安全在交通肇事領域內則主要指平流層民用航空器航行安全。劫持航空器罪、暴力危及飛行安全罪、劫持船只罪都不包含違反交通運輸法律法規而導致的危險交通安全事故的犯罪行為,其管束的是一般主體在交通工具上對交通運輸人員或其他人員通過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劫持運輸工具或影響交通運輸操作人員的行為,不在本文的討論范圍之中。交通肇事罪規定在195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草案(初稿)》(以下簡稱57年草案)的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章節中。196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草案》(以下簡稱63年草案)第33稿在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章節再次重申該罪,并做了局部修改。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在第133條規定了該罪,將該罪的調整對象從特殊主體擴大為一般主體,量刑最高刑期從5年增至7年。交通肇事罪以1957年刑法草案為初始,經歷了1963年刑法草案、1979年刑法、1997年刑法的修改,最終在1997年第133條修成正果。根據當前刑法條文及司法解釋可知,各類交通肇事行為均已納入我國《刑法》133條交通肇事罪。通過比較法條關系變化,發現交通肇事罪相關法律條文的歷次修改均是就交通肇事罪的犯罪構成要件進行修改,而未改變交通肇事罪所保護的法益,即所有交通條件下的交通安全,是個人法益和社會法益的統一。
對于交通肇事罪中所稱違反的交通運輸法規中所包含交通運輸的范圍,理論界有著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這里的交通運輸是指我國領域內的所有交通運輸,包括公路交通運輸、水上交通運輸、鐵路交通運輸及空中交通運輸。持此種觀點的學者認為,盡管刑法另設了重大飛行事故罪和鐵路運營安全事故罪,然而在對罪狀進行表述時,這兩個罪的主體均為特殊主體。倘若不具備該特殊主體身份的人員違反交通運輸規章制度,發生重大事故的,會出現無法可依的情形,存在罪名適用上的空白。因此認為,《刑法》第131條的重大飛行事故罪和第132條的鐵路運營安全事故罪同第133條的交通肇事罪的關系應當是特別法條與一般法條的關系。
二、水路運輸中肇事行為的入罪及法益保護認定
(一)當前水路運輸交通的法律法規適用
水上交通肇事行為是指行為人因違反水上交通安全管理法規的規定,導致各類水上交通事故的行為。毫無疑問,嚴重侵害法益的水上交通肇事行為當屬刑法的懲治范圍,以期更好的保護水上交通運輸中的各類法益。目前我國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海上交通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內河交通安全管理條例》等法律法規規范水上交通肇事行為,保障水上交通安全。
水上交通肇事行為是行為人違反水上交通法律法規導致水上交通事故的行為。現實生活中,水上交通事故的發生并非單一原因導致,通常為多類型的原因共同引發。本文認為最終可入罪的水上交通事故的發生原因僅限于由人為因素引發的交通事故。只有當相關主體具備“非難可能性”時,才是刑法討論的可以追究法律責任的范疇。
目前我國關于水上交通運輸管理的法規從管轄地域來看,主要包含1986年頒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海上交通安全法》以及2002年頒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內河交通安全管理條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海上交通事故處理條例》第四條可知海上交通事故涵蓋范圍,2002年頒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內河交通安全管理條例》同上文提及條例的涵蓋范圍基本一致,其說明被刑法規范的行為對象相對穩定,唯一的差別在于海上交通事故中規定了“在航行中發生影響適航性能的機件或者重要屬具的損壞或滅失”這一類型,這是因為立法者認為在海上交通運輸中,這一情形對船舶的安全危害大到有必要單獨予以說明。
(二)水上交通肇事行為與道路交通肇事行為構成要件比較
主體方面,水上交通肇事的主體范圍的界定難于道路交通肇事的主體范圍界定。在一般的道路交通中,駕駛人通常是交通肇事罪的主體,即便司法解釋對其進行擴大后,其犯罪主體范圍進行了擴大,與駕駛人同車的人、單位都被納入犯罪主體的范圍,但一般來說,還是駕駛人為主要犯罪主體,在司法實踐中易于界定。而另一方面,由于船舶駕駛的特殊性,除單人駕駛的小船外,大部分船只,都由一定數量的船員團隊合作,共同駕駛。在發生交通肇事事故時,首要面臨的問題便是主體的確定。毫無疑問,船長是這艘船上的最高指揮官,但是否能直接將船長確定為該行為的犯罪主體呢?顯然是不能的,這種一刀切的判斷方法過于武斷,有悖于刑法“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不利于實現刑法懲治犯罪的目的。而如何確定水上交通肇事罪的行為主體呢?學界普遍的觀點是責任倒追至個人。這是因為船舶駕駛具有如下特點:1.船員的操作職能不同,船舶一般分兩部分,即駕駛部和輪機部,其職責劃分不同。且兩個部分要通過不同的專業考試取得其專業駕駛證,不能相互代替操作;2.船員的職務層級不同,駕駛部有船長、大副、二副,而輪機部有輪機長、大管輪、二管輪等。單有駕駛部船員或輪機部船員,船舶都是無法航行的,就是在這樣的團隊協作中,該如何確定發生交通肇事行為時的責任承擔主體,成為了學界爭議的焦點。有學者指出根據船舶駕駛的職務要求,高級船員指揮低級船員駕駛船舶發生交通事故的結果應由下達命令的高級船員承擔,若是低級船員不執行高級船員正確的指令最終導致交通肇事的,應由違背指揮命令的低級船員承擔責任。
在主觀方面,通過歷次法條修改,交通肇事罪的主觀方面由業務過失修改為過失。所謂業務過失是指,具備一定專業知識或者技能的人員,在從事職業過程中違反相關的法律、法規或者職業規章,造成人身損害或者財產損失的結果。而變更為過失后,其主體不再要求將交通駕駛作為從事職業,擴大了主體范圍。但是有學者認為,在水上交通中,其由于操作資格經歷了相比道路交通駕駛更嚴苛的專業資格考試,有的職位甚至對申請人的學歷有所要求,其資格證的取得遠遠難于道路駕駛執照的取得。甚至有的職位要求從業者具有大專及以上文憑,顯然其限制了水上交通運輸人員的準入資格,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水上交通運輸還可以認定為業務過失。但是毫無疑問,業務過失是從屬于過失的,故而水上交通肇事行為的主要構成要件是在交通肇事罪犯罪構成要件的主觀要件之內的。
在客體方面,水上交通運輸中所指的交通法規當然是包含在交通肇事罪所指向的交通運輸法規之中。
在客觀方面,除一般交通肇事行為外,水上交通肇事因為水路寬闊復雜,支流極多,同時水路上肇事證據固定存在困難,給駕駛員創造了“極佳”的逃跑條件,在懲治犯罪難度巨大而逃跑成本極低的情況下,在發生肇事行為后,交通駕駛人員通常會選擇逃逸。磨滅犯罪痕跡非常簡單,可以輕易避免受到刑事、行政、民事各方面處罰。如何處罰水上交通運輸肇事后的逃逸行為亦成為一個重要的爭論點。
關于交通肇事后逃逸行為,除我國刑法第133條提及的相關規定外,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公布《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也細化了交通肇事逃逸情形的具體法律適用。在《解釋》的第3、4條,對“交通運輸肇事后逃逸”作出了具體的解釋和規定。根據《解釋》第3條可知,刑法意義上的交通肇事后逃逸是指在具有法律規定的危害后果、責任程度或違章行為等前提下,發生交通事故后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為。從此角度可知,交通肇事后逃逸根據《解釋》第2條第2款的規定,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傷,負事故全部或主要責任,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離事故現場的,構成交通肇事罪。而由于水上交通運輸其特殊的交通條件,受水流速度、河流條件等客觀條件的限制,并在其共同作用下,沉船后受害人員的搜尋非常困難,常常出現“生不見人,死不見尸”的情況。而這種不確定傷亡的情況是在定罪量刑的時候不容許存在的問題。在現行刑法133條的規定中,只有致人重傷或死亡兩種情況,而沒有水路運輸中所特有和常有的“下落不明”情況。學界普遍承認,民事上的“宣告失蹤”、“宣告死亡”的法律擬制不適用于刑事中定罪量刑的標準,在刑法中,水上交通肇事行為是否將下落不明作為交通肇事罪的客觀要件加以認定仍值得討論。
一種觀點指出,“下落不明”不是交通肇事罪的客觀要件。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刑法133條和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釋》都沒有對這種“下落不明”的狀態加以規定,依據罪刑法定原則中“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的解釋,該肇事行為不應作為交通肇事罪的客觀要件。另一種觀點認為則持肯定態度,“下落不明”是交通肇事罪的客觀要件。持這種觀點的學者以最高人民法院在1992年給四川省高級法院做的一個電話答復為根據,認為在該電話答復中最高人民法院既然認為其可以定罪量刑,就足以說明下落不明的情形就可以被認定為交通肇事罪的客觀構成要件。本文認為,在水路交通運輸中,“下落不明”的情形可認定為交通肇事罪的構成要件。一是就犯罪的危害性而言,在水路運輸中基于其復雜的自然環境,“下落不明”這種危害后果與刑法中明文規定的“重傷、死亡”具有相當的危害性,其危害結果都很嚴重。若通過被害人家屬、海事管理機構、肇事船舶等多方的積極搜尋打撈,均未發現被害人,根據正常人類的生存極限和客觀情況來判斷,此時被害人的生存幾率幾乎可以認定為零。另一方面,若將“下落不明”排除在客觀要件之外,也不符合我國刑法的立法任務和目的,我國刑法的任務是實現保障人權和懲治犯罪的統一,“下落不明”本質上來說已經侵害了被害人的生命權、健康權,故水上交通肇事致人“下落不明”的情形自然而然應當屬于交通肇事罪的客觀要件。
(三)水上交通肇事行為屬于交通肇事罪的法益保護范圍
通過本文對水上交通肇事行為與交通肇事罪構成要件的比較,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水上交通肇事行為雖然在客觀方面與交通肇事罪的構成要件存在一定的差異,但是其可以通過體系解釋、立法解釋得到補正。其并沒有超過交通肇事罪的保護法益范圍。沒有必要如王茹軍、丁芝華、何濤等學者建議的在條件成熟時修改刑法,將水上交通肇事犯罪行為作為獨立的罪名加以規定。
在交通肇事逃逸的情形下,雖然水上交通肇事行為中存在特有的被害人“下落不明”情況,但本文認為該種情況也應歸于交通肇事罪的保護范圍,其對被害人生命權、健康權的侵害與刑法133條規定的“重傷、死亡”的后果具有相當的社會危害性,可以通過體系解釋將其納入交通肇事罪的犯罪構成要件范圍內。明確水上交通肇事行為屬于交通肇事罪的保護法益范圍。
參考文獻:
[1]王茹軍.水上交通肇事犯罪若干問題淺探[J].水上消防,2006(01).
[2]丁芝華.試論水上交通事故刑事責任追究的嚴格和強化[J].中國海事,2008(08).
[3]何濤.水陸交通肇事犯罪初探[J].人民檢察,2006(03).
[4]侯國云.交通肇事罪司法解釋缺陷分析[J].法學,2002(07).
[5]何濤.水路交通肇事犯罪初探[J].人民檢察,2006(03).
[6]高銘暄,馬克昌.《刑法學》[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7]向本陽.交通肇事罪基本犯若干問題檢討[J].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6(01).
(作者單位:貴州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