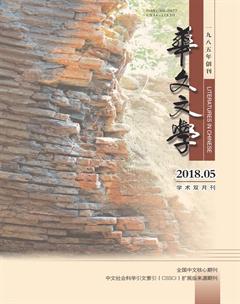后現代自傳體小說
郭海霞
摘 要:湯亭亭的《女勇士》自1976年出版以來引起了美國學界的一場持續、激烈的體裁辯論:關于這部作品是自傳、小說、自傳體小說,還是后現代自傳,評論家眾說紛紜。本文借助敘事交流模式,聚焦文本真實作者、隱含作者、敘事者、主人公和真實讀者的動態關系,深度探析《女勇士》體裁紛爭這一現象產生的根本原因,并以自傳、自傳體小說和后現代自傳體小說的敘事特征為依據,管窺文本對傳統自傳體小說敘事的“循規”和“逾規”,據此提出《女勇士》是一部后現代自傳體小說,旨在拓寬后現代文學體裁的研究視野。
關鍵詞:《女勇士》;敘事交流;自傳;后現代自傳體小說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677(2018)5-0112-06
引言
當代華裔美國文學的旗手湯亭亭(Maxine H. Kingston,1940-)的代表作《女勇士:在鬼佬群中度過的少女時代回憶錄》(以下簡稱《女勇士》)獲1976年全美圖書獎,被耶魯等美國高校引入文學課堂,被錄入人類學、女性研究等多個學科文選,作者本人也問鼎1997年美國“國家人文科學獎”。隨著這部作品關注度的日漸提升,其體裁的獨特性也吸引了眾多評論家的注意,并引發了一場持續的、激烈的體裁辯論。
作品的取材和敘事形式成為這場體裁紛爭的主要導火索,爭論主要涉及兩大陣營:自傳陣營和小說陣營,前者以美國非華裔評論家為首,后者以華裔美國評論家為主。前一陣營的主要依據是,此作品主要采用第一人稱敘述,整個文本圍繞“我”的成長展開,況且湯亭亭自己也坦言《女勇士》的素材多取自其親身經歷和家庭歷史①;另外,副標題的關鍵詞“回憶錄”暗示強烈的自傳色彩②。但是這一陣營的大多學者也承認《女勇士》并非傳統意義上的自傳:亨特利(E.D. Huntley)指出與傳統自傳中的自我塑造不同,湯亭亭“通過展現自己的思緒、猜想以及對過往事件的重構”③來塑造自我;瑪麗蓮·亞隆(Marilyn Yalom)直接提出可以把《女勇士》解讀為一部后現代自傳④;另有學者從女性批評角度出發,把《女勇士》歸為女性主義自傳⑤。盡管各持己見,但這些評論者共享《女勇士》是一部自傳的立場。而以趙健秀為首的華裔美國評論家對此表達了強烈不滿,并提出了很明確的否定原因。第一,文本中很多漢語詞匯、文學典故、歷史記述與事實不符,從根本上講不能稱其為自傳;而且把湯亭亭自己主觀的敘述當作自傳來讀很容易誤導非華裔讀者對華人和中國文化的認知;第二,這部作品最多反映的是湯亭亭的內在心理成長,因此《女勇士》至多稱得上是“名義自傳”⑥;第三,《女勇士》中存在大量的虛構成分。另外,趙健秀從華裔美國文學的獨立性出發,指出自傳起源于基督教中的懺悔⑦,本身不是中國文學的傳統形式,并據此指出對《女勇士》自傳體的默認是對美國白人文化的皈依。更重要的是,從文學欣賞角度講,自傳被認為是最沒有藝術創造價值的體裁⑧,因此更能滿足美國白人大眾對少數族裔文學作品的心理期待。中國學術界對《女勇士》體裁界定的研究多為對兩大陣營的爭論進行梳理,或者仍從作品的取材、第一人稱、體裁界定影響等角度出發展開討論,且尚未得出明確結論。這為本文的探討留下很大空間。
本文第一部分嘗試借助敘事交流模式,對這一持久爭論進行重新審視,指出真實作者和隱含作者立場的不符以及真實讀者的多樣性導致敘事交流遇到障礙,并對查特曼敘事交流模式進行補充。第二部分從自傳、自傳體小說和后現代自傳體小說的關系出發,分析《女勇士》的文本敘事特征,進而指出它是一部帶有鮮明后現代敘事特征的自傳體小說。文章嘗試為《女勇士》的體裁爭論本身提供一個新的切入點,剖析其實質原因之所在,并說明傳統的體裁劃分難以解決這一問題,提出新的體裁界定,旨在拓寬后現代文學體裁的研究視野。
作者-敘事者-主人公
敘事是修辭行為,敘事交流本質上講是一個“說服”過程,而閱讀文本的過程即作者說服讀者的過程。對文本體裁的界定無疑是此說服過程的基礎。美國敘事學家查特曼提出如下敘事交流圖:
圖中方框表示敘事文本,真實作者和真實讀者在方框之外表明二者在文本內部結構之外,其與敘事文本之間的虛線則表明二者與敘事文本之間不存在直接聯系,因而不屬于此敘事交流分析范圍⑨。不難看出,此交流模式更注重在敘事進程中隱含作者與隱含讀者與敘事文本的內在聯系。然而,本文發現從真實作者到真實讀者之間交流的分歧對《女勇士》體裁之紛爭扮演著重要角色,而這又深刻影響對文本敘事性質的判斷以及文本終極意義的生成。
傳統意義上的自傳被定義為:一個人書寫的關于他/她自己生平的故事⑩。這個簡單的定義貌似只涉及到了作者(“一個人”)和主人公(“他/她自己”)。法國自傳研究者菲利普·勒瓊(Philippe Lejeune)在《自傳契約》(“The Autobiographical Pact”)中就作者、敘事者和主人公三者關系列出2個公式:“作者=敘事者”,“作者=主人公”,從而進一步推出“敘事者=主人公”{11}。換言之,在自傳敘事中,作者、敘事者和主人公保持同一性。以此審視《女勇士》,讀者很難通過文本來確定作者是不是敘事者,而敘事者又是不是女主人公。第一人稱敘述貌似可以為這個問題提供一個肯定的答復,然而也不足以成為敘事判斷的“鐵證”,況且第4章《西宮門外》又特意采用了第三人稱全知敘述,有力暗示敘事者和主人公的非同一性。再加上5個小故事分別圍繞不同的主人公展開,雖然大部分是“我”敘述的,但敘事者“我”也沒有必要是同一人物。即便被理解為同一人物,把她解釋為作者假想出的人物也是可以成立的。可見,單從作者-敘事者-主人公的關系來看,《女勇士》體裁無從確定。
勒瓊進一步指出,當主人公的名字與作者的名字有可能同一也有可能不同一的時候,作者對文本體裁的界定起著決定性作用。也就是說文本出版時作者在扉頁上標明的體裁即為文本體裁。這有三種情況:虛構契約(版權頁上標明是虛構敘事),零契約(版權頁上沒有任何標注)和自傳契約(版權頁上標明是自傳)。基于此,我們有必要來看一下《女勇士》出版時的體裁標注情況。
紐約古典書籍出版社出版的《女勇士》(1977)在其版權頁上標明這本書是一部“傳記”(biography),在印刷頁的最后一頁的左上角上印有“自傳”(autobiography)字樣。四月古籍出版社國際版(1989)的版權頁上表示這本書應歸為傳記。而英國斗牛士出版社(Picador)2002年的版本在版權頁上沒有提供任何關于文類劃分的字眼。讀者或許質疑,版權說明應該是出版社的最終決定。事實也確實如此。湯亭亭的編輯克諾夫(Knopf)曾坦言“(《女勇士》)可以被劃為任何體裁,但是一般作者的第一部小說都比較難賣。我很清楚如果作為自傳進入市場,它大賣的幾率會大大提升”{12}。換言之,這是出版社考慮市場因素做出的裁定而非作者的決定。我們再來看看真實作者對這部作品體裁的態度。在1977年的一次采訪中,湯亭亭說到“在我把文本寄給出版社的時候,我覺得它應該是一部小說。它必須是一部小說。”繼而說到“(敘事者)的名字不是瑪克辛(Maxine),那是我的名字”{13}。稍后她的態度有了動搖,說“我想我確實覺得它更像小說,但是什么賣得好......”{14}回答的語氣愈漸微弱,足以說明她的態度開始曖昧。幾年之后的又一次采訪中,她的態度變得更委婉了:“我的編輯告訴我非虛構類作品是對我的作品的最恰當歸類,非虛構作品包羅萬象,甚至詩歌也屬于非虛構類。”{15}再之后她的態度越來越不堅定,但她還是謹慎地避免承認《女勇士》是自傳。她只是說“如何歸類對我而言無關緊要,可是好像很多人都很在乎……我想如果稱之為小說,應該是對的。”最后她提供了一個更加成熟、圓滑的解釋:她創造了一個新的體裁,“我決定我是在給虛構的人寫傳記和自傳。”{16}至此,湯亭亭最終認可《女勇士》是一部自傳,盡管是一部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自傳,一部“虛構”的自傳。她為它取了一個特殊而別致的名字,“神話式精神自傳”(mythopsychic autobiography){17}。
勒瓊的公式只涉及作者,并未區分隱含作者和真實作者,如果把“作者”概念加以區分,可以看出,關于《女勇士》體裁界定上隱含作者和真實作者的立場并不一致。根據韋恩·布斯(Wayne Booth)在《小說修辭學》(The Rhetoric of Fiction)中的定義,隱含作者指讀者在文本所體現出的特定立場、觀點、態度及價值觀基礎上構建的作者形象。如上所述,通過文本,讀者很難確定《女勇士》的體裁,隱含作者并未提供任何關于其體裁的暗示。另外根據申丹的定義,隱含作者是“在特定寫作狀態中”{18}的作者,而湯亭亭曾坦言“或許在我的人生中,我的很多感受和文中小女孩的感受是一致的,但是當我寫這本書的時候,我鐵定不是這么想的。”{19}此即表明隱含作者否認自己是作品主人公,即隱含作者并不認為《女勇士》是一部自傳。然而,真實作者態度的搖擺不定使得其體裁界定從最初的小說慢慢過渡到了自傳。
因此,有必要對查特曼的敘事交流圖做如下修訂:
真實作者雖然處于創作過程之外,處于文本內部結構之外,但其立場依然對文本敘事性質的界定產生重要影響,而這一界定是敘事交流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方面。
關于作者、敘事者和主人公三者關系的討論,法國敘事學者熱耐特(Gérard Genette)等在《虛構敘事、事實敘事》(“Fictional Narrative, Factual Narrative”)一文中也有精彩呈現。文章依據三者不同的關系來界定敘事文本是虛構性敘事還是史實性敘事。該文用5個三角形直觀地標明5種關系及其相應的敘事模式:
并對五個三角形關系做出解釋,指出當作者和敘事者同一時,文本即為事實性敘事,當作者和敘事者不同一時,文本為虛構性敘事{20}。換言之,在事實性敘事中,敘事者的獨立自主敘事權威被作者占據,因此作者要為文本的真實性負責;而在虛構性敘事中,作者虛構了一個敘事者,無需對文本的真實性負責。這從敘事權威的角度為華裔陣營堅決否認《女勇士》為自傳體裁提供了最核心、最實質性的解釋。一旦認定這部作品為自傳就意味著作者/敘事者默認文本中的敘事為事實性敘事,作者要為文本的真實性負責。然而,作品中卻存在著大量個人感情色彩濃厚與不符合事實的筆觸。“不可靠敘述”作為一種敘事策略指未按隱含作者規范展開的敘述,然而《女勇士》體裁紛爭所討論的敘述不可靠性超越了這一敘事常規,不僅包括敘事者的不可靠,而且包括對隱含作者和真實作者可靠性的質疑。這一點在華裔美國批評家看來暗藏著很嚴重的政治敘事后果。
在華裔評論家看來,《女勇士》如果被界定為自傳無疑會誤導美國主流讀者,并加劇華裔美國人的“他者”(Other)形象。在美華裔移民早已被主流社會貼上了文化他者的標簽,從華裔社區走出來的任何一位作者一旦以自傳形式發表任何一部作品都會被美國大眾讀者視為是整個華裔的代表。凱瑟琳·馮(Katheryn Fong)一針見血地指出“作為虛構作品,這些故事很有創造性,有形象的畫面感和情感。但問題是,[一旦界定為自傳]非華裔讀者在閱讀時會把他們當作對中國歷史和美籍華裔歷史的真實記錄”{21}。因此,華裔美國批評家就兩個問題提出了質疑:《女勇士》中的文本內容都是事實嗎?湯亭亭有資格代表整個華裔社區甚至是中國文化來發言嗎?很明顯,對他們而言,兩個答案都是否定的。但是,非華裔美國文學研究者沒有足夠的背景文化知識來識別《女勇士》文本中的“事實”與“虛構”,也沒有華裔美國評論家對在美華裔處境的政治敏感度,因此也就相應不可能預見到這一敘事影響。通常情況下,作者借助文本引導讀者參與敘事進程進而實現其“說服”過程,但《女勇士》所面對真實讀者的獨特性卻加劇了其文本類型的爭論,對敘事交流的動態過程產生反作用力。因此,可以對查特曼的敘事交流圖做進一步修訂:
真實讀者雖然也處于創作過程之外,處于文本內部結構之外,但其閱讀體驗參與了文本動態運動,深刻影響文本敘事性質的界定以及由此產生的文本價值和意義。
鑒于上述分析,隱含作者和真實作者態度的不明確以及兩者之間立場的分歧,再加上真實讀者的多樣性共同構成《女勇士》作者與讀者在敘事交流過程中遇到的不同尋常的障礙,而這一障礙無疑引發了不同陣營的不同呼聲,甚至給《女勇士》和湯亭亭帶來負面評價和攻擊。從敘事交流的角度來看待《女勇士》的文體紛爭,無疑給這一現象的解讀提供了另一個切入點,也進一步對查特曼的敘事交流模式提出補充,強調真實作者和真實讀者對文本敘事交流產生的直接影響以及對文本終極意義生成所起的重要作用,折射出《女勇士》的后經典敘事傾向。
自傳-自傳體-后現代自傳體
同一文本引出美國評論界如此不相一致的闡釋和爭論,既證明了《女勇士》文本意義的豐富性,也表明其中每一單獨解讀都是片面的,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否認了該作品內涵的多樣性{22}和敘事技巧的復雜性。本文第二部分嘗試以自傳、自傳體小說和后現代自傳體小說的關系出發,深入剖析《女勇士》的敘事特征,并探討其對傳統自傳體小說敘事的“循規”和“逾規”,進而提出《女勇士》是一部后現代自傳體小說,嘗試對《女勇士》體裁界定提供一個新的視角,以把握其豐富內涵。
詹姆斯·奧爾尼(James Olney)曾指出區分“自傳”和“自傳體的”必要性{23},后者脫胎于前者,往往指涉具有自傳性質的文本創作,以自傳體小說為最常見形式。從根本上講,自傳體小說以缺乏上文勒瓊所提“自傳契約”而區別于自傳,主要創作特征為(1)自傳體小說的主人公與作者密切相關;(2)自傳體小說著力探尋自我,是一個自我身份建構的過程;(3)自傳體小說體現了虛構性與真實性的融合。根據這三個特征,《女勇士》完全可以被界定為自傳體小說,是自傳和小說的結合。另外,勒瓊也對自傳體小說的界定提出過較為合理的解釋,他提出當讀者以他/她猜測到的一些類似素材為基礎,判斷作者和故事人物同一,但作者卻否認此同一性,或至少不明確予以肯定時,即可將這樣的虛構文本稱為自傳體小說{24}。據此,《女勇士》無疑也是一部自傳體小說。
雖然《女勇士》遵守了以上自傳體小說的敘事常規,但是文本本身又蘊含著非常明顯的敘事逾規,這些敘事逾規本身帶有異常鮮明的后現代特征,使得《女勇士》不僅成為一部自傳體小說,更成為一部后現代自傳體小說,其體裁界定的合法化也據此完成。
1. 非線性敘事+非連貫主人公=結構松散最大化
《女勇士》由5個相互獨立又相互聯系的短篇故事組成,每個故事的獨立性都很強,以至于讀者甚至可以把它當作一部短篇小說集。事實上第一個故事《無名女人》在《女勇士》出版之前確實曾以短篇小說的形式獨立發表。開篇故事《無名女人》圍繞“我”的姑媽展開,發生在1949年之前的廣東;第二個故事《白虎山學藝》對花木蘭替父從軍的傳說進行改編,時空跨度很大,從幾千年前的中國到當代美國;接下來《鄉村醫生》是母親英蘭的傳記,發生在抗日時期的廣東;第四個故事《西宮門外》追述了阿姨月蘭來美尋夫的前因后果,時間跨度較小,從月蘭抵達美國到她去世短短一年;最后《羌笛野曲》圍繞小女孩“我”的童年展開。因此,五個故事并沒有一個顯而易見的敘事主線,也沒有統一的情節安排,傳統自傳體小說的線性敘事和連貫主人公也明顯缺失。
在《無名女人》里,從“我”的敘事聲音和視角的變化可見,“我”由一個剛剛初潮的小女孩慢慢長成一個具有獨立思想的成年女性,再到最后是孕育新生命的母親;然而到了第二章,“我”又變成了充滿幻想的小女孩,還把自己想象成花木蘭的化身,整個故事在“我”的腦海中展開,最后回歸美國現實;《鄉村醫生》中,“我”一會兒是向媽媽提問的小女孩,一會兒又變成滿頭白發的成年女性;第四章全知敘述者講述月蘭的故事,“我”完全退場;最后一章,“我”又變回小女孩,展望未來,希望自己可以像蔡琰一樣,用文字發聲。可見,整個文本的敘事一直處于一個跳躍的狀態,時間隨敘事的需求而變,沒有一個連貫的敘事線索。另外,每章都分別圍繞一個敘事中心展開,雖然幾個故事靠“我”的敘事而串聯起來,但每章中的“我”扮演的角色都不一樣,甚至“我”都很有可能不是同一個人。這樣破碎的敘事時間和處于分離狀態的主人公,使得文本敘事結構松散到最大化。
2. 五個主人公+兩個敘事者=去自我中心化
德里達后現代理論中的一個核心概念是去邏各斯中心主義,即對二元對立進行解構,針對二元結構中永恒中心,比如,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對立中的口頭語言,男性和女性對立中的男性,自我和他者(Other)對立中的自我。去中心主義成為后現代寫作的一個標志特征,《女勇士》亦不失為一絕佳例證。這部小說的去自我中心化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為對自傳中被聚焦者,即主人公的去中心化。如上所述,五個故事分別圍繞五個主人公展開,每個敘事分別通過不同的聚焦對象展現人物從表象到內心、從感性認知到理性批判的一個過程。分散的敘事不僅使得敘事結構呈現松散狀態,而且使得傳統自傳體小說中的中心人物被消解,自傳中包含大部分他傳。
其二為對自傳體小說中敘事者的去自我中心化。自傳體小說大多采用第一人稱敘述,且多同時采用經驗自我與敘述自我在回顧性視角中的雙重聚焦,以構成敘事張力,并在張力中透露自傳體中成長小說的元素,與此同時,敘事眼光與敘事聲音得以重合,增強文本敘事的可信度,所以整個敘事始終保持敘事者的敘事權威。然而在《女勇士》中,在以“說故事”(talk-story)的形式展開的敘事進程里,有媽媽和“我”兩個敘事者,兩個敘事眼光、兩個敘事聲音,整個敘事構成多重聚焦,共同挑戰傳統自傳體小說中唯一敘事者的敘事權威。小說五個故事蘊藏著同一個敘事模型:同一故事再敘述。無名姑姑的故事、花木蘭的傳說、母親英蘭的親身經歷、月蘭尋夫的過程以及女詩人蔡琰的境遇,都分別由媽媽和“我”以講故事的形式傳遞給讀者。在兩次蘊含不同敘事聲音、敘事視角以及敘事立場的敘述中,不同聚焦者對同一被聚焦者的不同敘事不僅使得人物形象更多面,呈現立體狀態,而且凸顯兩個敘事者之間的交流和對話,整個敘事呈現復調狀態,一個全知全能、處于中心和支配地位的敘事中心被解構了。在五個故事的敘事進程中,兩個敘事聲音處于此消彼長的狀態,女兒的成長伴隨著對母親敘事權威的抗爭,也從敘事的角度暗示了女兒對以母親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疏離感。直到故事最后,女兒決定和母親一起來完成“說故事”,敘事者的去自我中心過程完滿結束。
3. 多個敘事人稱轉換+第一人稱敘事中的轉換結構=異故事與同故事相結合
傳統自傳體小說多采用第一人稱敘事,但也有少數采用第三人稱敘事,比如伍爾夫的《奧蘭多》、勞倫斯的《兒子與情人》等,前者采用同故事敘事(homodiegetic narration),后者采用異故事敘事(heterodiegetic narration)。這兩個概念的分類依據是敘事者和故事之間的關系:同故事指敘事者處于被敘述事件中,參與了整個事件的敘述進程;異故事指敘事者處于被敘述事件之外,未介入到敘述事件的進程中。
《女勇士》不僅在多個敘事視角之間轉換,也采用了不僅一個敘事人稱。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章都采用的第一人稱敘事,而第四章采用第三人稱敘事,緊接著在第五章的開頭,敘事者借用一句“我弟弟跟我說的實際上是……”{25}把第四章的最高潮部分用第一人稱進行再敘述,使得整個文本處于多人稱敘事的靈活轉換當中。第三人稱敘事使得敘事的個人感情色彩得到淡化處理,敘事客觀性增強,更具有真實性和說服力,另外,也使得敘事者和讀者以及敘事者和主人公的距離最大化。因此,可以看出敘事者在第四章中試圖用最客觀最冷靜的視角來看待月蘭的悲劇并疏遠她和月蘭的關系,而且敘事者在整個敘事進程中都沒有添加任何個人評論,不僅沒有介入敘事而且很嫻熟地實現了敘事者的隱退。這樣異故事敘事在《女勇士》中得到了完美演繹。然而,第五章開頭一句簡短的開場把第四章精心設計的敘事策略輕而易舉地推翻,最主觀的視角、最強烈的個人色彩、敘事者和讀者、敘事者和月蘭最短的敘事距離等等使得第一人稱敘事與第三人稱敘事輕松接軌,異故事已經不再是異故事,同故事也很難說是單純的同故事,最后呈現一個異故事與同故事相結合的敘事畫面。
異故事和同故事相結合的另一個敘事策略是第一人稱敘事中轉述結構的運用。這一結構指的是敘事行為雖然由第一人稱敘事者承擔,可是卻需要借助另一位敘事者的口吻來敘述故事,因所敘述素材并非其所親歷。如上所述,《女勇士》五個章節都蘊藏著同一個故事被敘述兩次的敘事模型,先是母親敘述,而后“我”用“我”的方式實現再敘述,敘事者很巧妙地通過“再敘述”使得同一個故事穿過不同的敘述層,成功地把他人的故事轉換成她自己的故事。比如,第二章花木蘭的故事。第一人稱敘事轉換結構使得這個故事呈現四個相關的敘事層:(1)花木蘭的故事;(2)媽媽給經驗自我講故事的故事;(3)敘事者講述的關于經驗自我聽媽媽講故事的故事;(4)隱含作者的故事,即整個故事文本。第一人稱轉述結構給予敘事者足夠的自由穿梭在這四個敘事層之中,“再敘述”也使得“我”最終從故事之外走入故事之內,無名女人的故事最終變成了“我”的故事的一部分,很難確定哪一部分屬于異故事,哪一部分屬于同故事,最終異故事和同故事難以區分,各敘述層次相互融合。
結論
《女勇士》的體裁紛爭不僅讓讀者思考其中原因,也使得讀者對傳統體裁的界定提出質疑。經過對敘事交流過程的深入分析,可見真實作者和隱含作者之間立場的不符以及真實讀者的多樣性是造成文本體裁不確定性的根本原因。另外,我們也會發現《女勇士》可以被當作自傳體小說來讀,但是又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自傳體小說。非線性敘事和非連貫主人公形象使得文本敘事結構松散最大化,圍繞五個主人公展開的故事和兩個敘事者的敘事模式促成文本的去自我中心化,多個敘事人稱的自由轉換以及第一人稱敘事中的轉換結構完成了敘事中異故事與同故事的融合。這些明顯的后現代敘事逾規足以讓這部自傳體小說成為一部后現代自傳體小說。耶魯大學教授艾米·亨格福特將《女勇士》稱為“小說或傳記”,似乎暗示在后現代敘事語境下我們無從也沒有必要嘗試去斷定其體裁。然而筆者認為后現代的開放性、流動性和不確定性恰恰為探究《女勇士》的體裁敞開了空間,而此探究過程反過來又拓寬了后現代文學體裁的研究視野。
①{19} Kubota, Gary.“Maxine Hong Kingston: Something Comes from Outside Onto Paper” [J]. 1977. Conversations with Maxine Hong Kingston. [C] ed. Paul Skenazy and Tera Martin.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8. p.2.
② Gotera, Vicente F..“Ive Never Read Anything like It: Student Responses to The Woman Warrior. ”[J] Approaches to Teaching Kingstons The Woman Warrior. [C] ed. Shirley Geok-lin Lim. New York: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991. p.71.
③ Huntley, E. D..Maxine Hong Kingston: A Critical Companion[M]. Westport: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2001. p.89.
④ Yalom, Marilyn,“The Woman Warrior as Postmodern Autobiography”. Approaches to Teaching Kingstons The Woman Warrior, ed. Shirley Geok-lin Lim. New York: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991. p.112.
⑤ Kennedy, Colleen &Deborah; Morse,“A Dialogue with(in) Tradition: Two Perspectives on The Woman Warrior”. Approaches to Teaching Kingstons The Woman Warrior, ed. Shirley Geok-lin Lim. New York: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991. p.124.
⑥{15}{21} Sau-ling Cynthia Wong,“Autobiography as Guided Chinatown Tour? Maxine Hong Kingstons The Woman Warrior and the Chinese American Autobiographical Controversy”. Maxine Hong Kingstons The Woman Warrior: A Casebook. Ed. Sau-ling Wo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32, p.30, p.30-31.
⑦ DianeSimmons, Maxine Hong Kingston.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99. p.41.
⑧{23} James Olney,“The Ontology of Autobiography”Autobiography, Essays Theoretical and Critical.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p.4.
⑨ Chatman, Seymour. Story and Discourse[M]. Ithaca & London: Cornel UP, 1978. p.151.
⑩ M. H.Abrams,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Fort Worth: Harcourt Brace College Publishers, 1993. p.15.
{11}{24} PhilippeLejeune,“The Autobiographical Pact”. On Autobiograph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9. P4, p.135.
{12}{13}{14} David Leiwei Li,“Re-presenting The Woman Warrior: An Essay of Interpretive History.”Critical Essays on Maxine Hong Kingston. Ed. Laur E. Skandera-Trombley. New York: G. K. Hall & Co., 1998. p.189.
{16} PaulaRabinowitz, “Eccentric Memories: A Conversation with Maxine Hong Kingston”. p.75.
{17} Neila C.Seshachari,“Reinventing Peace: Conversations with Tripmaster Maxine Hong Kingston”1993. Conversations with Maxine Hong Kingston. ed. Paul Skenazy and Tera Martin.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8. p.198.
{18} 申丹:《再談隱含作者》,《江西社會科學》2009年第2期。
{20} GérardGenette,Nitsa Ben-Ari, Brian Mchale.“Fictional Narrative, Factual Narrative”. Poetics Today, Vol.11, No.4, Narratology Revisited II(Winter, 1990), p.765.
{22} 劉英,程廉:《〈女勇士〉中的多重視角:女性主義與巴赫金對話詩學的交融》,《四川外語學院學報》2003年第6期,第47-50頁。
{25} Maxine H. Kingston, The Woman Warrior: M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M]. London: Picador. 2002.
(責任編輯:黃潔玲)
Abstract: Since its publication in 1976, The Woman Warrior, by Maxine Hong Kingston, has been causing a sustained and heated debate about its genre in the American world of letters, with critics arguing about whether it is an autobiography, or a fiction, or an autobiographic novel or a postmodern autobiography. Based on the mode of narrative communication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al author, the hidden author, the narrator, the protagonist and the real reader in analysing the root cause of this debate surrounding The Woman Warrior, apart from gaining peeps into the following or breaking of the rules in the traditional autobiographic narration, based on the narrative features of autobiography, autobiographic fiction and postmodern autobiographic fiction, with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novel is a postmodern autobiographic novel, in an effort to expand the vision of research on the postmodern literary genre.
Keywords: The Woman Warrior, narrative communications, autobiography, postmodern autobiographic fi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