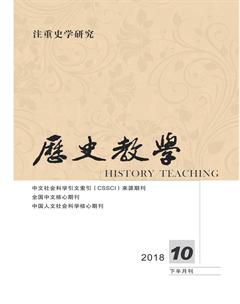范睢之死新論
摘 要范睢是戰國秦昭襄王時期著名的客卿,功與過皆昭然于史冊。然而,史書對其結局的記載卻比較模糊,引發了后世學者的不同判斷。秦簡《編年記》出土后,昭王五十二年的記載被學者視為范睢“非善終”的鐵證,由此,范睢“非善終說”成為學界的主流觀點。本文通過細致的考證,認為僅憑秦簡《編年記》的記載得不出范睢“非善終”的結論,系統梳理各類材料,可知其結局應是善終,但其死因卻與趙國實施的反間有重大關聯,因而只是形式上的善終。對這一問題的探討,既可以深刻地揭示戰國晚期各諸侯國之間無所不用其極的斗爭謀略,又能夠推動秦國法律制度、客卿制度等的研究。
關鍵詞范睢,秦法,趙國,反間,結局
中圖分類號K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57-6241(2018)20-0043-07
范睢,是秦昭襄王時期著名的客卿,與秦孝公時期的商鞅、秦惠文王時期的張儀、秦莊襄王時期的呂不韋及秦王政時期的李斯齊名。其主要功績在于:對外,他明確提出了“遠交近攻”之策,奠定了秦國對山東諸國有效實施蠶食鯨吞的戰略基調。對內,他敢于揭露秦國外戚與宗室貴族專權的弊端,直接促成了秦國王權的加強。這兩個方面都為秦統一全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史記》記載:“昭王得范睢,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①所言誠是。其主要過失在于:一是缺乏大局意識,為與武安君白起爭功,譖殺之,斷秦臂膀。此見載于《史記·范睢蔡澤列傳》。二是用人唯親,有失察之過,導致秦在對外戰場上的失敗。史載他“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于秦”。②毋庸置疑,這是一位重要而復雜的歷史人物,功與過皆昭然于史冊。當今史學界對他的關注與研究集中在以下兩個問題上:一是其稱名,范雎乎?范睢乎?二是其結局,善終乎?非善終乎?對前一個問題,我們曾有專文進行討論,③肯定其稱名以“范睢”為確,此不贅言。近日梳理相關材料,對其結局有一些新的思考,不揣谫陋,寫就拙文如下,愿與諸師友共同探討。
《史記·范睢蔡澤列傳》是對范睢其人生平、事跡記載最為詳盡的文獻。然而,這一記載止于燕人蔡澤得知范睢因用人不當而導致極端惡劣的后果之后,入秦勸他識時務、功成身退、避位讓賢,范睢信其說,“因謝病請歸相印”,之后“范睢免相”。④
范睢免相后的命運如何?太史公沒有后續記載,因而引發后世學者的不同判斷:
(一)善終說。這種觀點認為秦昭襄王念范睢功大,未再追究范睢之責,使其得以善終。元代學者馬端臨在《文獻通考·封建考六》中就說范睢“幸善終”。⑤
(二)非善終說。這種觀點認為秦法嚴厲,范睢免相后還是未能逃脫不得善終的命運。這一結論的主要依據是《史記》《戰國策》和云夢秦簡《編年記》的相關記載。《史記·范睢蔡澤列傳》在記“鄭安平……以兵二萬人降趙”后,繼言道:“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①《戰國策·秦策三·秦攻邯鄲》篇記載王稽被軍吏舉報欲反后,“秦王大怒,而欲兼誅范睢”。②云夢秦簡《編年記》載昭王五十二年(前255年):“王稽、張祿(筆者按:范睢入秦后更名張祿)死。”③這樣形成的證據鏈,使這一派學者相信,范睢之死并非善終。尤其是云夢秦簡《編年記》的出土,更堅定了這一派學者的判斷。
細分起來,持范睢“非善終說”的學者,對其具體死因,又有不同解釋:
一種觀點認為范睢是“請藥自殺身亡”。
秦史專家馬非百是這種觀點的代表,“其死法,則不是明正典刑,而是‘請藥賜死。且其事進行甚秘,不為外人所知。至《大事記》著者則身為治獄吏,此等重大檔案,皆其平日所習知,故得詳記之耳”。④不難看出,馬先生的結論是依據《戰國策》和《編年記》的記載得出的,《戰國策·秦策三·秦攻邯鄲》篇王稽通敵事泄后,有范睢對秦昭襄王的一段陳情:
臣,東鄙之賤人也,開罪于楚、魏,遁逃來奔。臣無諸侯之援,親習之故,王舉臣于羈旅之中,使職事,天下皆聞臣之身與王之舉也。今遇惑或與罪人同心,而王明誅之,是王過舉顯于天下,而為諸侯所議也。臣愿請藥賜死,而恩以相葬臣,王必不失臣之罪,而無過舉之名。⑤
這段話有幾層含義:1.范睢在人生低谷時奔秦,秦昭襄王信任、舉用了他。2.將范睢明正典刑會讓天下諸侯議論秦昭襄王用人不明。3.范睢愿意“請藥自殺”,偷偷死去,這樣可以保全秦昭襄王的顏面。4.范睢希望秦昭襄王能顧全他死后的哀榮,以安葬“相”的禮節來安葬他。而《編年記》明記王稽、范睢死于同年。兩相結合,很容易得出馬先生的結論。
沈長云師也有類似的看法,他在《士人與戰國格局》一書中寫道:“當鄭安平降趙的消息傳至秦都后,就已有人彈劾范雎,以為其罪當收三族。當時秦王念范雎往日功勞,不忍加誅。及至王稽事發,昭王再也不能保住范雎了,范雎也自覺無顏再茍活于天地間,遂請藥自殺身亡。”⑥(筆者按:這段話中的“范雎”,原書如此,仍依其舊錄出)
另一種觀點認為范睢是被秦王明正典刑殺死的。
同為秦史專家的林劍鳴就斷言:“鄭安平、王稽均為范雎保任,按照秦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王稽‘與諸侯通,其罪應誅,鄭安平降敵也屬重罪。因此,在公元前二五五年,范雎就同王稽一起被處以死刑。”⑦(筆者按:林書中作“范雎”)
黃盛璋在《云夢秦簡〈編年記〉初步研究》一文中也說:“而張祿死又和王稽相連,兩者必有聯系,看來秦王‘欲兼誅范睢,后恐成為事實”,又說:“按照秦法,范睢也要連坐,最后和王稽同樣處死,這是秦推行法治比較堅決和徹底的一個很好證據。”⑧
繆文遠也認為范睢未必“幸善終”,⑨他在《戰國策考辨》一書中對此進行了較為詳盡的辨證,最終推論:“殆昭王之于范雎始雖‘弗殺,終亦‘兼誅之歟?”⑩(筆者按:繆書中作“范雎”)
上述學者的推斷有傳世古籍的記載,更有出土文獻的佐證,故而,范睢“非善終說”基本占據了學術界主流,而“善終說”的聲音日益微弱。
我們重新梳理了現在所能見到的與范睢之死相關的資料,卻得出了與“非善終說”相反的結論。下面,試逐一進行分析。
(一)范睢舉用的鄭安平降趙后,秦昭襄王仍極力回護范睢。《史記·范睢蔡澤列傳》在“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之后,繼言“于是應侯(筆者按:范睢入秦后因功封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①可見,鄭安平事件沒有動搖秦昭襄王對范睢的信任,此時的秦昭襄王絲毫沒有懲處范睢的意思。
(二)秦昭襄王雖一度因王稽通敵而欲“兼誅”范睢,但是在范睢陳情后,仍舊寬宥了他。《戰國策·秦策三·秦攻邯鄲》篇在記載范睢陳情之語后,有秦昭襄王的表態:“王曰:‘有之。遂弗殺而善遇之。”金正煒曰:“‘有字當讀為‘宥。”②可見,王稽事件后,秦昭襄王確實一度動了誅殺范睢的念頭,但最終仍選擇了寬恕。
(三)云夢秦簡《編年記》的記載也不是范睢“非善終說”的鐵證。昭王五十二年的記載是持范睢“非善終說”的學者最為倚重的一條材料,然而《編年記》記載的是秦昭襄王元年至秦始皇三十年間秦國發生的大事,昭襄王五十二年王稽、范睢之死只是其中的一件大事而已,短短的“王稽、張祿死”五個字不能解析出范睢死于非命的內容。
由上所述可知,范睢“非善終說”的得出,實有對傳世文獻斷章取義之嫌,通讀之即可推翻,而所謂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共同構成的證據鏈也隨之斷裂,結果便是立論不堅,難以服人。
以上我們對范睢“非善終說”的三條最關鍵的證據進行了反駁,既然“非善終說”不能成立,那么,范睢就應該是“善終”的。下面所述,我們認為可以作為范睢善終的補充證據:
(一)依據文獻,可知范睢死時年齡已在70歲以上,這在先秦時期已屬高齡,昭襄王若加刑于一位有大功于秦國的古稀老人,只會讓天下人覺得秦王刻薄,故而有讓其“善終”的可能。據《史記·秦本紀》記載,秦昭襄王即位后,“三年,王冠”。③秦昭襄王三年為公元前304年,按照古人“二十而冠”的習俗,秦昭襄王即位時當為18歲。又據《范睢蔡澤列傳》的記載,范睢入秦在秦昭襄王三十五年,拜為客卿在秦昭襄王三十六年,這一年昭襄王應為54歲。至秦昭襄王五十二年范睢死,昭襄王應該是70歲。《戰國策·秦策三》有蒙傲對范睢說:“秦王師君,天下莫不聞。”④秦昭襄王也曾對平原君有言:“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⑤由以上兩則史料、尤其是昭襄王說話的口吻可以推知,他的年齡應小于范睢。范睢死時,秦昭襄王已經70歲,則范睢死時年齡應在70歲以上。范睢的古稀之齡應該是昭襄王考慮讓其“善終”的一個重要因素。
(二)據《范睢蔡澤列傳》記載,王稽通敵事泄,蔡澤即入秦勸范睢退位讓賢,范睢仔細聽取他的分析后,當即表示“先生幸教,睢敬受命”。⑥我們認為,范睢在王稽通敵事件發生后,及時聽從蔡澤的勸告,迅速做出“謝病請歸相印”的反應,讓昭襄王免于在秦法與人情之間為難,最終得以茍全性命,終老家中。
(三)范睢對蔡澤的成功舉薦,也可視為他實現了“軟著陸”的一個依據。《史記·范睢蔡澤列傳》記載范睢聽取蔡澤的勸告后,即入見昭襄王,言蔡澤“足以寄秦國之政”,請以自代,昭襄王隨即“拜為秦相”。⑦由此可以看出,秦昭襄王并沒有因為范睢此前舉用人的重大失誤而對他失去信任。這與魏惠王對待公叔座的態度形成鮮明的對比。公叔座為魏相,臨死向前來探病并詢問國事的魏惠王鄭重舉薦公孫鞅(即商鞅)以自代,魏王當面允諾,背后卻說:“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⑧兩例比較,可以看出,當此之時,范睢在秦昭襄王心中仍有較重的分量,昭襄王依然對其言聽計從,這應該是他沒有橫死的一個依據。
(四)比較《史記》記載的秦國著名客卿的結局,可以推導出范睢應是善終。在這部煌煌史著中,商鞅、張儀、呂不韋和李斯等人的死亡,太史公都有詳細的說明,商鞅的結局是“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遂滅商君之家”;⑨張儀的結局是在秦失勢,“群臣日夜惡張儀未已……張儀懼誅”,⑩奔魏,死于魏國;呂不韋的結局是“恐誅,乃飲鴆而死”;?輥?輯?訛李斯的結局是“論腰斬咸陽市……而夷三族”。①而唯獨將范睢的結局止于“免相”,不記范睢具體死法。司馬遷作《史記》,是有《秦記》為資料來源的,范睢為秦著名客卿,如果橫死,不會不在《秦記》中記載,而司馬遷為其作傳,也不會忽略其最終的結果。這讓我們相信范睢應該是善終的。
綜上所述,我們得出結論:范睢之死是善終。
正如上文所論,我們相信范睢之死既非秦王“賜藥”,更非“明正典刑”,而是善終。結論如此,卻不妨礙我們繼續追究他的死因,其死因依然有一些值得推敲的地方。
眾所周知,戰國晚期的歷史舞臺波云詭譎,變幻莫測,其中有一群神秘的人物活躍其間,這些人名不見經傳,卻發揮著令人膽寒的威力,他們就是在傳世文獻中頻繁出現的“間”,即間諜。
“間”之用,并不始于戰國,只是戰國這一特殊的歷史時期讓諜戰更加一發而不可收。當是之時,各諸侯國之間頻繁用間,其中反間②更具殺傷力。秦國在反間的使用上尤其成功,趙國的名將廉頗、魏國的信陵君無忌、趙國的武安君李牧,他們的失勢、出奔或死亡都有秦國的反間在暗中發揮著無可替代的作用。③
范睢,作為秦昭襄王的主要謀臣,是秦國反間策略的重要制定者,這在傳世文獻中有明確的記載。據《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秦、趙長平大戰期間,因為廉頗實施堅壁不戰、消耗秦軍的戰略,秦軍無如趙軍何,急于尋求戰機的秦國遂使出反間,散布流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信秦之間……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趙國中秦反間,臨陣換將,最終導致戰國晚期最慘烈的戰爭結局,“括軍敗,數十萬之眾遂降秦,秦悉坑之。趙前后所亡凡四十五萬”。④而秦國這次用間的主謀就是范睢,《史記·范睢蔡澤列傳》有言:“昭王用應侯謀,縱反間賣趙……秦大破趙于長平,遂圍邯鄲。”⑤趙國之精銳盡喪于長平。可見,先秦軍事史上最著名的反間案例正是范睢一手策劃并實施的,結果是給予了趙國致命的打擊。
梳理文獻后,我們發現,其實,趙國在反間的使用上毫不遜色于秦。長平之戰結束后,秦軍進圍趙都邯鄲,趙國面臨亡國之虞。危急關頭,趙國上下齊頭并舉,紓危解難,《戰國策·中山策》記載:“趙自長平已來,君臣憂懼,早朝晏退,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為務。”普通百姓則“涕泣相哀,勠力同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⑥除上述措施外,趙國也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全力實施反間,其矛頭直指長平之戰的兩大罪魁范睢與白起,并分兩個階段完成了對其二人的反間。
第一階段,離間范睢與白起,最終導致白起被范睢譖殺。
《戰國策·秦策三》“謂應侯曰君禽馬服乎”章,就是暗寫的趙國“反間”。此章記述的是長平之戰后,秦欲一舉滅趙,文中不具名的間者⑦對應侯范睢言:“武安君所以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余城,南亡鄢郢、漢中,禽馬服之軍,不亡一甲,雖周呂望之功,亦不過此矣。趙亡,秦王王,武安君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欲無為之下,固不得之矣。……故不如因而割之,因以為武安功。”鮑注:“如是則起無大功,睢不為之下。”補曰:“《史》‘無以為,此‘因字非。”⑧在這段說辭中,趙間極力夸大白起的功勞,甚至以西周王朝的開國元勛呂望與白起相比擬,并反問范睢“能為之下乎?”言下之意,是說范睢的運籌帷幄之功,不堪與白起的戰場殺敵之功相比。很明顯,這是要激化范睢與白起的矛盾。
《史記·白起王翦列傳》繼言之:“(秦)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①由此可知,范睢顯然聽信了趙間的說辭,力勸秦昭襄王與趙媾和,切斷了白起滅趙揚名、立不世之功的機會,白起與范睢之間的嫌隙由此生發。趙間一舉離間了秦國兩位重臣的關系,造成了二者的隔閡,并形成蝴蝶效應,導致范睢與白起、甚至秦昭襄王與白起之間的矛盾日益加深,最終范睢利用秦昭襄王對白起的猜忌,“言而殺之”。②至此,趙國順利完成了反間的第一階段,除掉了心腹大患秦武安君白起,且埋下了日后秦昭襄王對范睢不滿的種子。
第二階段,趙國精準抓住范睢舉人不當、觸犯秦法的機會,大施反間,致其去相位并憂死。
秦武安君白起死后,范睢遂成為趙國實施反間的頭號目標。然而,范睢自昭襄王三十六年拜為秦客卿始,至昭襄王五十年時,已為秦國服務長達十六年之久,為秦國的發展立下大功,蔡澤曾當面頌揚其功績,曰:“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③尤為重要的是,在這個過程中,范睢與秦昭襄王建立起了極其默契的君臣關系,昭襄王對范睢的厚遇更是超乎尋常,對此我們在文章的第二部分已有闡述,除前文提到的例證外,我們還可以試舉幾例以說明之:
1.范睢入秦后,秦昭襄王在對其官、爵的封賜上毫不吝嗇,先是任之為客卿,繼而任之為相,封應侯。而且應侯之封是當時較為罕見的實封,有封邑“應”。更不可思議的是,“‘應為太后養地”,“昭王奪太后養地以封睢”。④可以說,秦昭襄王給予范睢的是無上榮寵。
2.在對其權力的賦予上,秦昭襄王也是極為慷慨的。魏國使臣須賈就曾感慨:“天下之事皆決于相君(指范睢)。”⑤
3.秦昭襄王甚至親自出馬,為范睢鏟除仇人魏齊,為此不惜對鄰國使用詐謀。⑥
4.秦昭襄王對范睢禮遇優渥,尊稱其為“寡人之叔父也”,⑦以至于有人對范睢言:“秦王師君,天下莫不聞。”⑧
范睢與秦昭襄王之間這種融洽度極高的君臣關系,實屬罕見,也使趙國的反間難以施展。故而,與直截了當挑撥范睢與白起的矛盾、致白起之死的反間策略不同,趙國在對范睢的反間上,下了更大的功夫。《孫子·用間》有言:“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⑨趙國對范睢實施的反間,正是以其親信為突破口。
1.范睢任鄭安平、王稽為將,給自己埋下了隱患。
從傳世文獻可知,范睢最為親信的人物有二:鄭安平與王稽。鄭安平是其救命恩人,王稽是其仕秦的引薦人,均是在其人生的轉折點上發揮過關鍵作用的人物。而范睢又恰恰具備“一飯之德必償,睚眥之怨必報”⑩的性格。白起被譖殺后,秦國繼續攻趙,范睢“任鄭安平,使擊趙”。又以“王稽為河東守”。?輥?輯?訛很顯然,范睢對此時的秦趙戰局有過于樂觀的估計,匆匆將兩位作戰經驗不足的親信送到秦趙征戰的前線,明顯有爭功的意圖。遺憾的是,戰局的走向并沒有如范睢所愿,趙國聯合盟國魏、楚竭盡全力地進行自救和反擊,鄭安平、王稽先后陷于困局。據《史記·范睢蔡澤列傳》記載:“鄭安平為趙所困,急,以兵二萬人降趙。”王稽則在戰場上“與諸侯通”。?輥?輰?訛
這種局面,我們認為是非自然形成的,是趙國針對范睢的反間有序推進的結果。前引《孫子·用間》的文字提示我們,趙國對與己方對陣的秦國將領不可能不進行摸底,鄭安平與王稽屬范睢親信的情報應在趙國的掌握之中。也許就在這個時候,趙國高層敏銳地發現反間范睢的時機出現了。秦法嚴苛,盡人皆知,既然難以直接離間秦昭襄王與范睢,那么,將范睢陷于觸犯秦法的境地,是除去范睢的一條有效路徑,而“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輥?輱?訛鄭安平與王稽遂成為趙人眼中可以扳倒范睢的籌碼。
2.鄭安平在趙國封君,實質是趙國醉翁之意不在酒。
以上所言并非妄論,支撐這一推論的依據是事態的發展,鄭安平降趙后,被迅速封為武陽君,并領有封地。?輥?輲?訛我們曾有專文討論趙國的封君制度,其中談到:封君是一種殊榮,是時人夢寐以求的;在趙國,異姓封君極難,并舉廉頗為例,戰功赫赫的廉頗從趙惠文王時就以勇武名揚諸侯,然而直到趙孝成王十一年才受封信平君。①鄭安平以一介降將的身份,何德何能受封為君?故而,其封君應該有特殊的含義。《史記·樂毅列傳》曾記載趙國封從燕奔趙的樂毅為望諸君,并明言其目的是為了“尊寵樂毅以警動于燕、齊”。②那么,分封范睢的親信鄭安平是否為刺激秦昭襄王的神經呢?我們認為,這種可能性極大。
史載,鄭安平降趙后,依秦法,“于是應侯罪當收三族”,范睢因此而“席藳請罪”,“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③從秦昭襄王所出之令可以推知,鄭安平降趙的消息傳回咸陽后,秦都之中針對范睢應是物議如沸,而這與廉頗、信陵君、李牧等人遭受秦國反間時的場景如出一轍。故而,我們推測,此時應有趙間在咸陽城中推波助瀾。只是由于秦昭襄王對范睢極度信任,或者說因為秦昭襄王識破了趙國的意圖,而使趙國的反間一時未能奏效。
3.鄭安平之死,使我們確信他是趙國反間鏈條上的一環。
鄭安平在秦昭襄王五十年兵敗降趙,受封武陽君;至趙孝成王十一年(前255年)死,死后,其封地被迅速收回。前255年,也是云夢秦簡《編年記》記載王稽、范睢死亡之年。三個關系如此微妙之人,死于同一年,絕非偶然。王稽之死,史有明載:“王稽為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④王稽死于秦法的制裁,毋庸置疑。依照《編年記》的記載順序,范睢之死應在王稽之后(前文我們已論證其應是善終),而鄭安平之死,只在《史記·趙世家》中有一句簡單的交代:“(孝成王)十一年……武陽君鄭安平死,收其地。”⑤這則記載明確了鄭安平死亡的時間,卻沒有明確其死因,《呂氏春秋·無義》的一則記載則有相關信息的透漏:“鄭平于秦王臣也,其于應侯交也,欺交反主,為利故也。方其為秦將也,天下所貴之無不以也,重也。重以得之,輕必失之。去秦將,入趙、魏,天下所賤之無不以也,所可羞無不以也。行方可賤可羞,而無秦將之重,不窮何待?”⑥解析這段文字,我們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鄭安平之死在范睢之后。范睢死后,鄭安平的政治價值消失殆盡,而其“欺交反主”的行徑日益受到時人的輕賤,最終陷于窮途末路,不久亦死。而其死后,趙國迅速收回其封地的決絕做法,更是使人相信他是趙國用來對付范睢的一枚棋子,是趙國針對范睢反間的一個環節。
4.范睢實質是憂懼而死,因而只是形式上的善終。
范睢以古稀之年連遭故交背叛,即使秦王不加罪、秦法不加身,他也有很大可能憂懼而亡。
《戰國策·秦策三》有“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應侯內慚”的記載,⑦《史記·范睢蔡澤列傳》也有“應侯日益以不懌”的說法。⑧“內慚”“不懌”可證其“憂”。
秦昭襄王雖然在面對其親信接連叛國投敵的問題上,表現出成熟政治家的風度,即使有國內輿論的壓力,有趙國反間的推波助瀾,他依然定力十足,沒有牽連范睢。然而,其對于范睢也不是全然沒有失望的情緒。對此,史書中有兩次相關的記載:一次是王稽通敵后,“秦王大怒,而欲兼誅范睢”。⑨另一次即《史記·范睢蔡澤列傳》記載的“昭王臨朝嘆息……曰:‘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應侯懼,不知所出”。⑩秦王的“大怒”與“嘆息”是范睢“懼”之緣由。
鑒于此,我們推測:辜負秦王知遇之恩的愧疚、對秦法嚴苛的恐懼,以及對故交的極度失望,加上古稀之齡不堪心理重壓,范睢憂懼而死的可能性很大,這從表面上看依然屬于壽終正寢,但只是形式上的善終。
至此,趙國完成了其第二階段的反間,清除了蠶食鯨吞山東諸國的主謀范睢。
戰國時期,客卿對秦國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然而,這些客卿大多結局悲慘。史書中屢言秦王“有虎狼之心”“無親”,①對失勢客卿的誅殺極不留情。相較之下,范睢得以善終是僥幸的,雖然深究起來這樣的善終有流于形式之嫌,但畢竟保住了范睢的死后哀榮,更保全了秦昭襄王的顏面,應該算是秦昭襄王與范睢君臣之間相互成全的一種體現,這少有的平靜結局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秦國貫有的暴戾、強橫形象,讓我們重新認識到嚴苛的秦法也有法外容情的偶然。
范睢之死,背景因素復雜,深追其死亡真相,從大的方面來說,可以更深刻地揭示戰國晚期各諸侯國之間無所不用其極的斗爭謀略;從小的方面來講,則對于秦國法律制度、客卿制度等的研究有一定的推動意義。
【作者簡介】白國紅,天津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主要從事先秦史研究。
【責任編輯:杜敬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