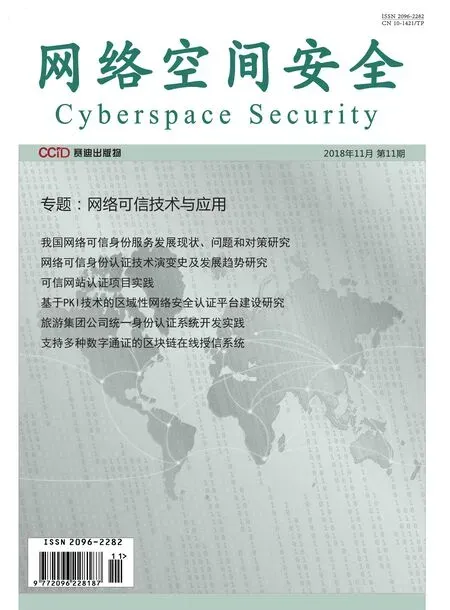美國對我國信息領域進行技術封鎖的戰略意圖及應對之策
王超
(賽迪智庫網絡空間研究所,北京 100846)
1 引言
近年來,我國信息領域核心技術能力的快速提升引發了美國強烈擔憂。2017年8月18日,美國正式對中國發起“301調查”,重點針對技術轉讓等知識產權領域。不久,美國總統特朗普發布命令,以國家安全問題為由,阻止了中國私募基金Canyon Bridge Capital Partners對美國芯片制造商萊迪思(Lattice Semiconductors)的收購,并授意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進一步加強對中國在IT領域投資的安全審查,強化對我國信息領域高科技封鎖。2018年4月16日,美國商務部宣布未來7年將禁止美國公司向中興通訊銷售零部件、商品、軟件和技術。美國政府的系列舉措對我國信息技術產品安全可控的實現進程造成較大沖擊,有必要深入剖析美國行動背后的戰略意圖,結合我國信息技術產品安全可控的實現困境,研究提出針對性的措施建議,為有關部門決策提供參考。
2 美國政府接連出手意欲何為
2.1 對我國信息領域實施高科技封鎖是美遏制我國技術發展的一貫主張
美國長期將我國作為假想敵,采取各種手段壓制我國信息領域的核心技術創新發展。
一方面,美國依據《瓦森納協議》《出口管理條例》等法律,以國家安全為由限制對我國出口材料、電子器件、計算機、信息安全等多個領域的“所謂”軍民兩用技術,涵蓋了高端芯片、高安全等級的操作系統和數據庫等技術產品,并根據技術發展情況不斷增補。對于不屬于美國本土的公司,如ARM等,由于其核心研發團隊在美國,也受到美國出口管制法律約束。
另一方面,美國高度警惕我國在芯片等高科技核心技術領域的海外收購,并多次以國家安全為名予以阻止,其影響范圍甚至由美國本土企業擴展到與美國利益相關的歐洲企業。2015年7月,美國政府以鎂光是美國惟一生產個人電腦所需動態隨機存取存儲器芯片的制造商為由,未批準中國清華紫光向鎂光科技(Micron Technology)發出的價值230億美元的收購要約。2016年12月,在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建議下,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發布行政令,叫停中國福建宏芯投資基金收購德國半導體企業愛思強。2017年9月,美國總統特朗普發布行政令,以“交易會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無法以緩和手段消除的風險”為借口,阻止了中國私募基金Canyon Bridge Capital Partners對美國芯片制造商萊迪思的收購。
2.2 開展“301調查”、阻止海外并購是美國維持信息領域主導地位的集中體現
近年來,我國通過海外并購、指令集授權、成立合資公司等方式,走上引進吸收再創新之路,大力推進安全可控的信息技術和產業發展,華為海思等部分廠商的產品性能已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引發了美國各界對中國以并購等形式獲取美國等國家信息領域核心技術的廣泛擔憂。美國政界人士和軍事領導人多次呼吁政府,嚴密審查中國在美國科技行業的投資;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USCC)發布年度報告,建議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阻止中國企業對美國半導體公司的收購;美國總統科技顧問委員會(PCAST)向總統提交的《維持美國在半導體行業的領軍地位》報告稱,中國的芯片業已經對美國的相關企業和國家安全造成了嚴重威脅,并建議美國總統下令對中國的芯片產業進行更加嚴密的審查。在此背景下,對中國發起“301調查”、阻止我國企業在芯片等領域的海外并購,成為美國防止我國獲取其信息領域核心技術、進一步鞏固其在信息領域主導地位的重要戰略手段。
2.3 制裁中興體現美國遲滯我國創新技術發展的堅定決心
近年來,隨著“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中國制造2025”等國家戰略的落地實施,我國制造業創新能力明顯增強,新技術突破帶動產業變革呈現加速態勢。為遲滯我國技術創新、產業發展,美國近期對我國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高檔數控機床和機器人、航空航天裝備、海洋工程裝備及高技術船舶、先進軌道交通裝備、節能與新能源汽車、電力裝備、農機裝備、新材料、生物醫藥及高性能醫療器械等十大行業出口進行制裁,美國官員更是直白地表示,美國此舉就是要遏制中國制造業升級,拖慢“中國制造2025”這一強國戰略。作為通信行業的龍頭企業,中興不可避免地成為首要打擊對象。為此,美國甚至難以顧忌Acacia、Oclaro、Lumentum、Finisar、Inphi、Fabrinet等美國諸多大型元器件供應商的利益,即便股價大跌、效益大降也要將中興拉下馬。
3 我國信息技術產品深陷安全可控實現難的困境
3.1 核心技術受制于人
當前,我國中央處理器、操作系統等信息領域核心技術受制于人,供應鏈關鍵環節缺失,難以掌握產業發展主導權。以芯片領域為例,全球主要高端芯片設計、生產和供應企業集中在美國,核心技術主要掌控在英特爾、AMD、高通、ARM、三星等外企手中。在PC和服務器領域,X86處理器中占據主導地位,Intel和AMD兩家擁有PC領域99%的市場份額,Intel在服務器領域擁有99%以上的市場份額。移動芯片市場則以ARM為主,高通、華為海思、聯發科、展訊等都屬于ARM架構陣營。DSP、GPU的核心技術掌握在美國TI、AMD等企業手中。芯片設計中用到的EDA設計工具,基本由Cadence和Synopsys兩家美國公司壟斷。
3.2 實現路徑搖擺不定
當前,我國信息技術核心技術發展方面仍存在自主創新和引進創新的路徑之爭,導致無法集中優勢資源實現技術突破,難以構建真正自主的產業生態體系。一方面,部分專家認為應該走獨立自主發展的道路,基于完全自主的技術突破擺脫技術引進、技術模仿對外部技術的依賴,其本質就是牢牢把握創新核心環節的主動權,掌握核心技術的所有權;另一方面,部分專家認為應該走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發展路線,在引進國內外先進技術的基礎上,實現學習、分析、借鑒和再創新,形成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新技術。
3.3 自主創新能力不足
長期以來,我國已經在信息領域形成對國外技術的體系性依賴,自主創新能力嚴重不足。一方面,在信息技術發展早期,我國過度重視經濟效益,對其中隱藏的網絡安全風險認識不足,“拿來主義”盛行,忽視了在基礎核心技術方面的自主創新,特別是芯片等核心技術往往在沒有消化和吸收的情況下就拿來使用,并在此基礎上發展上層應用技術,從而形成體系性依賴,人才、技術等存在較大缺失,從頭發展需要的投入巨大;另一方面,我國在材料、物理、數學等基礎科學上仍存在較大缺失,芯片制造材料和設備等缺少基礎科學支持,從根本上限制了芯片等核心技術的發展,導致芯片流片、封裝所需的重要材料和制造裝備嚴重依賴進口。
3.4 創新環境亟需優化
我國信息領域核心技術發展的創新機制仍不完善,自主創新環境亟需優化。一方面,我國推進信息技術產品安全可控的相關配套政策標準還不健全,核心技術引進缺乏統籌管理,安全可控缺少評價標準,導致技術引進混亂、同質化競爭嚴重等問題。以芯片為例,我國當前擁有MIPS、X86、Power和ARM等七種技術路線,存在較嚴重的碎片化問題。而有些企業直接使用國外硬核,并不具備培養自主創新能力的基礎,這些企業在市場上不能有效區分,嚴重挫傷自主創新企業的積極性;另一方面,我國信息技術產品協同創新機制尚不完善,產業鏈協同創新效應還未顯現。國家企業重視掌控產業生態主導權,如微軟和英特爾為推動PC產業發展,組成了“文泰來”聯盟(Wintel聯盟),微軟的視窗操作系統只配對英特爾的芯片,而國內企業仍多以“單打獨斗”為主,盡管龍芯中科以及飛騰和天津麒麟先后發起了以“龍芯CPU”,以及“飛騰CPU+麒麟OS”為核心的產業協作,但是協同創新和應用效果還未顯現,良性、共贏的產業環境仍需完善。
4 幾點建議
4.1 確立踐行安全可控實現路徑
一方面,盡快研究梳理信息技術產品的安全可控實現方式,形成清單,明確哪些技術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自主創新,哪些技術可以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另一方面,統籌規劃信息技術產品的安全可控實現,堅持開放創新,促進兩種路線最終走向安全、可控。對于CPU等最關鍵最核心的技術,必須立足自主創新、自立自強。市場換不來核心技術,有錢也買不來核心技術,必須靠自己研發、自己發展。應大力支持走自主研發路線的企業,使其不斷提高技術能力和產品性能,縮短與國外技術產品的差距。對于可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部分技術,要督促、引導相關企業真正吃透引進技術,將國外技術消化吸收并轉化為自主發展能力。
4.2 著力突破核心技術瓶頸
一是潛心發展基礎技術,充分發揮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等國家核心科研機構的作用,實現在材料、物理和數學等基礎技術上的突破,為發展高端技術產業提供支撐;二是加強對高端芯片、核心電子元器件、基礎軟件等開發周期長、資金回收慢的信息技術基礎產品的研發支持,推動核心關鍵技術實現突破,做到核心技術產品的可知、可編、可重構、可信和可用,形成自主知識產權,推動研究成果轉化;三是加強前沿科技布局,組織開展對光計算、生物計算、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的研究,夯實量子計算的技術優勢,搶占下一代信息技術至高點。
4.3 統籌推進信息技術產品國產化替代
一是建立信息技術產品安全可控評價機制。由國家網信主管部門牽頭成立工作組,結合網絡安全需求和我國實際,制定信息技術產品安全可控發展路線圖和時間表。劃定開展評價工作的對象,明確工作流程和依托單位。二是盡快啟動信息技術產品的網絡安全審查和強制性認證工作,依托信息技術產品安全可控評價系列標準,以試點方式將網絡安全產品的強制市場準入制度引入到核心信息技術產品領域,以評促改,以評促用,推動提升信息安全技術產品安全可控程度,創造安全可控產品市場應用空間,支持政府部門和重要領域率先采用安全可控的信息技術產品,逐步推進國產化替代。
4.4 積極營造良好創新發展環境
一是爭取更有利的國際貿易環境,作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中國應積極參與國際合作,爭取更多的合作伙伴,打破以美國為首的技術封鎖同盟;二是推進國際技術合作,依托華為、360等國內龍頭企業,不斷加強國際技術交流合作,積極爭取國際技術標準話語權,實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突破美國的科技封鎖線;三是促進產業鏈協同創新發展,組建、依托安全可控信息技術產學研用聯盟,設立“產業基金”“創新基金”,加強產業鏈上下游企業在戰略、技術、標準、市場等溝通協作,加強產業鏈上下游產品間的適配和協同應用推廣,形成協同創新和產業發展合力。
5 結束語
本文首先介紹了近期美國政府對我國采取的一系列技術封鎖舉措,分析了美國行動背后的戰略意圖,點出我國信息技術產品實現安全可控面臨著核心技術受制于人、實現路徑搖擺不定、自主創新能力不足、創新環境亟需優化等現實困境,提出了確立踐行安全可控實現路徑、著力突破核心技術瓶頸、統籌推進信息技術產品國產化替代、積極營造良好創新發展環境等相應舉措,希望能為有關部門決策提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