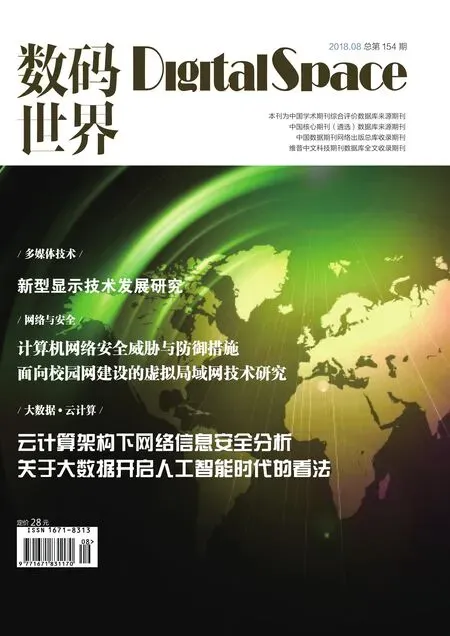淺談我國核電站的自動化設計與發展
谷春曉 李姿* 沈陽工學院
1 核電站發電的自動化設計原理
核電站是利用原子核裂變反應釋放出能量,經能量轉化而發電的。現以壓水堆核電站為例,說明其在壓水堆內,由核燃料235U原子核自持鏈式裂變反應產生大量熱量,冷卻劑(又稱載熱體)將反應堆中的熱量帶入蒸汽發生器,并將熱量傳給其工作介質——水,然后主循環泵把冷卻劑輸送回反應堆,循環使用,由此組成一個回路,稱為第一回路。這一過程也就是核裂變能轉換為熱能的能量轉換過程。
蒸汽發生器U型管外二次側的工作介質受熱蒸發形成蒸汽,蒸汽進入汽輪機內膨脹做功,將蒸汽焓降放出的熱能轉換成汽輪機的轉子轉動的機械能,這一過程稱為熱能轉換為機械能的能量轉換過程。做了功的蒸汽在凝汽器內冷凝成凝結水,重新返回蒸汽發生器,組成另一個循環回路,稱為第二回路,這一過程稱為熱能轉換為機械能的能量轉換過程。汽輪機的旋轉轉子直接帶動發電機的轉子旋轉,使發電機發出電能,這是由機械能轉換為電能的能量轉換過程。
2 核能安全出現危機
我國在日本福島核事故后,提出了安全、高效發展核電的方針,理論界、能源產業界對我國今后是否要積極發展核電,是否應經濟發展核電提出了質疑。
核電的安全、高效發展應該是安全、高效與經濟均衡發展。核安全是核能(電)可持續發展的前提與基礎,應置于一切核電活動之上,把“安全第一,質量第一”的方針落實到核電規劃、布局、設計、建造、運行、退役、廢物處置的全過程及所有相關產業。
3 發展核電的重要性
2010年,我國發電設備平均年利用小時數為4660h,其中火電5031h,水電3429h,而風電不足2000h。核電是穩定、可靠、可作為基本負荷的電能,年利用小時數在7000~8000h,是電站平均利用小時數最好的裝置。采用設備可用率來考察電站效率、效能是一個比較好的方法。如按核電站年利用小時數7446h(約合85%負荷因子)計,是發電設備平均利用小時數的1.6倍,火電的1.48倍,水電的 2.17倍,風電的 3.7~4倍。
4 既要人民安全也要經濟發展
日本福島核事故引起全世界對核安全、核電站安全的高度關注與重視“核安全是核能(電)的生命線”已成為共識。我國也暫時停止發展核電,不過很快想出兩全的解決方案。
2012年3月,“安全高效發展核電”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胡錦濤主席在首爾世界核安全峰會上強調中國將繼續安全、可持續發展核能。5月,國務院通過《核安全與放射污染防治“十二五”規劃及2020年遠景目標》。10月,國務院再次討論通過了《核電安全規劃(2011-2020年)》和《核電中長期發展規劃(2011-2020年)》。同日,國務院新聞辦發布《中國的能源政策(2012)》白皮書,闡述了我國能源總體部署,再次強調將安全、高效發展核電。11月,在“兩個規劃”批準后,我國核電發展的大門重新開啟。2012年11月,福清、陽江核電站4號機組同時復工,12月山東石島灣高溫氣冷堆示范工程開工建設。經過約一年半的安檢、評估、規劃后,中國核電產業重新啟動,而建設我國安全、高效的核電產業就是這次核電重啟的戰略與方針。
5 核安全與高效、經濟相均衡
能源、電力如果沒有經濟性,沒有成本、價格優勢,它就沒有市場,缺乏競爭力,該能源產品就缺乏生命力,最終將退出市場,核電也是如此。
核電的安全、高效、經濟三者既矛盾又統一。核電安全、高效發展會使研發費用增多,項目投資增加,電力成本加大,特別是首堆費用會增加50%以上。但隨著技術成熟,多堆建設,容量增大,比投資、發電成本會迅速下降。安全、高效給核電帶來經濟性的提高,可提高電站可靠性、效率和容量,延長運行周期,減少維修費用,杜絕事件和事故的發生,避免經濟損失。
6 總結
在此討論的是核電安全、高效、經濟三者之間的關系。我們講安全第一,核安全應置于一切核電活動之上。但核安全并不是各種安全措施的疊加,核安全也是有“度”的。我國核安全規劃提出了“十萬分之一”、“百萬分之一”兩個核電安全目標。這就是在實施核安全總目標及其他具體目標的條件下,當前我國核電安全標準的“度”。在此前提下,我們要使核電成本、價格下降,經濟性提高,即所謂的核電安全與經濟相均衡。
同樣,核電的高效發展也要與經濟相均衡。并不是核電設施越先進、效率越高、效能越優、規模越大就越好,這也有一個標準,就是先進、高效的核電站,必須是經濟、有競爭力的核電站,也就是要安全、高效、經濟均衡統一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