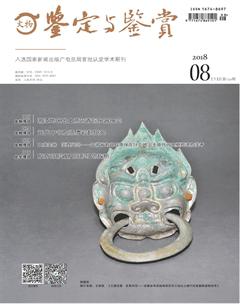吉林地區(qū)所見圓臺遺跡的年代探討
秦麗榮
摘 要:文章結(jié)合三普實地復(fù)查和對夫余文化的再認(rèn)識,對吉林地區(qū)第二次文物普查中命名為遼金時期烽燧圓臺遺跡的年代與性質(zhì)進(jìn)行了探討,認(rèn)為此類圓臺遺跡當(dāng)為具有軍事意義的漢代夫余國堡寨遺跡。
關(guān)鍵詞:圓臺遺跡;堡寨
吉林地區(qū)地處東北中部、松嫩平原南側(cè),是青銅時代西團(tuán)山文化的命名地和中心分布區(qū)。在20世紀(jì)80年代的第二次全國文物普查和2008年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中,吉林市周邊及地區(qū)所屬的永吉、蛟河、樺甸、磐石、舒蘭等五縣市均發(fā)現(xiàn)有以低矮山丘圓形頂為主要特征的遺跡,在二普中調(diào)查者將此類遺跡認(rèn)定為遼金時期的烽燧[1]。本文結(jié)合三普實地復(fù)查和近年來對夫余文化的認(rèn)識,認(rèn)為此類圓臺遺跡當(dāng)為漢代夫余國堡寨遺跡。在文中為表述方便,仍采用二普中的原用命名“烽燧”,不揣淺陋,談一下自己的認(rèn)識。
1 遺跡的基本特征
吉林市周邊此類遺跡如永吉縣西山灣烽燧、昌邑區(qū)柳條溝東山烽燧、豐滿區(qū)漂爾烽燧、磐石市余富西山烽燧、樺甸孤頂子烽燧、治安烽燧等,當(dāng)?shù)乩习傩斩嗨追Q之為“高麗城子”,它們均呈圓形或近似圓形的橢圓形,高出周圍地表,呈臺狀,高度從1米到8米不等,周圍有一周壕溝,均未經(jīng)發(fā)掘清理,其中個別遺跡似有門址或者臺階。
樺甸孤頂子烽燧,位于八道河子鎮(zhèn)向陽村北,其東、西兩側(cè)為溝壑,南面地勢開闊,一條小溪從山腳下流過。烽燧建于山頂端,山頂較為平坦,為一臺地,北高南低。烽燧平面為橢圓形,南北徑31米,東西短徑26米。周圍有壕溝,東南似有一門,寬約1米,通過壕溝可來往于內(nèi)外。烽燧中央略高于周圍,于此盡可眺望四方,視野開闊。
豐滿區(qū)漂爾烽燧,位于旺起公社漂爾大隊屯西南側(cè)一漫崗上。崗高出地面10余米,其北距公社所在地2千米,南與10千米外的摩天嶺遙遙相望,東臨小河,西靠長嶺。烽燧地面平坦,面積約1000多平方米,四周有人工挖掘的溝壕,東部邊緣為陡峭的斷崖,西部邊緣為峽谷,南北與一長嶺相接。從遺址向四周瞭望,除西部山嶺外,東、南、北三方數(shù)十里盡收眼底,而且從地理位置看,此地扼南北交通咽喉,其下即是吉樺公路。2008年10月三普時在對漂爾烽燧的復(fù)查中,發(fā)現(xiàn)該遺址平面近似圓形,且四面均勻分布著四個臺階,當(dāng)為進(jìn)出之用。
永吉西山灣烽燧遺址,地處黃榆公社平埠子大隊西北0.8千米處,遺址位于屯西一山頭上,當(dāng)?shù)胤Q之為“西山”或“山城”。山頭相對高度500米,東去0.5千米為平埠子北山遺址,東北連接起伏的山丘,西南面向開闊的平地,飲馬河由南蜿蜒而來,經(jīng)西側(cè)向北流去。山頭西南陡峭,東北平緩,依山傍水,視野開闊。烽燧平面呈橢圓形,長徑31米,短徑25米,周長100米,高于周圍4.5米,似一平臺,臺面平坦。有壕溝繞此一周,溝上口寬2.5米、深1.5米,為就地取土堆筑而成,壕溝是有意挖的。
西南屯烽燧與西山灣烽燧不但同處飲馬河右岸,而且周圍地理環(huán)境相似,都位于連綿起伏的山嶺中較為突出的山丘上,視野開闊。兩處烽燧相距僅11千米,可遙相互望。
柳條溝東山烽燧,位于兩家子公社柳條溝大隊東約1千米一座蒼翠的山崗上。其西面為柳條溝屯,東面1.5千米處有泉山,南面視野開闊,方圓幾百里盡收眼底,東南與松花江右岸的烏拉街公社遙遙相望,烽燧東西長40米左右,南北寬40米。三普中實地調(diào)查知整個遺跡為圓形,周圍有一周壕溝,中心高出四周1.5米左右,地表無用火痕跡。
永吉縣還有一處桄子溝烽燧,位于五里河子公社所在地西2千米桄子溝大隊隊部北側(cè)一高約30米的山頂端。此烽燧四周陡峭,峰頂有一塊面積約80平方米的平坦臺地。該地地理位置優(yōu)越,站在山巔處,可俯瞰整個五里河子公社。東2千米是吉林樺甸公路,西側(cè)山腳下五里河一支流繞山而過,周圍是萬畝良田,視野開闊。1983年二普時,采集到一些紅褐色夾砂陶片。
蛟河以及舒蘭部分地區(qū)此類遺跡與吉林地區(qū)其他縣市在形制上略有不同。蛟河此類遺跡亦分布在低矮山丘頂部,平面為圓形或橢圓形,整體呈圓臺狀,面積在1000平方米左右,與其他市縣類似。區(qū)別在于這一區(qū)域發(fā)現(xiàn)的此類遺跡其邊緣為一周凸起的黃土棱子,這種形制或為一種地域建筑特色。《蛟河縣文物志》記錄此類遺跡10余處,而且多集中在池水鄉(xiāng),松江、漂河、拉法、龍鳳等幾個鄉(xiāng)鎮(zhèn)也有發(fā)現(xiàn),均位于松花湖沿岸,當(dāng)為古代重要通道兩側(cè)。
2 遺址的年代與性質(zhì)
二普中,此類遺跡發(fā)現(xiàn)器物極少,其原因大概是此類遺跡均分布在山丘頂,多年無人類活動,地表植被茂密,不易發(fā)現(xiàn)。在永吉縣西山灣烽燧“僅在臺上采集到一件黃褐色陶片,另在山坡上采集到漢代殘鐵錛一件和泥質(zhì)繩紋陶片一件”[2]。2009年5月,在昌邑區(qū)柳條溝烽燧復(fù)查中,因該遺跡被新開辟為耕地,地表裸露出來,采集到陶片若干。陶片從質(zhì)地可分為三種,即夾砂紅褐色陶片若干、夾粗砂褐色陶片若干、泥質(zhì)灰陶質(zhì)地繩紋陶片一件。
根據(jù)吉林地區(qū)青銅時代文化特征判斷,第一種夾砂紅褐色陶片屬于吉林地區(qū)西團(tuán)山文化遺存。第二種夾粗砂褐色陶片是張忠培先生在《吉林市郊區(qū)古代遺址的文化類型》[3]一文中提到的以東團(tuán)山、帽兒山等遺址為代表的“文化三”考古遺存。林沄先生指出,“早先被張忠培命名為‘文化三的考古遺存在吉林市及其周圍地區(qū)分布甚為普遍,從文化特征來看,應(yīng)該就是夫余考古遺存”[4]。而在西山灣和柳條溝東山發(fā)現(xiàn)的泥質(zhì)灰陶質(zhì)地繩紋陶片,正是漢魏時期典型器物,故判斷此類遺跡的年代當(dāng)為漢魏時期。至于在此類遺跡中發(fā)現(xiàn)的西團(tuán)山文化陶片,則更進(jìn)一步證實了夫余文化是在西團(tuán)山文化基礎(chǔ)上發(fā)展而來的。
《三國志·魏志·東夷傳》中:“夫余在長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與高句麗、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方可二千里,戶八萬。其民土著,有宮室、倉庫、牢獄。多山陵、廣澤,于東夷之域最平敞……作城柵皆員,有似牢獄。”《后漢書·東夷傳》中有關(guān)夫余的記載基本與《三國志》相同,“夫余國在玄菟北千里,南與高句麗、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本濊地也……以員柵為城,有宮室、倉庫、牢獄”。《后漢書》中將《三國志》里“作城柵皆員”改為“以員柵為城”。筆者認(rèn)為“作城柵皆員”中的“城”與“柵”在古文中當(dāng)分別理解,“城”應(yīng)為土城,漢代所謂的“城”應(yīng)包括大型的城址和小型的軍事守備城。“柵”當(dāng)為木建,則可以理解為具有軍事意義的堡寨。《資治通鑒》中注:“壘城者,筑壘附近大城,猶今堡寨也。”[5]人們很早就知道在城市的邊緣設(shè)置以軍事為主的小型城壘作為據(jù)點,以烽燧與主城聯(lián)系,是為早期的防御體系。城堡的選址一般在高地或丘陵附近,主要為解決水源、交通等問題。秦漢時期,為了滿足野外軍事需要,通常都要在營地周圍構(gòu)筑以壕溝、圍墻為主體工程的營壘。這種營壘本因戰(zhàn)爭需要產(chǎn)生,后隨著筑城技術(shù)的提高,逐漸演變?yōu)楸ふ痆6]。吉林地區(qū)發(fā)現(xiàn)的這一系列圓臺、壕溝、土棱子等遺跡即為具有軍事性質(zhì)的夫余城柵。“柵”因其質(zhì)地不易留存,所以不見地面遺存,但保留了原有圓形形狀的臺體,相信今后對其進(jìn)行考古工作時必將發(fā)現(xiàn)圓形分布的柱洞。從圓臺遺跡的分布來看,其均為吉林地區(qū)從古至今交通要道,且依山靠水,既得居住之便,又具守備之勢。綜上所述,將其認(rèn)定為漢夫余時期堡寨遺跡,不僅與信史記載符合,而且與秦漢時期軍事堡寨在選址、營建方式、功能等方面特征相符合。
近年來,隨著東北史地研究的深入,學(xué)術(shù)界基本將漢魏時期的夫余王國確定在吉林市,林沄、李健才、武國勛等發(fā)表了多篇論文,論證吉林市當(dāng)為夫余王國的前期王城所在地。除了在吉林市帽兒山發(fā)現(xiàn)的大型墓葬群確定為漢魏時期夫余王國遺跡外,其他有關(guān)夫余王國的典型遺址、遺跡均未確定,這是不合符常理的。因此,重新定義為夫余堡寨的此類圓臺遺跡對進(jìn)一步認(rèn)識夫余王國將有重要的學(xué)術(shù)價值。
參考文獻(xiàn)
[1]景愛,董學(xué)增.吉林舒蘭縣古界壕、烽臺和城堡[J].考古,1987(2).
[2]吉林省文物志編委會.永吉縣文物志[M].吉林:永吉縣科技印刷廠,1985.
[3]張忠培.吉林市郊古代遺址的文化類型[J].吉林大學(xué)社會科學(xué)學(xué)報,1963(1).
[4]林沄.夫余史地再探討[J].北方文物,1999(4).
[5]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鑒:卷一百四十四[M].北京:中華書局,1956.
[6]李晴.宋明兩代軍事堡寨研究[D].天津:天津大學(xué),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