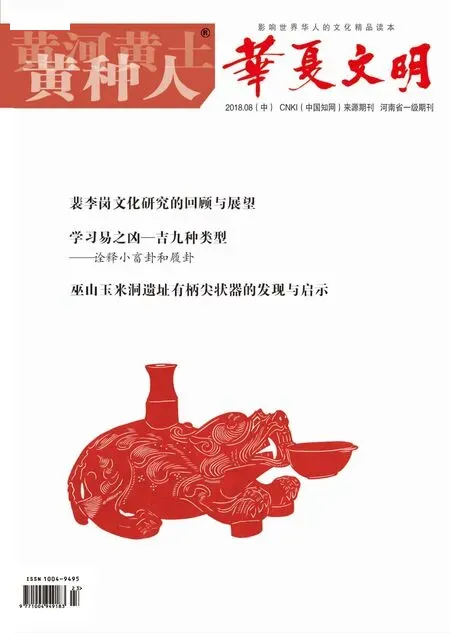規劃設計視域中文物建筑再利用芻議
□ 張 超 何建平
文物建筑作為一種建筑實體存在,是人類智慧與文明發展演進的重要佐證。習近平總書記近年對文物工作的重要指示中指出:“……努力走出一條符合國情的文物保護利用之路。”文物保護利用符合中國國情,要求我們的文物事業與我國現階段的社會經濟文化和生態相聯系,講究各類資源與文物保護利用間的協調發展關系。因此,我們進一步明確了文物建筑再利用的目的是為了協調發展,所以在文物建筑的開發和利用過程中“適度”尤為重要。
實踐中,文物建筑的再利用開發過程運用到大量規劃設計的專業知識,與考古學、博物館學結合后形成專業化的博物館展覽策劃設計與遺址公園規劃設計等專業類別更強的設計,至此設計行業的服務對象和專業程度分領域向社會各行業發展。始終沒有改變的是,任何設計都是為人服務的、“以人為本”的,文物資源通過規劃設計的途徑,被解讀展示出來,更富活力和吸引力,規劃設計成為大眾與文物之間溝通、傳遞信息的有效和必要方式。文博與設計融合重組后,產生的不僅僅是一個個專題性強、行業水平專的文化產品項目,我們更在一次次的設計實踐中得出很多學科交叉的理論性成果。這里從文物建筑再利用現狀存在的問題入手,分析規劃設計在文物資源尤其是文物建筑利用時的重要性。再以設計學理論為出發點,分別從意識、形態上對文物建筑利用和規劃的長久干預性進行研討,旨在為文物建筑再利用提供更多思路與理論依據。
研究前,就本文的研究范圍加以限定。“文物建筑”概念意指依據《文物保護法》確定并被公布為文物的建筑。其范疇小于“歷史性建筑”“建筑遺產”,是歷史建筑中具有較高價值且應受到重點保護的建筑[1]。這些建筑保留至今,價值意義值得我們去深度挖掘。文物建筑勢必是在具備一定的完整性和較高的保護研究價值基礎上存在的。其在建筑設計概念內有多種體現形式,從空間角度講,存在地上、地下之分;從建造形式角度講,分矗立式建筑和洞穴式建筑;從體量上講,以內部空間組成形式可區分為包容式與開敞式。本研究緊扣文物建筑這一主題,主要以不可移動文物范疇,國家和各省(區、市)核準公布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中的古建筑、歷史紀念建筑、革命紀念建筑和近現代代表性建筑為研究對象。橋梁、堤壩、石窟石刻及建筑殘跡不在本研究范圍。
一、文物建筑再利用現狀及存在問題分析
1.文物建筑再利用科技含量低,缺乏與前沿技術的結合
文物保護與利用科技含量普遍偏低,多數文物保護停留在巡視、登記、發現情況上報等原始的保護方法上,缺乏新思路,與新技術新媒體相結合甚少;文物建筑再利用更是如此,各類事物處于被動接受,缺乏前瞻和創新的狀態。管理層級的上級給個指令、發個文件,文物建筑管理部門按照內容要求報一個數據,錄入一個信息。如果把一座文物建筑比作人的機體,這個機體的反應能力僅限于“膝跳反射”,“動能與活力”無從談起,更無法去匹配高速度的城市發展、經濟進步與社會文明程度。更有甚者會成為社會發展的腐朽之物,城市經濟發展的雞肋,喪失了文物建筑保護與再利用應發揮的意義與作用。
2.文物建筑再利用規劃思路受局限,缺乏與周邊資源的結合
被確定為文物的建筑,按照所在區域歸屬不同層級文物管理單位,按照其本身價值與保護需求,部分成立有專門保護管理機構,部分歸屬當地文管所直管。無論是文物建筑的直管機構,還是上級管理部門,在文物建筑再利用過程中,他們都其與周邊資源相結合發展考慮得甚少,處于封閉式發展狀態。試想一座單體文物建筑若處在市中心,寸土寸金之地,規劃其利用發展時不與周邊資源集合;或是處于偏遠郊縣的文物建筑不預留文物保護用地,不與當地文化旅游相聯系,閉門談發展,勢必走向沒落。
3.文物建筑再利用過程中忽視文物本體,不能兼顧式發展
文物建筑再利用,前提是保護。隨著我們利用意識的不斷增強,很多建筑文物保護單位以展館、主題文化公園等形式呈現在世人面前,并因此收獲了諸多贊譽、榮譽或是利益。此時極易將大量財力人力投入文化拓展與產業發展當中,容易忽視文物建筑本體的保護。對于建筑出現的小問題、小毛病置之不理,甚至習慣性地認為文物就應是這樣,“這樣的建筑更古樸滄桑,歲月感、文化氣息才更加濃烈”。但從文物保護視角來看,這恰恰是文物建筑應當進行修繕和保護的訊號,這些類似“蛋殼上縫隙”般的建筑損傷看似無大礙,如不及時修繕,會引起建筑主體建設材料的老化鈣化,因此變脆,縮短建筑壽命,文物本體安全系數大幅降低。所以一味地重視利用,不能與保護兼顧,終將使文物毀于疏忽與無知。另一種狀況是,忽視了建筑原本的藝術價值,不能內外兼修。只注重精雕細琢內部展覽、文化活動創意等,文物建筑本身的價值被忽略,出現文物建筑意義與利用項目文化內涵脫節現象,罔顧建筑外觀原本價值的解讀和傳承。
4.文物建筑再利用為博物館,存在盲從現象
文物建筑再利用為博物館已是常態,但利用過程中對博物館的概念理解有偏頗。常見某某故居被打造為某某博物館,對于該主題來講,無疑是首選。但該博物館能否滿足“博物”這一基本性能?取決于解決兩個基本問題,一是有沒有較大的場地干“博物”這件事,二是有沒有足夠的“物品”供觀眾博覽。如能客觀解決以上問題,還需要思考有多少空間能用來滿足參觀群眾的基本需求,例如游憩、文化衍生品售賣、盥洗、物品寄存、安檢等。若空間不能滿足,周邊資源無法配備,那么管理部門要重新定位這里是一個展室還是一個博物館。換言之,要對自身資源條件有客觀理性的認識,不要追風求大。
分析以上文物建筑利用現狀存在的問題,宏觀上可得出現階段我國文物建筑保護利用缺乏富有前瞻性、持久性的科學利用規劃。規劃設計學科的很多理念沒有能深入并融入文物事業發展中去,對于文物建筑的保護與利用,缺乏長效的理論指導;管理思路兩年一小變、三年一大改,管理者沒有形成站位高度與發展方向上的共識,影響文物保護利用的成果與社會價值意義的最大程度發揮。文物工作者通常做不可移動文物保護規劃很專業,編制完成后能夠以其為指導和參照,對文物本體進行科學修繕和日常維護。但利用部分的規劃往往編制內容與實際規劃設計相脫節。究其原因有兩方面因素:一方面是文物管理者依賴第三方力量做文物利用規劃,沒有提出自己對文物建筑利用的宏觀想法;另一方面是當地政府對文物保護事業的不重視。
文物管理者提不出有關利用方面的想法,主要是由于文博從業人員知識結構不完善,常年以保護死守為準則,眼界不夠開闊,利用意識沒有跟上,團隊缺乏懂得規劃設計理論的人才。作為了解文物的管理者,如能有大框架式的規劃意識或思路,僅提出點狀片狀想法就能非常有助于在對文物資源重組、進行規劃設計時,兩學科充分融合,創造出更多適于該文物保護和利用的形式。
二、文物建筑再利用建立規劃設計意識
文物建筑再利用,是讓其繼續發揮價值,為人類物質精神生活所用。文物建筑作為歷史文化資源彌足珍貴,再利用要依從建筑本身價值意義,展開文化服務和有關文化項目。隨著人們文化需要的日益增長,人們在追逐視聽新感受的過程中愈加重視事物文化價值與內涵的深層次品讀。此時,文物建筑以其大體量的客觀存在,成為大眾文娛生活的首選。如果把以文物建筑為核心的文化之旅比作“盛宴”,那么文物建筑再利用的過程好似“烹飪”。我們文物工作者應因地制宜,根據建筑本身狀況和周邊環境資源,制訂相應的利用開發方案,讓保護利用與經濟建設齊頭并進,這是區別于各種商業開發,體現文博專業技術水平和能力的務實性工作。
對文物建筑進行規劃設計前應對其進行全面專業考察評估,關注文物建筑保存狀況、場地條件、可用資源。
文物建筑保存狀況良好是再利用的基礎。再利用前,我們要客觀科學地評估建筑本體的堅固程度和建筑材料的鈣化情況,在對其有了全面客觀認識的基礎上,決策該文物建筑的再利用方式方法,是否通過加固修繕達到一定的接待能力,便于前來參觀學習的觀眾更深入地了解和感受。
文物建筑及其配套場地內是否有利于集合與疏散的空間環境,能否滿足現代消防需求,是決策再利用方式方法的重要因素,也是規劃設計開放場所游覽線路時重要的參照標準。適于對外開放的良好空間通常是開場與閉合有序,開放時利于參觀游覽,緊急情況時利于疏散,且參觀路線流暢,出入分離,避免人群流向沖突。
建筑內部及周邊配套設施是開放品質體現的關鍵。例如公共交通是否便利,自駕行駛道路情況,公共停車場地大小,衛生間配備情況等。更為重要的是,該建筑周邊要有供文物建筑再利用再度開發的空間。根據開放情況對以文物建筑為中心的整個園區進行有規劃的升級擴充,以滿足更多前來參觀觀眾的需求。
三、文物建筑再利用設計體現形式
1.以文物建筑內部空間為主要開放場所的設計利用——博物館
以內部空間為主要利用場所的文物建筑再利用方式便是傳統意義上的博物館。這種方式對建筑本身要求較高,除要具備較大的空間外,在建筑本體堅固程度上也有較嚴格的要求,滿足開放時段參觀群眾絡繹不絕地進入建筑內的需求。理想的博物館建筑內部80%的空間用于博覽文物藏品,另有20%的空間用于對外開放工作的各類配套,如安檢區、盥洗區、衛生間、文化產品售賣區、餐飲區等。且游覽線路設計滿足單程環線,不走回頭路,出入口分離。而現實中,文物建筑較少能以單座建筑為主體開展再利用,常因場地受限、路線不暢、建筑功能缺失而無法實現博物館的性能,因此多以展室形式存在。
2.以文物建筑外部形制為主要看點的規劃利用——主題公園
以文物建筑外部形制為主要看點的利用通常以公園的形式呈現。因為城市中的公園綠地規劃有服務半徑要求,在綠地系統規劃設計時往往優先以文物建筑、遺跡遺址所在位置為中心預留用地板塊,設計為城市綠地規劃中的“綠點”,這些點即成為城市公園、游園。因此以文物建筑所在位置為主題公園的情形較為常見。公園不僅遠離城市各類建設、交通干擾,有利于文物建筑保護,還能為建筑外觀觀賞提供較好的觀賞距離和較大范圍的配景,部分場地可設計絕佳的觀賞角度,打造如詩如畫的天際(輪廓)線。與博物館相同的地方是,作為對外開放場所,其服務功能齊全、游憩線路要清晰明了,配套設施要充裕。與博物館不盡相同的地方是,主題公園要以其主題為文化核心,打造公園屬性下的功能區域,如更多的游憩設施、兒童娛樂、步道、健身廣場等。
3.部分文物建筑本體與現代架構及院落的組合式利用
根據文物建筑保存狀況和開放利用的需要,我國很多旅游景區開發方式是以文物建筑為中心,或根據文獻記載,仿照主體留存建筑樣式和當時建筑風格還原歷史場景,以建筑群的形式展現給觀眾,補全功能上的缺失,創造更長更豐富的參觀路線,從而統籌安排游覽過程和時間。這種較常見的利用方法無論有無文獻依據,都容易被人接受、理解,因為中國古建筑原形通常是以院落形制出現的。當前國外的一些設計利用案例,將殘缺的文物建筑本體與現代建設工藝材料結合,創新設計拓展出大面積空間滿足室內環境的參觀群眾的需要。這類建筑與建筑間的相互呈啟,往往以院落形式出現。此時,觀眾注重的不是文物建筑本體,而是整個建筑群組成或圍合成的園區。與前兩者利用方式不同的地方主要體現在院落和建筑間相互的關聯。再利用的策劃設計要講究對景、照應,處理院內小型景觀構筑物與建筑主體的聯系至關重要,站在建筑內看建筑外是窗景,景觀節點和人的視點,極易成為焦點的地方是整個園區打造的重點。
四、文物建筑再利用規劃設計注重文物氣質打造
文物建筑再利用要尊重文物原有的氣質。策劃設計以文物建筑原本的性能作用為理論依據,在利用的方式方法上找到關聯、互通之處。開發過程中應正確定位文物建筑的價值與應體現的歷史氣質和氣節,絕不開發與文物建筑原有氣質相沖突的服務項目。再者,無論哪種形式的利用,均講究“內修外養”,不因注重內部展覽服務項目打造,忽視建筑本身價值體現,不要習慣性將建筑的外部損傷當作歷史感滄桑感的體現,及時進行建筑本體維護與修繕。
策劃設計要有前瞻性,預留長期發展空間,這是長效保持文物建筑氣質的根本。試想再好的利用方式,經不起時間和社會文化需要的更迭與演進,如若僅限于文物建筑本身占地資源去開發,遲早會被周邊經濟建設淹沒。與其不斷呼吁各級政府、社會各界重視文物保護與開發利用,不如自身早期重視起來。
設計建設過程注重文物建筑本體保護,在建筑內部作業,注重工程項目的可逆性,盡量避免對文物本體實施工程,以免造成損傷。
五、文物建筑再利用規劃設計管理建議
一部好的規劃設計通常能指導實踐15至20年,文物保護利用規劃亦是如此。文物建筑保護規劃和利用規劃一樣,不但要對當前文物本身面臨的問題提出有效的解決辦法,更要在今后的規劃期內指導文物保護和利用事業向更好的狀態發展。所以,在文物建筑利用規劃編制時,通常預留有項目的發展空間,在規劃實施到第幾年或者一期規劃取得成效后,啟動新板塊的利用方案,還有可能以三年、五年為一個時間段,分階段實現規劃目標。并且規劃中還應對利用方案投入使用后的管理提出原則性的建議。例如:文物建筑被利用后,人為因素導致的安全預警訊號都有哪些方面;科技監控監測和數據統計與文物保護安全方面的聯系;針對文物建筑對外開放的精細化管理;等等。文物保護的最終目的是利用,在我們確定了某一文物建筑的利用方式后,怎樣通過科學的管理讓保護與利用兩者有機結合起來,在保護和利用良性循環中發展下去,是不可移動文物保護利用規劃最終要協調的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