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第一次約會(huì)多數(shù)應(yīng)由男人付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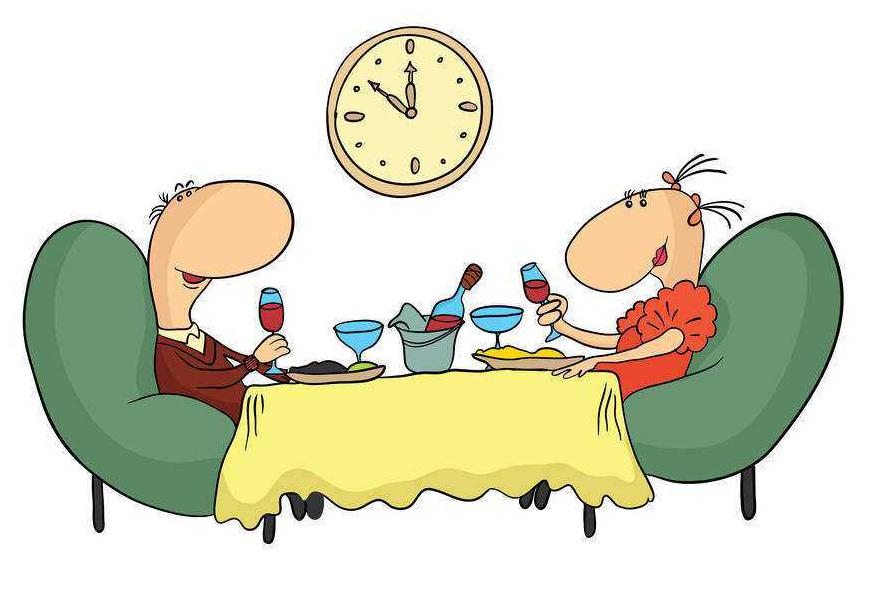

安妮·魯凱托

安妮認(rèn)為,社會(huì)結(jié)構(gòu)內(nèi)在的不平等意味著,AA 制并不公平
我剛開始和人約會(huì)的時(shí)候,媽媽就警告過我,這世上“沒有免費(fèi)喝一杯”這件事。
她接下來(lái)說(shuō)得更具體也更嚴(yán)重:“男人會(huì)覺得,你欠他點(diǎn)什么。”
我知道媽媽并不是故意想嚇我,但是她這一番話,令我每次結(jié)識(shí)一個(gè)新的人都會(huì)感到困擾。我花了好些時(shí)間,才擺脫掉那種男人請(qǐng)我喝了五塊錢的啤酒我就覺得自己有所義務(wù)的觀念——不過自此之后,我就再也沒回頭。
作為一個(gè)14歲就開始約會(huì)的人,我用了很多時(shí)間去想、去談如何找到一個(gè)好伴侶的問題,還有初次見面應(yīng)該關(guān)注哪些行為。
這年頭,找約會(huì)對(duì)象比任何時(shí)候都更容易,能想到的所有選擇、身份和背景的人,都有相應(yīng)的應(yīng)用程序和網(wǎng)絡(luò)分眾來(lái)滿足需求。
不過,第一次約會(huì)誰(shuí)付賬這件事,總是能引起一番激烈的討論。
我曾經(jīng)信奉的邏輯是,女人如果要和男人一樣被平等對(duì)待,我們就應(yīng)該付自己的部分,和約會(huì)對(duì)象AA制。為了確保不出現(xiàn)問題,我總是建議去負(fù)擔(dān)得起的約會(huì)場(chǎng)所——便宜而熱鬧的餐廳、社區(qū)酒吧、演唱會(huì)、公園等等。
大約在五年前,我的朋友和老師們讓我認(rèn)識(shí)了一些觀念,令我開始質(zhì)疑過去的做法。
我發(fā)現(xiàn)了,像格羅麗婭·金·沃特金斯(更為人所知的是筆名貝爾·胡克斯“Bell Hooks”)這樣的女性主義作家,令我開始思考,在現(xiàn)行的社會(huì)結(jié)構(gòu)當(dāng)中,誰(shuí)是獲益者。她和其他一些人令我開始想,權(quán)力在每一個(gè)層面上的運(yùn)作方式,包括最小的個(gè)人互動(dò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