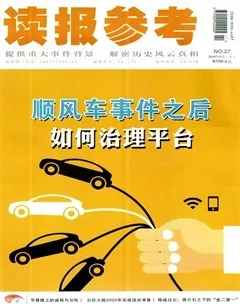陳誠日記:蔣介石之下的“坐二望一”
陳誠,字辭修,浙江青田人,保定軍校第八期炮兵科畢業,從黃埔軍校特別官佐到國民黨政權敗退臺灣后的“行政院長”“副總統”和“副總裁”,他的一生跌宕起伏,與中國國民黨和國民革命軍的歷史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陳誠有寫日記的習慣,日記時間起自1931年2月,止于1964年1月生病擱筆,前后持續34年。可惜因為種種原因,比如1936年日記毀于“西安事變”,造成年份殘缺不全,目前保存下來的僅有二十余年。雖然缺佚很多,但日記內容相當豐富,包括日常記事及個人思考、反省、自勉、與友人對話、備忘事項等等。2015年7月,臺北“國史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為了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陳誠去世50周年,合作出版了《陳誠先生日記》。
“現在政治腐敗,蔣先生實應負責”
1931年12月22日,陳誠在江西駐地像往常一樣給未婚妻譚祥寫信,所不同的是,這一次他剛剛提筆,眼角早已濕潤:“今天是我倆訂婚的七周月紀念,國仇友恨,豈堪回首。擇生兄(鄧演達)為革命而死,為中華民族而死,為世界弱者而死,死得其所矣!又復何憾?惟壯志未酬身先死,不能不為革命前途、中華民族前途、世界弱者前途痛哭耳。”
時間總是過得很快,遙想4年前,蔣介石下野,陳誠的師長職務亦被何應欽等人解除,后來多虧好友嚴重出手相助,總算得以擔任軍政廳副廳長、廳長。蔣介石再起,陳誠寫了一封長信,大膽建議總司令忍小忿以成大謀,“務望以總理(孫中山)之度量為度量,容納眾流,包含一切,庶幾革命早成,民生有托”。陳誠的耿直顯然給蔣介石留下了深刻印象。
1928年1月9日,蔣介石日記第一次出現陳誠,“惟陳辭修為有志之官長”。其后中原大戰,更是贊不絕口“各將領皆有憂色,惟陳誠之精神尚佳也”“辭修實一將才也,甚有希望”。憑借屢次蕩平地方軍閥的顯赫戰功,陳誠升任第18軍軍長,時年不過32歲。
1931年元月,宋美齡得知陳誠與原配不睦,早已沒有婚姻之實,好心介紹干女兒譚祥與陳誠認識。譚祥是已故國民政府主席譚延閩的三女兒,舉止落落大方,二人很快墜入愛河,并于5月22日在蔣、宋夫婦見證下完成訂婚。然而陳誠無法長久陪伴未婚妻,江西“剿共”戰事如火如荼,“中央軍將領加入前線,可鼓勵士氣,且促友軍將領之決心”。隨著步步深入江西蘇區,陳誠通過比較分析國共兩黨政策、作戰部署及軍隊素質的優劣,十分不滿統治階級的黑暗現實。蔣介石認為只要占領蘇區重鎮寧都,政治一定可以恢復生機。陳誠不以為然:“我以為政治之生機,絕非專恃軍事之勝利,應視政治之設施,是否為大多數人民謀利益為要也。”
說起招募夫役黑幕,陳誠更是深惡痛絕:“軍隊委托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轉托當地豪紳,層層相委,弊端百出。每雇一佚,地方照例應籌墊安家費二十元,官廳借此搜刮地方,豪紳借此從中漁利。”令人大跌眼鏡的是,陳誠甚至還在日記中毫不避諱地批評蔣介石:“現在政治腐敗,蔣先生實應負責。”
鄧演達是陳誠素來敬重的,亦師亦友的國民黨左派領導人,1930年從蘇聯回到上海組建“第三黨”反蔣,期間與陳誠有過一定聯系。1931年8月,鄧演達因叛徒告密被捕,陳誠懇請蔣介石“為國惜才,從寬處理”,但他深知兇多吉少,“因總座與擇生雖以政見之不同,而各走極端,而私感亦太惡劣也”。日記同時也顯現出陳誠左右為難的復雜情感,“擇生,吾友也;總司令,吾之上官。一情不可絕,一義不能忘”。得知鄧演達被判死刑,陳誠幾乎跪求蔣介石:“而今公不能報國,私未能拯友,淚眼山河,煢煢在疚。請飭朱主任(培德)速蒞江右主持。職決即日離職赴京待罪。”9月22日,陳誠確認鄧演達已經慘遭槍決,想到東三省不能抗日,摯友又為革命丟掉性命,悲憤手書“國仇友恨”。
不過,眼看與譚祥佳期漸近,陳誠發泄完心中不滿,自動調整心緒,“論私誼擇生不過系我友,而蔣先生實無異父兄”。畢竟,現實利益更能左右政治人物的最終站隊。
“天下不是父子二人的”
1960年代的臺灣身處美蘇冷戰、國共對峙的夾縫中,不論內外部都面臨各種沖擊。根據大陸時期制定的“憲法”,“總統”任期為6年,得連選連任一次,蔣介石到1960年任期屆滿。隨著改選日子臨近,開始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聲音,有人“敦請”蔣介石第三次參選“總統”;有人不僅反對蔣介石三連任,甚至希望國民黨能夠分化出一個反對黨。后者的代表人物是以“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為核心的“自由派”知識分子。
1958年5月26日,陳誠約胡適、陳雪屏、蔣經國便餐,談到“總統繼承問題”,胡適心直口快:“美國人總是說蔣總統扶植兒子,既扶植兒子,何以要兒子做特務頭子和政治部主任?我看蔣總統是培植陳副總統。”場面頓時變得尷尬起來,蔣經國不發一言,陳誠連忙打起圓場,“這幾年大家工作都辛苦”。平心而論,蔣介石確實力挺陳誠不遺余力,從“行政院長”“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主任”到“副總統”“副總裁”,陳誠已然成為臺灣島內“蔣氏之下第一人”。在接班人問題上,蔣介石也曾“假定兩年之內反攻尚未開始,則屆期國民代表大會人數不足無法召開時,只有移繳總統職權于副總統繼任”。
陳誠的心情很復雜,要說沒有半點“坐二望一”之心,恐怕誰也不會相信。12月24日,“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舉行午餐會,陳誠回憶該會成立之初,秘書請示他有什么指示,“我說我不與本會一千八百余人比聰明”。沒想到胡適立馬接口:“有聰明而不與別人比聰明,這是做領袖的智慧,我覺得陳主任委員說這句話有做總統的資格。”大庭廣眾,陳誠竟不反駁,當天的日記反而顯得躊躇滿志:“胡適認為這是最聰明的指示。”其實陳誠也摸不透蔣介石到底想不想連任,蔣一會兒考慮卸任之后以黨魁身份指導軍政,一會兒考慮以在野“革命領袖”來領導“反共”。
1959年1月,陳誠為避壽,邀約胡適、梅貽琦、蔣夢麟、王世杰同到臺灣中南部參觀訪問。參訪閑暇之時,眾人討論政治。不料外界不明真相,引發諸多猜測,比喻胡適等四人為“商山四皓”(西漢初年著名隱士),拉幫結派,旨在慫恿陳誠搶班奪權。蔣介石原本與胡適提倡的“自由主義”格格不入,此后遷怒、猜忌之心日重,“辭修不識大體,好弄手段,又為政客策士們所包圍利用,而彼自以為是政治家風度,且以反對本黨侮辱首領的無恥之徒反動敵人胡適密商政策,自愿受其控制之言行放肆無所顧忌,不勝憂悶無法自遣”。
1960年3月,“國民大會”通過相關修訂案,規定“總統”可連選連任,不受“憲法”約束。蔣介石后來找到陳誠,表示“商山四皓”之事讓他覺得此種復雜的局面陳誠無法處理,只有他能應付,所以他才決定要連任,不過以后仍會以“國家重任見托”。陳誠心生惶恐,“余告以對于政治原無興趣奉命,由從軍改為從政,徒增總統負累及憂慮,內心歉疚,實無以自解,常感如能死在總統以前是幸福”。在這之前,陳誠已經意識到蔣介石對自己的“猜疑”,多次傳話胡適,“你上次說的‘夠做總統資格’這句話,給我闖了禍,希望你下次不再闖禍”“總統連任之必要,不要害我”。如今舊事重提,比蔣介石小11歲的陳誠只得近乎詛咒一般表明心跡,日記又云:“此次談話深感總統對于余之期望似甚切,但對余之疑慮實太深。”
1965年3月5日,陳誠因患肝癌醫治無效去世,未能進入古稀,但也不算早逝。彌留之際,陳誠口述遺言:“希望同志們一心一德,在總裁領導之下,完成國民革命大業。不要消極,地不分東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全國軍民共此患難。黨存俱存,務求內部團結,前途大有可為。”據說,還有一句臨終遺言沒有正式錄入——“天下不是父子二人的”。
(摘自《國家人文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