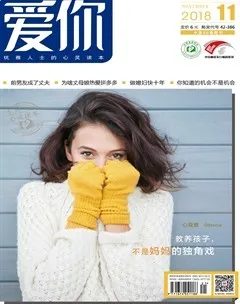為啥丈母娘熱愛拼多多
中國人的消費(fèi)在降級嗎?從數(shù)字上看,中國的居民消費(fèi)總額還在上升,但認(rèn)為消費(fèi)在降級的看法似乎正在成為主流,原因就是很多消費(fèi)者開始對那些質(zhì)量差、價格低的商品感興趣了。
我中學(xué)同學(xué)的丈母娘特別喜歡用所謂的消費(fèi)降級產(chǎn)品利器——拼多多。她在北京有一座集體公寓,她使用拼多多是為了購買那些低價的電器產(chǎn)品給她的房客用。這么做比她從舊貨市場買更便宜,而且質(zhì)量更有保證。她的資產(chǎn)狀況我有所了解,她憑借在北京的房產(chǎn)以及由此帶來的收入足以過上優(yōu)渥的生活。另外,她是老北京人,居住在北京二環(huán)和三環(huán)之間。
當(dāng)然了,一個樣本肯定不足以說明喜歡拼多多這種東西的人都是廉價公寓的房東,但這足以提示大家存在一種可能性——喜歡買廉價貨的人并不見得是窮人,而那些上班路上斜挎著LV包包的女孩也不見得是有錢人。
美國圣約瑟夫大學(xué)的邁克爾·所羅門教授舉了兩個例子來說明人們的消費(fèi)行為和自身財(cái)富水平的不平行性。一個是關(guān)于牧羊人的。這個居無定所的墨西哥人說房子不是一件值得上心的事,他只需要一個干燥的地方,但他要穿得很體面。“因?yàn)殒?zhèn)上的人會嘲笑衣服皺皺巴巴的人。”牧羊人回答。另一個是關(guān)于無家可歸者安德魯?shù)摹0驳卖斣瓉硎莻€餐館服務(wù)員,一天工作16個小時。有一天,他的妻子和女兒不辭而別。他瘋了,過著無家可歸的生活,直到接觸到了《街頭智者》—— 一份提供生活機(jī)會的報(bào)紙。安德魯通過賣報(bào),終于有錢去租房子、買食品,還買了一雙耐克鞋。
貧苦的牧羊人為什么重視穿著?瀕臨窘境的人為什么要買耐克鞋?沒有這種經(jīng)歷的人是說不清楚的。所以,一種糟糕的分析方法是:拿自己的消費(fèi)認(rèn)知去評估其他群體的消費(fèi)行為。
銷售組織形式更加靶向化,讓人們的很多消費(fèi)行為被分解了。比如,我同學(xué)的那個丈母娘,在十年前,她90%的購物行為都發(fā)生在家樂福的實(shí)體店鋪。而現(xiàn)在,她會在網(wǎng)易海淘給外孫女買貼了中產(chǎn)階級標(biāo)簽的嬰兒用品,在拼多多給她的房客買超便宜又不至于電死人的電視。如果評論者只注意到她在拼多多上購物的增量,就會以為她的消費(fèi)降級了。事實(shí)是,她以前沒有購買那些拼多多產(chǎn)品,是因?yàn)闆]有拼多多這種工具,而她當(dāng)時在二手市場和攤主討價還價的記錄又沒有引起消費(fèi)評論者的注意。(摘自《第一財(cái)經(jīng)周刊》2018年第33期 " 圖/劉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