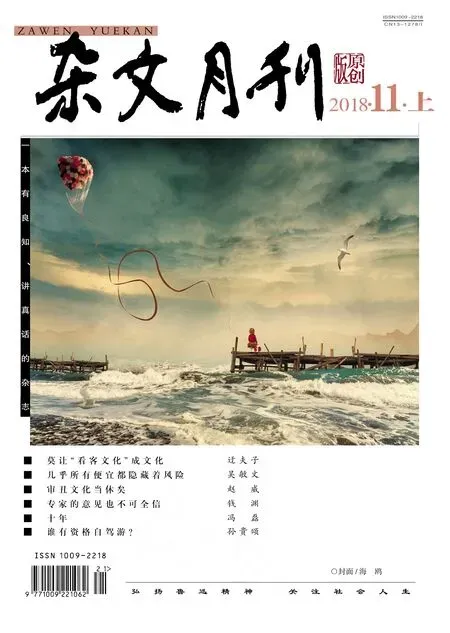聽書時代,重新發現評書
●禾 刀

9月11日下午3點30分,著名評書表演藝術家單田芳因病去世,享年84歲。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人,許多人是聽著單田芳的評書長大的。單田芳推出過《三俠五義》《白眉大俠》《隋唐演義》《水滸外傳》等許多優秀的評書,先后“錄制和播出100余部、共計15000余集廣播、電視評書作品,整理編著17套28種傳統評書文字書稿”。
算上2015年去世的袁闊成,“四大評書表演藝術家”已失去了“半壁江山”,在世的劉蘭芳、田連元均年事已高。在資本力量摧枯拉朽勢不可擋的當下,聽書APP如雨后春筍,一夜之間“千樹萬樹梨花開”。相比之下,有著古老傳承、曾經“霸播”數十年的評書藝術正陷入日漸式微的尷尬。
2008年6月,國務院發布了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評書名列其中。某種意義上,這也是評書生存困境的折射。
一門打著歷史烙印的古老藝術
評書是主要流行于華北、東北、西北的語言藝術,“四大評書表演藝術家”就全部出自東北。當然,這種藝術在華中華南也會有所存在,只不過表現形式略有差異,比如筆者這里的湖北大鼓就曾在本地紅極一時。
評書相傳起源于東周時期,近代評書公認的是起源于明末清初的柳敬亭。黃宗羲在《柳敬亭傳》中不僅指出“柳敬亭者,揚之泰州人,本姓曹”,還通過考證,道明兩宋時期說書藝人眾多。這表明在數千年的歷史中,評書藝術傳承脈絡清晰,綿延不息。
近年評書最開始是站在桌子后面,桌上放著折扇和醒木,表演者一襲長衫,“范兒”味十足。不知是否因為廣播評書的出現,切斷了傳統模式中表演者與觀眾之間的視覺聯系——表演形式被去繁化簡,桌子沒了,扇子沒了,長衫沒了,只是搞不懂,那個標志性的醒木怎會一同消失。
評書有著鮮明的藝術“套路”:開場有“定場詩”,介紹新角有“開臉兒”,講場景有“擺砌末”,此外還有“賦贊”“垛句”(串口)“關子”和“扣子”等相對固定的風格技巧。之所以說相對固定指的是表演形式,但內容并不統一。單田芳常用的“定場詩”就有“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五霸七雄鬧春秋,頃刻興亡過首。青史幾行名姓,北茫無數荒丘,前人撒種后人收,無非是龍爭虎斗”和“三尺龍泉萬卷書,上天生我意何如?不能治國安天下,妄稱男兒大丈夫”等。記得小時候聽湖北大鼓,開場白總會扯上一段與故事毫無關聯的奇聞逸事,大抵是為了活躍活躍氣氛,舒緩下緊張的神經吧。
與西方藝術大多源自宮廷明顯不同,評書誕生于市巷田野的社會中下層。這意味著,在知識極度稀缺的古代,評書表演者要想吸引識字不多的普通聽眾,必須通過極長的篇幅、復雜的情節、豐富的人物、接地氣的語言、鮮明的人物性格、出神入化的表演……使盡渾身解數,才能最大限度貼近聽眾。
只消看看袁闊成和單田芳兩大名家的幾個數據或可釋然。袁闊成的《三國演義》共365回長達182小時,人物超過400個。單田芳的《隋唐演義》216回長達86小時,刻畫人物也達180個,尤其是李元霸“長相丑陋,生性憨傻,但卻力大無窮”的形象,通過單田芳的表演早就深植人心。
評書本質是一門系統化的藝術
作為傳統說唱藝術,評書與相聲有許多相似之處,比如必須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加強繞口令這樣的訓練,確保表演時吐詞清楚;必須擅長運用抑揚頓挫的音調、豐富的臉部表情和肢體語言進行表演;必須對評書“開臉兒”“擺砌末”等套路滾瓜爛熟、易如反掌……但熟練掌握這些基本功還遠遠不夠。
傳統評書都有民間口頭文學特征,而口頭文學具有強烈的時代感,每個時代各有千秋。也就是說,評書并不是對歷史故事的簡單重復,而是將歷史故事與當下語言特點、受眾心理進行有機結合的結晶。打個簡單的比方,即便是近代評書“開山鼻祖”柳敬亭的作品放到今天,也只會令聽眾一頭霧水。
實際上,評書優劣不僅僅取決于表演水平,還取決于選材和創作,甚至還有生活體驗。以這一視角度之,評書當是一門“系統化”藝術。近代評書名家無一例外既是表演高手,同時也是創作的大家。
袁闊成把長篇小說《暴風驟雨》《烈火金剛》《林海雪原》《紅巖》《野火春風斗古城》《呂梁英雄傳》《保衛延安》等改編為評書。與此同時,他通過生活體驗和反復觀察,摸索出“氣、音、字、節、手、眼、身、法、步”等評書表演要點,至而形成了“漂、俏、快、脆”的鮮明表演風格。
單田芳既是評書的表演大戶,也是評書創作的名家。他創作的《白眉大俠》長達320回,后改編成電視連續劇,一時風靡全國。而前幾年播出的電視劇《隋唐演義》,正是改編自單田芳的評書作品。此外,單田芳還積極探索,將一些大案要案改編成評書,如《江洋大盜緝捕紀實》《九十年代大案要案偵破紀實》等。
評書亟待實現“三個對接”
一項調研數據顯示,在音頻技術和用戶需求的雙重刺激下,2018年國內有聲閱讀的市場規模或將逼近45億元。當當網CEO李國慶樂觀地估計,未來3年內聽書市場占紙書銷售額將超20%。
然而,在聽書市場日益火爆的今天,評書卻江河日下。袁闊成、單田芳等每一位老評書藝人的逝去,就像是評書界經歷的一次次塌方,且似乎看不到回暖的跡象。綜合現狀,竊以為,評書亟待實現“三個對接”。
首先是與現實的對接。雖然評書界也曾作過一些努力,但現實題材依然屈指可數,質量上也無法與傳統評書比肩。
其次是與新技術的對接。上世紀八十年代前,廣播的普及厚植了評書發展的沃土。時下火爆的APP軟件,理應成為評書發展的又一個春天,然而目前還看不出任何征兆。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技術并沒有厚此薄彼,根本原因或是評書人附于體制,安于現狀。
再者是與新內容的對接。時下聽書內容幾乎無所不包,像過去想都不敢想的哲學、心理學、經濟學、社會學等極為干澀的學科,均實現“一網打盡”。雖然魚龍混雜,有的還稍顯牽強,但聽書的強大“翻譯”能力,無疑大大壓低了普通大眾的“閱讀”門檻。也許有人認為這些學科不具備評書化的可能性,但這些書籍之所以能夠轉化為大眾愿意付費的聲音產品,主要原因便是對枯燥知識的故事化、邏輯化、口語化。
當然不應否認傳統評書的經典意義,但同時也應認識到,一味拘泥于傳統只會故步自封。在這方面,相聲的曲折經歷或可借鑒。前幾年相聲似乎頹相已現。就在坊間覺得相聲已一去不復返之時,郭德綱的德云社卻給茍延殘喘的相聲帶來一絲亮色。德云社的相聲既有傳統相聲的內核,同時也比傳統相聲更接地氣,還融入了小品的許多元素。他們不僅表演,還積極參與創作,所以作品常演常新,源源不斷。
古往今來,沒有一成不變的藝術。一些藝術之所以能夠穿越悠悠的歷史長河,綿延不息,就在于這些藝術能夠主動適應時代變化。一言以蔽之,與時俱進,藝術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