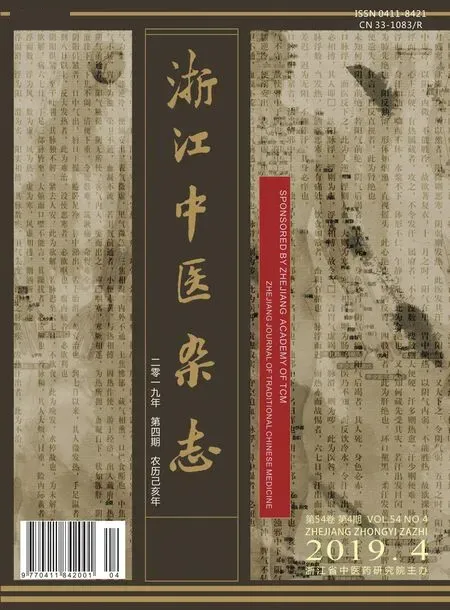淺析張介賓《景岳全書》婦人癥瘕辨治*
李萬雅 傅 萍 馬 嫻
1 浙江中醫藥大學 浙江 杭州 310053
2 浙江省杭州市中醫院 浙江 杭州 310007
張介賓,明代醫家,字惠卿,號景岳,會稽(今浙江紹興)人,其著作有《類經》《景岳全書》及《質疑錄》等。《景岳全書》成書于先生晚年,首選《內經》《難經》《傷寒》《金匱》之論,博采歷代醫家精義,并結合自身經驗,自成一家之書。首為《傳忠錄》三卷,統論陰陽、六氣及前人得失;次為《脈神章》三卷,載述診家要語;再次為《傷寒典》《雜證謨》《婦人規》《小兒則》《痘疹詮》《外科鈐》;又《本草正》,論述藥味約三百種;另載《新方八陣》《古方八陣》,別論補、和、寒、熱、固、因、攻、散等“八略”;此外,并輯婦人、小兒、痘疹、外科方四卷[1]817。其中《婦人歸·癥瘕》專篇對婦人癥瘕的辨治思想進行了全面系統地闡述,為臨床防治婦人癥瘕提供了有效的思路和方法。
1 理論源流
婦人癥瘕是指婦人下腹內結塊,或痛或脹的一種病證。其中癥指腹內結塊有形可查,固定不移,痛有定處;瘕指腹內結塊聚散無常,痛無定處。“瘕”的記載最早見于《黃帝內經》,有如《素問·骨空論》云:“任脈為病,男子內結七疝,女子帶下瘕聚。”[2]“癥”之名始見于漢代,《史記·扁鵲倉公列傳》云:“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特以診脈為名耳。”[3]而仲景《金匱要略·瘧病脈證并治》云:“病瘧……當如何?師曰:此結為癥瘕,名曰瘧母。急治之下,宜鱉甲煎丸。”[4]15,始創“癥瘕”病名。另《金匱要略·婦人妊娠病脈證并治》云:“婦人宿有癥病,經斷未及三月,而得漏下不止,胎動在臍上者,此為癥痼害……所以血不止者,其癥不去故也,當下其癥,桂枝茯苓丸主之。”[4]77,提出桂枝茯苓丸治療婦人癥病下血。巢元方在《諸病源候論》立專卷論癥瘕諸病,云:“癥瘕者,皆由寒溫不調,飲食不化,與臟氣相搏結所生也。其病不動者,直名為癥。若病雖有結瘕,而可推移者,名為瘕。瘕者,假也,謂虛假可動也……癥者,由寒溫失節,致臟腑之氣虛弱,而食飲不消,聚結在內,染漸生長。塊叚盤牢不移動者,是癥也,言其形狀,可征驗也;瘕病者,由寒溫不適,飲食不消,與臟氣相搏,積在腹內,結塊瘕痛,隨氣移動是也。”[5]同時在《積聚諸病》一卷中指出:“積聚痼結者……牢痼盤結者也。若久即成癥。”[5]揭示了癥乃積聚日久而成,而《景岳全書》中也明確指出癥瘕即為積聚的別名。陳無擇在《三因極一病證方論》中提出:“癥瘕積聚,隨氣血以分門……夫癥者,堅也,堅則難破;瘕者,假也,假物成形……婦人癥瘕,并屬血病,龍蛇魚鱉等,事皆出偶然。但飲食間,誤中之,留聚臟腑,假血而成。”[6]景岳先生之論亦以巢氏及陳氏說法為宗。
2 辨治特色
2.1 癥瘕之因機:張介賓《景岳全書》癥瘕篇對癥瘕的病因病機進行了深入概括。首先對癥、瘕二者進行辨別:癥即征者,成形而堅硬不移;瘕乃假者,無形則可聚可散;其次明確指出癥的病因病機不在血結就在食結,而氣滯則為瘕的病因病機,認為“總之非在氣分,則在血分”乃其主要因機。
2.2 分因論治:張介賓在《景岳全書》婦人歸篇中將婦人癥瘕分為血癥、食癥、氣瘕三方面內容,分別對其進行辨證論治。
2.2.1 血癥以調氣為先,活血相輔:張介賓認為血癥乃婦人特有,是瘀血留滯積聚形成,并將其病因概括為氣滯血瘀、氣虛血瘀兩種。而在血癥的治療上,張介賓提出調理氣機為先,輔以活血消癥,概因氣為血之帥,血為氣之母,氣行則血行,可助血癥消散。
氣滯血瘀則宜行氣活血以消癥,可依病情發展分別配伍而治,正所謂“但除之不以漸,則必有顛覆之害”[1]1377。若癥結初起、根盤未固,宜溫散行氣、養血活血,方用五物煎、決津煎,氣行則瘀血消而痛止;若瘀血日久,證見腹痛、腹脹者,當行氣活血止痛,宜用通瘀煎、失笑散等疏導,令氣血調達,氣通血活,而致和平[7];若病程更長、血癥堅硬時,如欲消之,當行氣破血,擬用三棱煎、萬病丸等方加減行氣消痞散結;若病情更甚者,瘀血不行,大便結閉,腹脹痛甚,當行氣攻下逐瘀,予桃仁承氣湯、桃仁煎等以攻下瘀結。
氣虛血瘀治當補氣扶正以祛邪消癥,正如“其有停雖甚而元氣困弱者,不可攻;病久而弱,積難搖動者,不可攻;凡此之類,皆當專固根本,以俟其漸磨漸愈,乃為良策”[1]1377。此類多為肝、脾、腎三臟為病,其中肝主藏血,而女子以肝為先天,脾主統血,乃氣血生化之源,為后天之本,腎主藏精,精血同源,乃先天之本。針對此類患者,張介賓偏重補虛養正之法,強調治宜從緩,顧護肝脾腎三臟,補氣溫陽,以固其根本,氣充則血行,血得溫則通,通則病自止,方如歸脾湯、暖肝煎、八味地黃丸之列。
2.2.2 食癥需斟酌虛實,權宜攻補:張介賓在食癥門中指出,食癥是因飲食不節、外感風寒、忿怒氣逆、勞倦等損傷脾胃,導致脾胃虛弱,運化失司,飲食積滯引起的。因此在治療時,當斟酌形體正氣虛實,而權宜攻補之法。形氣充實者,宜疏導為先,佐以補益脾胃;形氣虛弱者,當調補脾胃為先,佐以消導。正如張介賓于《景岳全書·雜證謨·積聚》云:“氣實者,非攻不能去……凡不堪攻擊,止宜消導漸磨者……而元氣未虧者,但當以行氣開滯等劑,融化而潛消之。”[8]若為前者,方擬五味異功散、溫胃飲等為宜,后者可予保和丸治之。
2.2.3 氣瘕當分清虛實,行氣為主:張介賓指出氣瘕屬無形,聚散無常,病在氣分,療瘕亦從氣出發,也因此著重強調“凡病在氣分,而無停蓄形積者,皆不可下”[1]1378。攻下之法雖可除有形之積,卻對無形之聚無效,甚則損傷正氣,為此他提出“散之之法,最有因通因塞之妙用”[1]1378。因通者重在破氣以行氣,氣實者以此法為佳;因塞者則須補氣以行氣,氣虛者惟此法可行。總之以散氣、行氣為治療大法,并根據正氣虛實,分別施以破氣、補氣之法。
其一氣實者當破氣行氣以散氣。若氣實氣壅而脹痛者,宜用排氣飲、四磨湯等行氣導滯,以止脹痛;若血中氣滯致瘀為痛者,宜調經飲等行氣化瘀;若夾濕、氣閉者,當佐以利濕通閉;若夾寒者,宜行氣為主,配伍溫里方藥,如丁香茯苓湯等;若兼熱者,行氣之外應佐以清熱之方藥,如抽薪飲等。其二氣虛者宜補氣扶正行氣以散氣。邪氣能聚而成瘕,乃因正氣不足,其趁虛侵入而為病。張介賓強調“人生以氣為主,得氣則生,失氣則死”[1]1378,著重點出了正氣的重要性。他亦應用臟腑辨證法靈活論治氣虛瘕聚者。心氣虛滯者,當圣愈湯等補氣養血;心脾氣虛不行者,參術湯主之,補氣健脾,養血寧心;肺氣虛者,當參附湯等大補肺氣,以助肺行五臟之治節;脾胃氣虛者,當以六君子湯健脾益胃,補氣行氣;氣血虧虛而滯而痛者,惟四物湯,甚則決津煎等大補氣血為宜;元氣虛滯不行者,當五福飲、十全大補湯補氣補血、培補元氣方可。
總之在癥瘕整體治療上,張介賓強調調氣為先。在分清虛實前提下,實者重在行氣、活血、溫通,虛者重視調補脾腎。從具體方藥來看,張介賓善用補氣養血、溫里行氣之方藥,少有攻下峻猛之劑。
3 結語
綜上所述,《景岳全書》分專篇論述婦人癥瘕,在《黃帝內經》《諸病源候論》等前人學術思想基礎上,進一步發掘創新,將婦人癥瘕分為血癥、食癥、氣瘕,系統論述其病因病機、理法方藥。提出辨治血癥當調氣為先、活血相輔;辨治食癥宜斟酌虛實、權宜攻補;辨治氣瘕需分清虛實、行氣為主。張介賓辨治癥瘕時善辨虛實,重在調氣,且多顧護脾腎,善用和法及補法,對后世婦人癥瘕的辨治有重要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