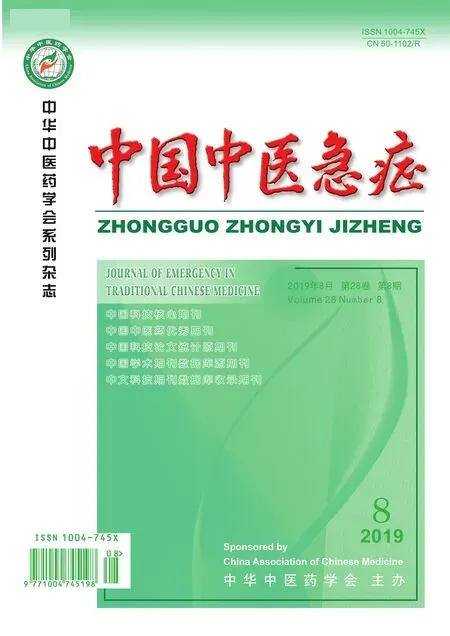中醫外治法治療哮喘的作用機制研究進展*
張媛媛 朱振剛 呂 英
(天津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天津 300193)
支氣管哮喘是由多種細胞如嗜酸性粒細胞、肥大細胞、氣道上皮細胞等和細胞組分參與的慢性氣道炎癥性疾病,其作用機制尚不完全清楚,現已發現的包括變態反應、炎癥作用、氣道高反應性和神經機制等。而中醫治療哮喘的歷史悠久,早在《黃帝內經》中就有對其的記載,被稱為“喘息”“喘鳴”等,并對其病因病機進行了描述。中醫外治法最早也是在《素問·至真要大論》中提及,曰“內者內治,外有外治”。發展至今中醫外治法包括針灸、敷貼、推拿等多種方法,治療范圍廣泛,既可以用于治療疾病又可以用于保健提高人體免疫力,并尤適用于“不肯服藥之人,不能服藥之人”。因其副作用小、療效突出、方便等優勢,被廣泛應用于臨床。但其確切的作用機制尚不明確,文中就中醫外治法對哮喘作用機制的研究加以概述。
1 中醫外治法對變態反應的影響
支氣管哮喘主要表現為Ⅰ型變態反應,即變應原進入特應癥患者體內后,巨噬細胞等形成抗原呈遞作用,刺激T淋巴細胞,產生白細胞介素(IL),并傳遞給B淋巴細胞合成高滴度的特異性IgE,隨后結合于肥大細胞和嗜堿性粒細胞表面的受體。當變應原再次進入體內,可與IgE交聯,合成并釋放多種活性介質,引起平滑肌收縮,炎癥細胞浸潤等表現[1]。
鐘耀東將90例老年咳嗽變異性哮喘(CVA)患者隨機分為對照組與觀察組各45例,對照組給予單純西藥治療,觀察組在此基礎上給予穴位貼敷大椎、肺俞、定喘天突等穴聯合中藥湯劑(炙麻黃10 g,杏仁10 g,炙枇杷葉10 g,桔梗10 g,荊芥10 g,防風10 g,川芎10 g,甘草10 g)內服治療,15 d后檢測兩組患者治療前后血清的IgA、IgG和IgE水平。結果提示穴位敷貼聯合中藥內服療法可使血清的免疫球蛋白IgA和IgG水平升高,IgE水平下降[2]。趙琦等將84例CVA患兒隨機分為對照組與觀察組各42例,對照組給予常規西藥治療聯合大椎、定喘、肺俞、膻中、命門、中府穴位敷貼治療,觀察組在此基礎上加用止敏平喘湯(茯苓15 g,炒白術15 g,黨參15 g,黃芪15 g,清半夏10 g,款冬花10 g,苦杏仁10 g,浙貝母10 g,桔梗10 g,麥冬10 g,紫蘇葉10 g,炙麻黃6 g,干姜6 g)口服。4周后觀察兩組患兒肺功能、血嗜酸性粒細胞(EOS)、免疫球蛋白IgE水平等均得到明顯改善[3]。宗凱將90例CVA患兒隨機分為3組各30例,西藥組給予單純西藥治療,穴位貼敷組在大椎、定喘、肺俞、化中、命門、天突、中府穴位上進行貼敷,中藥加穴位貼敷組,湯藥止敏平喘湯組成:炙麻黃10 g,清半夏10 g,款冬花10 g,苦杏仁10 g,茯苓15 g,炒白術15 g,黨參15 g,黃芪15 g,浙貝母10 g,枯梗10g,干姜10g,麥冬10g,紫蘇葉10g。每次200mL,每日2次,28 d后觀察得出中藥加穴位貼敷能明顯改善肺氣虧虛型CVA患兒的臨床癥狀,改善PEF水平、降低血IgA及EOS水平[4]。時寬通過觀察48例哮喘緩解期患者得出將白芥子、延胡索、生甘遂、細辛、麻黃等制成的膏藥貼敷于肺俞、心俞、膈俞、腎俞穴位可使哮喘患者血清IgE的水平下降,進一步證實穴位貼敷治療哮喘的療效是明確的和有效的,也許冬病夏治的原理之一正是通過降低哮喘患者冬季血液中IgE含量,抑制氣道高反應性的發生,達到控制哮喘復發的目的[5]。吳凌韜則通過對79例哮喘患者進行貼敷大椎、天突、肺俞、心俞、膈俞、脾俞、腎俞穴位觀察得出穴位貼敷后皮膚反應程度在一定程度上與治療支氣管哮喘的療效有關,皮膚發泡在改善血清IgE水平方面效果顯著[6]。王恩杰則對90例哮喘患兒進行隨機分組即治療組與對照組各45例,對照組給予西藥(孟魯司特鈉咀嚼片)治療,治療組在此基礎上聯合肺俞、膻中、定喘、足三里穴位埋線治療,可以看出治療組能夠改善患兒呼出氣一氧化氮、血清IgE及血EOS的水平并且治療后總有效率93.2%優于對照組83.7%[7]。張賽男對60例哮喘緩解期患者進行臨床觀察得出對定喘、肺俞、腎俞、脾俞、足三里等穴位進行埋線加常規西藥治療可使支氣管哮喘緩解期的患者血清IgE、IL-4水平下降,其總有效率93.1%明顯高于單純用西藥組79.3%[8]。沈毅韻對120例哮喘患兒進行隨機分組,對照組60例采用西藥霧化吸入治療,治療組60例在此基礎上加用清熱敷貼散(黃芩21 g,白芥子21 g,延胡索21 g,甘遂12 g,細辛12 g)和離子導入治療。結果顯示治療組可使熱性哮喘患兒的EOS及總IgE水平下降并在病情改善方面優于對照組[9]。許桂媚通過對120例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重疊綜合征(ACOS)患者臨床觀察,得出行肺俞、腎俞、定喘、大椎、天突、膻中穴冬病夏治敷貼療法可使ACOS患者血清IgE水平明顯降低[10]。何萍萍通過對62例CVA患者臨床療效觀察得出,針刺夾脊穴配合內服自擬中藥湯劑(炙麻黃6 g,紫蘇葉10 g,苦杏仁6 g,防風10 g,前胡12 g,枳殼12 g,桔梗 10 g,蟬蛻 6 g,五味子 10 g,紫菀 10 g,蜜百部10 g,桃仁10 g,橘絡6 g,白芍12 g,甘草6 g)治療可降低 CVA患者外周血EOS水平[11]。
2 中醫外治法對氣道炎癥的影響
哮喘的氣道炎癥是由Th2細胞活化并分泌多種細胞因子,從而進一步激活肥大細胞等多種炎癥細胞,并分泌多種炎性介質和細胞因子,最終可導致氣道高反應。楊照明等通過對100例哮喘患者進行隨機分組各50例,對照組給予常規西藥治療,治療組在此基礎上對雙側肺俞、風門、脾俞、腎俞行冬病夏治穴位貼敷治療。結果顯示治療組可抑制哮喘患者的外周血嗜酸性粒細胞浸潤并使IL-6及TNF-α水平得到改善,促進支氣管哮喘氣道炎癥的消退,緩解臨床癥狀,總有效率90.0%優于對照組74.0%[12]。朱曉婷則對120例CVA患者進行臨床觀察證明對定喘、膏肓、肺俞、豐隆、足三里穴位進行埋線聯合貼敷治療能夠使細胞因子hs-CRP、IL-6、TNF-α的水平降低[13]。王文亮對108例哮喘患兒分組進行臨床觀察,分別給予行清肝肺經,補肺脾腎經推拿療法聯合藥物霧化治療和單純藥物霧化治療,結果顯示前者IL-6、IL-33、IL-17等炎癥因子改善水平明顯優于后者[14]。舒毅芳通過對80例哮喘患兒進行臨床觀察,得出布地奈德霧化吸入聯合“冬病夏治”中藥穴位(心俞、肺俞、膈俞)貼敷療法可使哮喘患兒的血清炎性因子(hs-CRP、TNF-α、IL-6)的水平明顯降低[15]。王紅濤則通過對96例肺脾氣虛型哮喘患者進行臨床觀察得出使用敷穴化痰散(白芥子、甘遂、細辛、延胡索、冰片、生附子、半夏、膽礬、樟腦、花椒等)貼敷天突、肺俞、定喘、中府穴位與吸入沙美特羅聯合治療可使哮喘患者FEV1、PEF、FEV1/FVC升高,血清TGF-β1、IL-33水平降低[16]。薛明通過對90例CVA患兒進行實驗觀察可知對天突、膻中、膈俞、肺俞穴位進行貼敷聯合中醫辨證療法可使患兒血清IgA、IgM、IgG的水平升高,IgE水平下降[17]。方雪婷[18]、陳春燕[19]則均認為行清肝肺經補肺脾腎推拿療法可使小兒支氣管哮喘患者TLR1、TLR2和TLR4的水平上調,明顯改善哮喘患兒的臨床癥狀,增強其免疫功能。
3 中醫外治法對免疫功能的影響
哮喘發病主要免疫學機制是Th1/Th2免疫失衡,即Th1功能相對抑制,Th2功能相對亢進。周小梅通過對48例哮喘患者進行臨床觀察得出使用延胡索、白芥子、細辛、麻黃等藥物制成的膏藥對定喘、心俞、肺俞等穴位進行貼敷可使哮喘患者血清中IL-4和IFN-y水平下降,推測出其對哮喘的治療機制可能是通過調節Th2淋巴細胞分泌IL-4水平,進而調整體內Th1/Th2比值[20]。張艷梅對244例CVA患兒進行臨床觀察,證明對肺俞、膻中等穴位行埋線療法可明顯降低IgE介導的過敏反應,并且調節T細胞亞群,降低CD4/CD8比值[21]。張偉對哮喘模型小鼠行懸灸“肺俞”“脾俞”“腎俞”“膻中”療法,可使哮喘小鼠ROR-γt轉錄因子表達得到抑制,從而下調炎性反應因子IL-17含量,降低氣道內中性粒細胞水平[22]。蔡曉靜對466例哮喘患兒進行隨機分組,對照組與觀察組各233例。對照組采用常規西藥治療,治療組對肺俞、脾俞、心俞等穴位進行貼敷聯合中藥膏方(黃芪300 g,碧桃干300 g,茯苓300 g,麥冬300 g,黃精300 g,黨參200 g,白術200 g,熟地黃200 g,陳皮50 g,五味子50 g,紅棗50 g,山茱萸100 g,白芍100 g,枸杞子 100 g,女貞子100 g,蛤蚧1對)治療,2個月后觀察結果顯示治療組可使哮喘患兒IgE、EOS的水平下調,IgA、IgG的水平升高,臨床療效明顯優于對照組[23]。陳燕對90例哮喘患者進行臨床觀察,得出對肺俞、脾俞、腎俞、風門、豐隆行溫和灸配合口服固腎定喘丸(熟地黃、黑附片、牡丹皮、牛膝、補骨脂、砂仁、車前子、茯苓、益智仁、肉桂、山藥、澤瀉、金櫻子肉)能降低支氣管哮喘臨床緩解期患者的血清IgE含量,提高其免疫功能[24]。
T淋巴細胞是機體細胞免疫反應的主要參與者,在免疫應答中起重要的作用,已知T淋巴細胞表面分化抗原可將T淋巴細胞分為CD3+細胞、CD4+細胞、CD8+細胞亞群[25]。李巧香將120例CVA患兒隨機分為觀察組與對照組各60例,對照組采用西藥治療,觀察組采用益肺平喘湯(黃芪10 g,黨參9 g,白術9 g,炙麻黃6 g,射干6 g,杏仁6 g,紫菀12 g,款冬花12 g,炙枇杷葉10 g,紫蘇子6 g,蘆根6 g,沙參6 g,地龍6 g,甘草3 g)聯合天突、定喘、肺俞穴位貼敷治療可使CVA患兒EOS、ECP、IL-4及IL-5等炎癥因子水平顯著改善,并且CD4+、CD8+及CD4+/CD8+比值、IgE的水平也得到明顯改善[26]。陳小勇等將194例哮喘患者隨機分為兩組,研究組與對照組各97例,對照組采用沙美特羅替卡松粉吸入劑治療,研究組在此基礎上聯合對熱敏化腧穴艾灸治療,3個月后觀察得出對照組哮喘患者的FEV1、FEV1%、PEF、TLR2rpcp、CD4+T細胞、CD4+/CD8+T細胞、IgA、IgG、IgE、ACT得到明顯改善并且總有效率優于對照組[27]。馮良罡則對76例哮喘患者進行臨床觀察,得出冬病夏治穴位敷貼聯合中藥湯劑(炙麻黃10 g,白果10 g,杏仁10 g,黃芩10 g,防風10 g,半夏10 g,款冬花10 g,紫蘇子10 g,地龍10 g,陳皮10 g,蟬蛻10 g,黃芪30 g,桑白皮30 g,炒白術15 g,生甘草5 g等)治療可使哮喘患者CD3+T、CD4+T、CD4+/CD8+T值升高[28]。羅彩云對40例肺脾兩虛型變應性鼻炎—哮喘綜合征(CARAS)患者進行臨床觀察,認為補土通竅針灸治療即對上星、迎香(雙)、合谷(雙)、足三里(雙)、太淵行針得氣后留針并施以回旋灸法可使變應性鼻炎—哮喘綜合征(CARAS)患者的CD3+、CD4+水平上調[29]。孫雪松對118例哮喘患者進行隨機分組,對照組與治療組各59例。對照組采用常規西藥治療,治療組在此基礎上采用金貴腎氣丸隨癥加減聯合對大椎、肺俞、腎俞、脾俞、天突、定喘穴位貼敷治療,3個月后觀察治療組能提高CD4+的水平,改善CD4+與CD8+比值的失衡并在哮喘控制方面優于對照組[30]。莫珊對80例脾虛夾痰型CVA患兒進行實驗,可知培土生金穴位敷貼治療即發作期采用細辛、麻黃、干姜、姜半夏制成的膏貼貼于定喘、膻中、肺俞、天突穴位而緩解期則采用艾葉、附子、白芥子等制成的膏貼貼于脾俞、氣海、中脘、足三里穴位治療,可使CVA患兒的IgA、IgG、CD4+、CD4+/CD8+比值升高,IgE、CD8+值降低從而提升患兒細胞免疫及體液免疫功能[31]。
4 中醫外治法對神經機制的影響
呼吸系統不僅受自主神經支配,還受自主神經通路即非腎上腺素能非膽堿能神經(NANC)支配,其末梢釋放的遞質如P物質(SP)可興奮支氣管平滑肌而血管活性腸肽(VIP)則可抑制支氣管平滑肌,兩者比例失調可引起平滑肌收縮。李博林通過對50例肺氣虛型哮喘患者進行臨床實驗觀察證明,冬病夏治穴位貼敷治療即采用白芥子、細辛、甘遂、延胡索等藥物制成的膏藥貼于肺俞、膈俞、定喘、腎俞、足三里等穴位治療可使哮喘患者血清IgE、IFN-γ、IL-10含量降低,血清IgA、IgG、TNF-α含量升高,血漿SP含量明顯降低,VIP含量則升高。神經生長因子(NGF)參與了神經-內分泌-免疫網絡平衡機制的調節[32]。
5結語
中醫外治法治療哮喘的歷史悠久,發展至今包括針灸、敷貼、推拿等多種方法,因其具有“簡、便、廉、效”的優點現已被廣泛應用于臨床。從上文中可知中醫外治法治療哮喘的實驗研究取得了很大進展,但仍存在不足。中醫外治法對哮喘作用機制有著明顯的調節作用,并且是多方面的,例如文中穴位貼敷法對哮喘的免疫調節、神經機制、炎癥反應等都起到了一定的調節作用,能夠明顯改善哮喘患者的臨床癥狀,體現了中醫的整體觀念,但因沒有統一的選穴與用藥標準,不利于其進一步的推廣與應用。其次在臨床實驗研究中觀察組多采用中西醫結合療法,并不能完全體現中醫療法的作用機理,并且研究方式比較單一,研究范圍具有局限性。所以在以后的研究中應增加實驗的廣度與深度,即在中醫理論的指導下與現代科技手段相結合采用大樣本、多中心的方式更加深入地研究其作用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