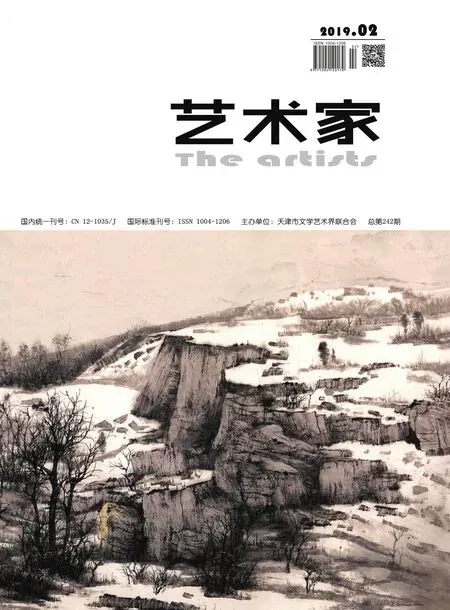誰扭曲了畫家的脊梁
□王進玉 知名青年學(xué)者、藝術(shù)評論家,中國文聯(lián)中國文藝評論家協(xié)會會員
一位畫家作品的好與差、水平的高與低,以及人格的優(yōu)與劣、情感的真與偽、責任的大與小等,都可以從他的作品中反映出來,明眼人一看便知,所以靠漫天的吹噓恐怕是“行而不遠”的,也終究會令人嗤之以鼻。因此作為畫家,務(wù)必要對自己的作品,以及自身的道德品行等負責。
此外,務(wù)必要堅守著一位文人畫家所具有的藝術(shù)良知,用富有生命感的真誠對待與孺子牛式的勤勞耕耘,肩負使命并充滿激情、不覺倦怠地進行著藝術(shù)的探索和實踐。其作品不僅要給我們呈現(xiàn)出當代繪畫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人文范本,而且還以一位藝術(shù)家剛直的脊梁,以及堅正的操守給我們深刻揭示了現(xiàn)實生活里真實存在的若干社會問題。
當然,當今畫壇的確有一批藝術(shù)家在認真且堅定地從事著具有自我良知與社會責任感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同時也誕生出了一批優(yōu)秀的畫作,比如高小華的《為什么》、邵增虎的《農(nóng)機專家之死》、毛旭輝的《水泥房間里的人體·幾種狀態(tài)》《剪刀》、張曉剛的《幽靈》系列,以及他的《黑色三部曲——惶恐、沉思與憂郁》,還有曾梵志的《協(xié)和三聯(lián)畫》《面具》系列,劉子建的《迷離錯置的空間》《宇宙中的紙船》《時間碎片》、張羽的《靈光》、邵戈的《城市垃圾》系列、王非的《關(guān)系》系列,等等。
但他們畢竟只是出淤泥而不染的蓮,蓮的數(shù)量卻總是有限。換句話說,當今太多的畫家已經(jīng)逐漸丟失掉了支撐個人責任感成長的脊梁,甚至出賣掉了具有獨立尊嚴的人格品行。他們的作品里也因此處處缺乏著清氣、靈氣和正氣,卻滿紙充斥著濁氣、死氣與俗氣。
其實這種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與很多因素有關(guān),其中較為重要的一點便是畫家創(chuàng)作態(tài)度的不純粹。也就是說,他們并不純粹地以藝術(shù)創(chuàng)作本身作為目的,而是隱含著對某些利益的追逐與擇取。我曾在一些場合上發(fā)表過,當代藝術(shù)的通病在于“俗”,在于“媚”,主要表現(xiàn)在“世俗”和“庸俗”,以及“媚政”和“媚眾”兩個方面。對于繪畫而言,“世俗”“庸俗”與“媚政”“媚眾”往往是糾纏在一起且很難分開的。特別在“官本位”思想極為濃重的中國,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當行政機構(gòu)主導(dǎo)藝術(shù)取向,當官場文化滲入藝術(shù)領(lǐng)域,眾多不良問題便開始層出不窮。
眾所周知,國家以及各地方畫院,包括美術(shù)家協(xié)會,雖然多是群眾性組織,但基本還是屬于官方或半官方的,其舉辦的各種比賽和展覽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了整個時期的畫風。這對于繪畫藝術(shù)的全面發(fā)展繁榮而言,無疑是一種隱性的羈絆和約束。此外,以職位頭銜論價格、論繪畫水平的高低,似乎誰占據(jù)領(lǐng)導(dǎo)崗位,誰的知名度高,那么誰就擁有絕對的話語權(quán)、評判權(quán)和決策權(quán),誰就備受追捧、備受禮贊、備受尊敬和寵護。這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現(xiàn)實,但這恰恰是現(xiàn)實的一種悲哀。殊不知藝術(shù)需要獨立和自由,不需要被“領(lǐng)導(dǎo)”、被“圈養(yǎng)”、被左右,應(yīng)該與政治,特別是與行政、與官場要保持一定的距離,而且職位的高低、頭銜的大小與繪畫水平的優(yōu)劣并沒有直接或必然的關(guān)系。相反,某些畫家正因為走上了所謂的領(lǐng)導(dǎo)崗位之后,其繪畫的水平卻不進反退,而且退步得相當厲害,其作品甚至到了慘不忍睹的程度。試問這該如何解釋呢?
而另一方面便是市場因素和大眾喜好嚴重影響了畫家的創(chuàng)作方向與創(chuàng)作品位。以市場為導(dǎo)向,跟著市場走、圍著市場轉(zhuǎn)、隨著市場變,目的就是希望能最大限度地討得市場和大眾的青睞、賣上好的價錢,并贏取現(xiàn)實利益。因此便出現(xiàn)了一大批畫家利用藝術(shù)價值、學(xué)術(shù)價值、收藏價值均不高,甚至特別劣質(zhì)的作品賺取著很高的經(jīng)濟效益。此類畫家不但沒有在藝術(shù)和精神領(lǐng)域為社會做出貢獻,反而破壞了整個書畫藝術(shù)市場的健康良性發(fā)展。
作為利益鏈條中的一分子、重要的參與者,他們已經(jīng)不再更多地關(guān)注如何提高繪畫技藝、如何傳承與弘揚國粹,以及如何探索創(chuàng)新,而是更多地開始關(guān)注起自己的身份、地位、名氣、周圍的圈子、作品的潤格等。試圖通過大量的宣傳包裝來成為社會上特別是官僚階層認可的“大名頭”、藝術(shù)市場認可的“搶手貨”。繪畫對于他們來說似乎已經(jīng)不再是一門純粹的藝術(shù),而是彰顯身份的一張名片,以及斂取錢財?shù)囊环N工具。為此他們可以不擇手段,可以大張旗鼓,甚至可以毫無顧忌地扭曲與丟掉象征道德與節(jié)操的人格脊梁,踢開和拋棄理應(yīng)具有的社會責任與藝術(shù)良知。
寫到這里不禁讓我想起一本書的名字:《這個世界會好嗎》。這本書是由著名學(xué)者梁漱溟先生著作的。梁先生是一位具有“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的新儒學(xué)大家,為國事、為安定、為團結(jié)、為文化、為教育等付出了畢生精力,一身正氣,學(xué)為人師,行為世范,令人敬仰。其實,不論是作家、思想家,還是書法家、畫家,都像教師、醫(yī)生、清潔工一樣,是一門職業(yè),所以也都要遵守其應(yīng)有的職業(yè)道德,也都要堅守其應(yīng)有的社會擔當。特別在國家日益昌盛的今天,畫家們更應(yīng)該有責任和義務(wù)沉浸在藝術(shù)的殿堂,弘揚經(jīng)典,追求卓越,而不是將自己打扮成道貌岸然的虛偽的藝術(shù)家,以及一身銅臭味兒的市儈之人,否則當今畫界真就好不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