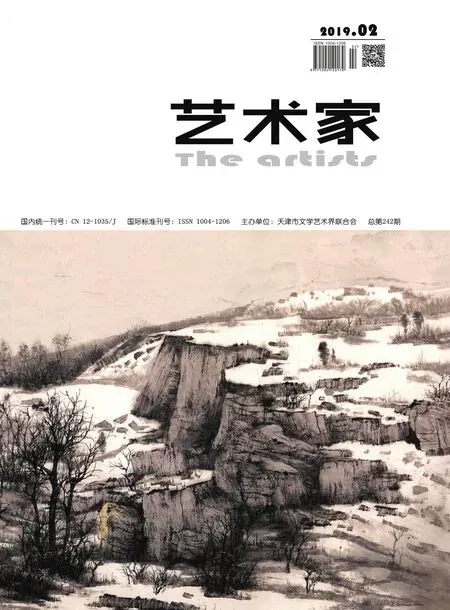阿富汗巴米揚石窟及主體塑像藝術特征研究
□勾若楠 西北大學
一、阿富汗巴米揚石窟
阿富汗曾是東西方宗教文化交匯的地方,這里誕生的巴米揚石窟藝術屬于世界文化遺產。其中,最著名的巴米揚大佛不僅是阿富汗歷史上的奇跡,也是古代世界的奇跡之一。阿富汗境內佛教石窟主要分布在三個地區,一是賈拉拉巴德附近喀布爾河沿岸的費爾哈納石窟,該石窟的建筑中心是山頂的覆缽塔,洞窟按位置分布為三區;二是阿富汗北部海巴克附近的塔夫特魯斯塔石窟;三是著名的巴米揚石窟。從總體上看,阿富汗境內的佛教石窟總數超過1000個,但絕大多數洞窟的形制簡單,洞內空間小,裝飾粗糙簡陋,雖說精美但數量很少。巴米揚石窟位于喀布爾約120公里的興都庫什山支脈賈加爾山南坡,沿腳下的巴米揚河谷自西向東分布。東西長約1300米的斷崖壁面上,大小洞窟總數750個左右,組成了以東西兩端大佛為主的布局。
二、巴米揚地區佛教石窟發展
(一)巴米揚佛教石窟藝術
巴米揚石窟位于絲綢之路上,曾是希臘、印度、波斯文化的交匯之地,也是古印度、古希臘、古中國三大文明的連接紐帶,其藝術品有多重文化因素,特別是涉及佛教向中國的傳播路線及所產生的影響。
巴米揚石窟分布概述,西南區位于弗拉蒂河谷兩岸(Foladi,也是巴米揚河的支流)現存50余窟龕,造像、覆缽塔等基本沒有了,但許多壁畫保存尚好。弗拉低第六窟有雙鴨連珠紋壁畫,是屬于伊朗風格的佛教藝術,與我國新疆克孜爾石窟區風格近似。
東南區位于喀拉拉客河谷(Kakrak,也是巴米揚河的支流)東岸與主區腳下的王城遺址相望,現存100余洞龕,除少量壁畫外,尚存一軀10余米高的立佛殘像,此像僅可辨認出身著通肩試袈裟,高肉發髻,面向略顯瘦長。它的形制與我國云岡石窟一期造像相似。
主區沿山壁又分東中西三段,范圍有1300米左右,洞窟700多個,有壁畫者約50個,巴米揚石窟最著名的東西大佛分別在主區的東西兩端。
(二)巴米揚石窟造像藝術特征
從技法上看,巴米揚地區大多數的造像是石像芯上包裹泥塑外形,這一手法因西大佛肢體上表層的泥塑剝落而意外明顯。它的優點是克服了泥塑難以制作超大造像的弱點,也將純石刻工程艱巨、不易把握整體造型的困難,變得相對自如且易操作些;而刻石為骨、塑泥為表的雕塑手法相結合,更在作品質感上體現出一種剛柔相濟的特殊韻味。
巴米揚的藝術特征可以用“文化上的多元性”來概括。正如日本學者樋口隆康在《巴米揚石窟》一書中所說:“若將巴米揚石窟構造和壁畫作一概括,就會發現許多要素混合在一起,當人引進印度笈多王朝式樣是毋庸置疑的,還有薩珊王朝,東羅馬拜占庭美術的影響和吐蕃,吐火羅斯坦的文化要素,這些要素渾然融合成一體就是巴米揚美術之實體。”
三、巴米揚大佛被毀事件及其原因分析
1996年,阿富汗塔利班掌握阿富汗政權。在此之前,兩尊大佛面部已經被鏟平,其中一座雙腿也被毀壞。塔利班政府并沒有在第一時間實施炸毀佛像計劃,而是宣布,巴米揚大佛是可以為當地帶來旅游收益的景觀,政府將對其予以保護。2001年后風云突變,塔利班忽然宣布將“銷毀一切異教偶像”,巴米揚大佛首當其沖。
第一,毀佛這種極端思想歸咎于原教旨極端主義為了凸顯他們所信奉的主義,暴力地推行自己的教義,并對異己宗教和文明存有極端的不寬容,投射到文化遺產之上也就產生了很多令人惋惜的破壞文化藝術的悲劇。第二,原教旨極端分子對時代早于本宗教或“圣訓”誕生的文化和文明遺產有本能的仇視感,巴米揚大佛的誕生早于伊斯蘭教200年左右,亞述文化則更古老,這種仇恨在很大程度上是原教旨極端分子內心的不安、恐懼的表現。第三,原教旨極端分子內部派系林立、魚龍混雜,希望借這種非常手段立威。
文化遺產本就非常脆弱,即使在沒有沖突的條件下,也很難保護,如要避免它們受到環境污染、工業化發展的影響等。在沒有正規政府,充滿沖突的局勢下,保護這些文化遺產更是難上加難。特別是在阿富汗目前局勢下,現有的軍事力量主要集中在對抗極端組織上,減少民眾受到的傷害,還沒有部門或組織采取任何長久有效、可持續的措施去保護這些文化遺產,把文明的足跡留給后人。
巴米揚是一個曾經被人們忽略的地方,一個現在想起就令人心情緊張的地方,一個將來人們會扼腕相惜,無比哀傷的地方……巴米揚的慘痛歷史和寧靜現狀形成強烈的反差,猶如銘刻在這個國際心臟的一道美麗傷疤,時刻提醒著世人和解與包容的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