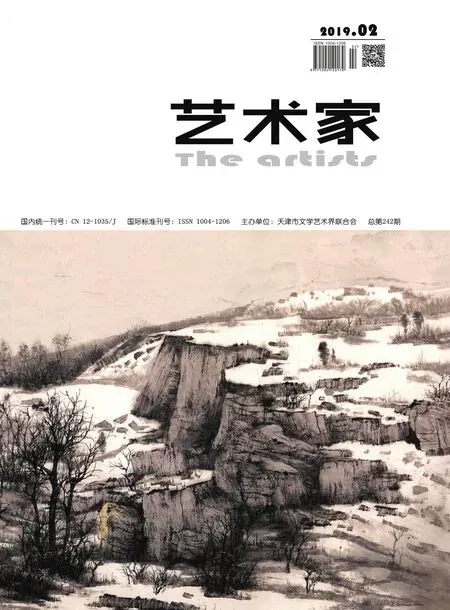當代藝術是一種思考方式
□張 琪 魯迅美術學院
當代藝術更加注重表現生活,更多地反映了人類與生存環境之間的關系,具有人文主義和思辨的特質。同時,當代藝術更具有創新意識,它改變了人們的思維方式和審美眼光。當代藝術所提出的問題在潛移默化地引導著人們去發現和思考。
一、再現與表現
一本書中提到,“藝術并不是對真實世界的復制。一種毫無意義的東西便已足夠”。這立刻讓我想到了杜尚的作品。他曾把一個自行車輪當作一件藝術品,還曾把小便池送去參加展覽,這些日常生活中的用品究竟具有什么樣的審美呢?為什么能夠被他看作是藝術。我們可以試想,當美術館里擺放著各種對現實世界的模仿和抄襲時,任何一個人都能夠看出個所以然來。可是從杜尚開始,藝術開始變得沒那么簡單了,藝術不再是一些能夠進入美術館讓人走走停停去附庸風雅的東西了,欣賞藝術也不再是那么的簡單事了。你看到了你看到的,然后呢?藝術的功能更多的是引發人的思考。其實對藝術的理解真的要一層一層地剝開,一層一層地去體會。最開始我所接觸的“藝術”是媽媽給我畫出來的“小鴨子”和“一個老丁頭”。那時候的繪畫對我來說可能就像任何一個玩具一樣讓我覺得有意思。到了后來我開始學習繪畫,人們看到后就會說,“好好畫啊,以后當個大藝術家!”那時候,我的眼界也只停留在畫素描靜物上,之后繼續畫畫是為了要考大學。我最迷茫的時候是我剛剛上大一的那年,我通過努力畫畫終于考上了大學,并在大學開學后繼續畫畫。那時候有人會問我美術學院上課都學什么,答案當然是畫畫。那個時候我覺得自己離藝術很近了,但為什么還是看不清藝術的本質呢?現在想想,可能因為當時的我只是在漫無目的地模仿,頭腦的空曠是再多的手頭功夫都填補不了的。慢慢我才能夠理解這句話,“藝術并不是對真實世界的反復。一種毫無意義的東西已足夠”。
那么,藝術的語言是否可以相互轉換呢?其實,之前我們所表達的一些語言在真實的轉換中是不符合實際的。“再現”并非是像鏡子一樣的物理過程,而是一種相對可變的符號關系。通常,我們在生活中對于“再現”和“表現”并沒有很明確地去區分,例如詩人盧綸寫的一首詩,“月黑雁飛高,單于夜遁逃。欲將輕騎逐,大雪滿弓刀。”其再現的到底是戰士在嚴寒中艱苦戰斗的場面還是邊塞凜冽酷寒的景象呢?如若要做到嚴謹,第一步就是要消除一個普遍的混淆概念,即“再現”是對于對象或者是事件的再現,而“表現”則是對于情感狀態或其他特征的一種表現。所以在這里,我們看到的是兩個范圍內的不同事物。
二、“我注六經”的觀看方式
縱觀藝術史的發展歷程,早期的藝術只是簡單地描繪自然,更多的是表現藝術家的直觀感受,而觀眾很直接地就能夠從作品當中看到藝術家想要表達的東西。這時候的藝術創作就是“六經注我”,“我”處于被動狀態,被動地吸收一切信息。然而藝術發展到后來的極簡主義時,就變成“我注六經”的狀態了。因為極簡主義往往是關注材料本身的屬性,是去掉了藝術家的個人痕跡后來表達材質和藝術的本質思維,觀眾如果只是單純地看藝術品是什么也看不到的。這時候的藝術是參與了思維的,需要觀眾去解讀藝術。由于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審美經驗和生活經歷,因此產生了對作品的不同解讀,面對藝術作品更多的是需要頭腦的思考,不是被動的吸收,而是主動思考的過程。馮友蘭先生在談“歷史”時提到,一種是客觀發生的歷史,一種是人寫的歷史,而人寫的歷史就是“我注六經”。所以,欣賞當代藝術作品的人都是要主動去“注六經”的。
說到當代藝術時,我們不得不提西方文化對中國當代藝術的巨大影響。對于當代藝術,更多時候我在想的是:我們的當代藝術究竟是西方當代藝術還是中國當代藝術,還是二者相互融合的產物?然而,中國的傳統藝術從表面上看起來很難和西方藝術融合到一起。時至今日,我們一說到當代藝術,更多時候的第一反應是西方的一些文化思潮或者作品。身在中國,我們如何找到本土的當代文化語言,或者如何從我國的傳統文化中尋找一些延續,讓當代藝術能與我們自己的文化傳統更好地結合呢?所以,在思考當代藝術問題時,我更加注重的是如何在吸收當代藝術思潮的同時在本民族的文化中找到一些契合點,這也是我最近創作的一個思想核心。當我們在接受西方當代藝術的同時應該知道東西方在思考方式上的差異,而當代藝術與傳統文化之間其實是可以有一個發展、延續的關系的。
對于當代藝術的學習,我的收獲不僅在于內容,更多的是一種思考方式和一種心態。要說對于當代藝術的認識,其實我們很多時候應該以一種追其所源的方式去看待問題,重要的不是你能做成什么樣子,而是你所做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