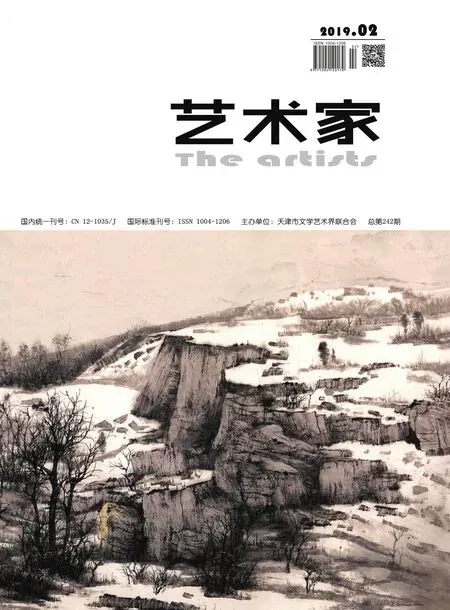論藝術創作中的模式化傾向
□張 娟 魯迅美術學院
藝術的形式感變化造成的模式化傾向是每位藝術創作者都不可回避的,但最終我們將走向藝術的再創造,走向內心。
一、什么是模式化
我們平時所認為的模式化是對已知事物的應用,即在已經存在的系統模式中進行加工,從而創造出一種新的組織形式。這種新的組織形式可以是之前模式的替代品,也可以與原本的模式共同使用,相互依賴。雷德侯在《萬物》中介紹漢字的模式化時就談到,漢字的五萬個單字全部是通過選擇并組合少數的模件構成的,而這些模件則出自相對而言并不算龐雜的兩百多個偏旁部首。當然,人們對這種模式化思維的創新和沿用存在于它的實用性本身,而藝術作品是不具有實用價值的。
在藝術史的發展中,藝術品從純粹的欣賞性上升到了精神領域,再上升到哲學范疇,藝術模式化更多的來源于它對外界產生的感覺因素。比如二千年前的音樂為什么我們現在還會喜歡聽,兩千年前的繪畫為什么我們現在還能夠去欣賞并學習,這是由于音樂、繪畫甚至舞蹈等藝術形式會產生出一種共性。音樂可以衍生出古典音樂、爵士樂、流行音樂、搖滾樂等等,而不管出現多少種新的類型,它都有一個情感的支撐點。藝術作品也是一樣,藝術家的創造力并不在于智商水平的高低,更多的是來源于對原有能源地融合和轉換。而原有能源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則不斷給藝術家提供新的創造動力,從而不斷地使其創造出多種藝術形式。人類的情感也許不會枯竭,可是這種不斷解構和創造的形式感本身會不會越來越模式化呢?
二、藝術形式感的多樣性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后,藝術開始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除了欣賞價值,它還產生了對戰爭的反思,對人性的批判,把藝術上升到了一種精神領域,藝術形式的更替更加迅速。立體主義出現之后,解構主義隨之而來,接著是抽象主義,超現實主義、達達主義、裝置藝術等等。而藝術形式的迅速更替使藝術創作達到了頂峰,原有能源的多樣化使藝術家很難再從這些復雜性當中尋找出新的創造動力,因為這些藝術主義不是貿然產生的,除了受到時代和生活環境的影響,其還存在一種對已有模型的重新排列和解構。
我們來看塞尚的《靜物》,在這幅作品中塞尚摒棄了“直線透視”。我們發現畫面上的桌子、水果、盤子都向前傾斜,作者用加深物體輪廓線的畫法來達到畫面的平衡感,這種方式完全不符合傳統式的素描法。再加上畫面對鮮艷顏色的使用,這使畫面既具有秩序感又同樣不失深度。荷蘭藝術家蒙德里安的作品則完全是用直線和純粹的色塊組成的,除了使作品更加簡潔化之外,他還試圖利用神秘主義者的思想去反映與揭露宇宙不停運動的客觀存在,他用哲學家的思想完美地闡釋了自己用簡單要素構成作品的意圖。
我們都知道,當一個藝術家把作品上升到了精神和哲學的范疇之后,這種新的形式就不能簡單地用作品的構成和排列去解釋了。“當實際的紙上繪畫真的不求形似了,同旁的繪畫理論就從旁推波助瀾起來。”那么,這種越來越簡化的模式化本身便很難再尋找新的創造動力。當各種各樣的藝術形式擺在人們面前時,藝術家的選擇就會變得越來越少,其在新領域的摸索也會變得越來越緩慢。
三、藝術的模式化傾向對藝術創作產生的影響
藝術各種形式化的發展帶來的不僅是創造力匱乏的問題,還出現了一系列模仿和抄襲藝術作品的現象。模仿是每一個個體走向群體的初步階段,只要個體之間產生交流,模仿就會出現,簡單個體通過對復雜個體的模仿和學習會變得更加成熟,因此模仿是個體在成長過程中必不可少的環節。但是,模仿也分低級和高級,對原有藝術品形式上的照搬屬于最低級的模仿,而對原有藝術作品內容和主題的照抄、照搬就等同于抄襲。在當代藝術中,這種現象特別常見,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與藝術越來越模式化有關。當然,還是有很多藝術家致力于藝術創新,他們喜歡去探索新的東西,越來越多地去尋找藝術更深層面的變化:人類與世界的精神狀態、藝術與哲學則成了藝術創作的主題。
藝術的模式化可能會造成藝術的終結,但不會讓藝術滅亡。純粹的藝術形式感看上去似乎是已經固定的,而關于生活和文化的變化則是在行為中不斷產生的。在藝術模式化面前,我們應該讓自身變得更加敏銳,提升個人的眼界,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著力于藝術的再創作。模仿也許是我們現在面對藝術創作必然經歷的過程,但真正的藝術創作必定發自于內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