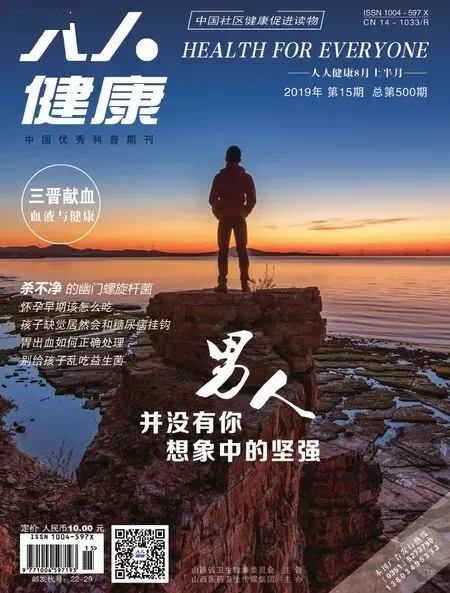乳腺癌細胞因子微環境的研究進展
張啟迪 趙心宇 魏霞
(三峽大學醫學院組織胚胎學教研室)
乳腺癌是全球女性發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惡性腫瘤,隨著對乳腺癌的研究深入,發現乳腺癌微環境中除細胞成分外,還有許多非細胞成分能夠與乳腺腫瘤細胞發生相互作用,進而產生一系列有利于癌細胞生存和生長的反應。本文重點對免疫炎性因子進行了討論,對它們通過各種信號通路,近距離或遠程促進腫瘤細胞的增殖和侵襲,調控腫瘤生長活躍狀態的相關研究進展進行了綜述。
1 淋巴因子
白細胞介素35(IL-35)是一種有效的免疫抑制細胞因子,由Epstein-Barr病毒誘導的基因3亞基和p35亞基組成。IL-35主要由調節性T細胞和調節性B細胞產生,在預防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最近的研究中,科學家們證明乳腺癌細胞(Breast cancer cell,BCC)也表達和分泌IL-35,且BCC中IL-35水平升高與患者預后不良密切相關,是乳腺癌獨立的不良預后因素。后續研究發現,BCC來源的IL-35抑制傳統T(Conventional T,Tconv)細胞增殖,并進一步誘導抑制的Tconv細轉變為IL-35誘導的調節性T(Induced regulatory T,iTr35)細胞。此外,乳腺癌細胞來源的IL-35增加了抑制性細胞因子IL-10的分泌,并且明顯減少Th-1型細胞IFN-γ的分泌和Tconv細胞Th17型IL-17的分泌。同時,BCC上清液處理后,Tconv細胞表面抑制受體CD73的表達也升高。從機制上講,BCC來源的IL-35耗盡了Tconv細胞,并通過激活轉錄因子STAT1/STAT3誘導iTr35[1]。因此,BCC來源的IL-35通過抑制腫瘤浸潤Tconv細胞的增殖和誘導腫瘤微環境中的iTr35細胞,促進腫瘤進展。因此,可以考慮針對IL-35的傳導通路設計相應的阻斷藥物,來治療乳腺癌。
Siyang Wen發現,白介素-32(IL-32)與整合素-β3(由ITGB3編碼,整合素家族成員之一)相互作用,介導CAF與乳腺癌細胞的相互作用,在CAF誘導乳腺腫瘤侵襲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IL-32是一種含有RGD基序的細胞因子,在CAF中大量表達。乳腺癌細胞在上皮間充質轉化期間,上調整合素β3。CAF來源的IL-32通過RGD基序特異性結合整合素β3,從而激活乳腺癌細胞內下游p38 MAPK信號。這一信號增強了EMT標志物(纖維連接蛋白、神經鈣黏素和波形蛋白)的表達,促進了腫瘤細胞的侵襲。抑制IL-32活性,調低IL-32或整合素β3導致特定的p38 MAPK信號在腫瘤細胞失活。阻斷p38 MAPK通路也可降低IL-32誘導的EMT標志物表達和乳腺癌細胞的侵襲、轉移[2]。這些數據表明,CAF分泌的IL-32通過整合素β3的p38 MAPK信號,促進乳腺癌細胞入侵和轉移。
在試圖找出三陰性乳腺癌(Triple negative breast cancer,TNBC)的微環境時,研究者發現了IL-22的內源性表達[3]。他們發現,作為IL-22主要來源的Th22細胞主要存在于感染部位或一系列炎癥性疾病中。Th22細胞分別在正常組織、癌旁組織和腫瘤組織中的逐漸增多[4]。在體外,IL-22促進TNBC細胞遷移,誘導對紫杉醇的耐藥。重要的是,IL-22暴露于TNBC細胞,導致jakstat3/MAPKs/AKT信號通路激活[3]。IL-22可能促進TNBC的發展。針對IL-22作用通路的干預有可能為TNBC的治療開辟新的方法。
已知多種炎癥因子可通過誘導巨噬細胞的產生,促進乳腺癌的發展。在小鼠模型中,白介素-1B(Identified interleukin 1B,IL-1B)及其受體(Identified interleukin 1 receptor,IL-1R1)在轉移到骨的乳腺癌細胞中比未轉移到骨的細胞中均有所上調。科學家已經通過臨床許可的拮抗劑Anakinra阻斷IL-1R信號通路來研究IL-1的功能作用。Anakinra可顯著降低MDA-MB-231-IV腫瘤在骨中的生長,從6.50+/3.00mm2(安慰劑)降低到2.56+/-1.07mm2(治療)和 0.63+/-0.18mm2(預防)。Anakinra還將發生骨轉移的小鼠數量從90%(安慰劑)減少到40%(治療)和10%(預防)。Anakinra不增加腫瘤細胞的凋亡,但減少腫瘤細胞的增殖和血管生成,對腫瘤環境有顯著影響,降低骨周轉率標志物IL-1B和TNF-α[5]。所以,IL-1B對乳腺腫瘤的骨轉移有一定的正向作用。通過Anakinra阻斷腫瘤細胞的IL-1B受體,或許可以達到治療和預防乳腺癌骨轉移的目的。
2 胰島素樣生長因子受體
Li Y之前證明了胰島素樣生長因子受體(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1 receptor,IGF-1R)在三陰性乳腺癌的Wnt1小鼠模型中可以作為腫瘤和轉移抑制因子[5]。IGF-1R的降低如何影響TNBC表型的機制尚不清楚。Alison E.Obr’分析了乳腺癌國際聯盟的分子分類數據集,發現低IGF-1R與降低了的患者總生存率之間存在相關性。即使在激素受體陽性的乳腺癌中,IGF-1R的表達也與患者生存率呈負相關,這表明IGF-1R低的患者總生存率的下降并不僅僅是由于TNBC中IGF-1R低表達所致。在小鼠或人腫瘤上皮細胞中抑制IGF-1R可增加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的產生并激活內質網應激反應。IGF-1R受抑制的腫瘤上皮細胞,IL-6和CCL-2表達升高,這一情況可以經ROS清除后逆轉。此外,Wnt1/dnIGF-1R原發性腫瘤顯示出促腫瘤免疫的表型。增加了的CCL-2促進CD11b+單核細胞流入原發腫瘤,也增加了基質金屬蛋白酶MMP-2、MMP-3和MMP-9的表達。腫瘤基質中MMP活性增加與基質重塑和膠原沉積增強有關。進一步分析代謝數據集發現,低IGF-1R患者IL-6、CCL-2、MMP-9表達增加,與他們小鼠腫瘤模型和人類乳腺癌細胞系數據一致[6]。IGF-1R功能的降低會促進細胞因子的產生和細胞應激,從而通過免疫細胞的浸潤和基質的重塑促使形成侵襲性腫瘤微環境。
3 表皮生長因子
表皮生長因子(Epidermal growth factor,EGF)誘導了EGFR、ERK、AKT和NF-kB信號通路的激活,抑制MMP-2和MMP-9的分泌,從而促進乳腺癌細胞增殖和趨化。這一結論可以用表皮生長因子的抑制劑大麻二酚(Cannabidiol,CBD)來佐證,CBD是一種非精神類大麻素化合物。Mohamad Elbaz分析了CBD對包括TNBC亞型在內的高侵襲性乳腺癌細胞系的抗腫瘤活性,展示CBD能顯著抑制表皮生長因子誘導的乳腺癌細胞增殖和趨化。此外,研究者還證明,CBD在不同的小鼠模型系統中均能抑制腫瘤的生長和轉移[7]。他們的研究表明,EGF可通過EGF/EGFR信號通路和調節腫瘤微環境,促進乳腺癌的生長和轉移。
4 結論
本文從細胞因子這個方面來論述非細胞微環境對于乳腺癌發生發展的影響。腫瘤微環境的構成和變化是復雜的,僅僅通過這些分析很難非常全面的說明乳腺癌的局部非細胞微環境。例如,關于Tcony cell和iTr35如何促進乳腺癌的發生機制在現有文獻中并未闡述清楚,毋庸置疑,充分了解乳腺癌的微環境,了解構成這些微環境的重要要素,可以為今后乳腺癌的研究和臨床治療提供有價值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