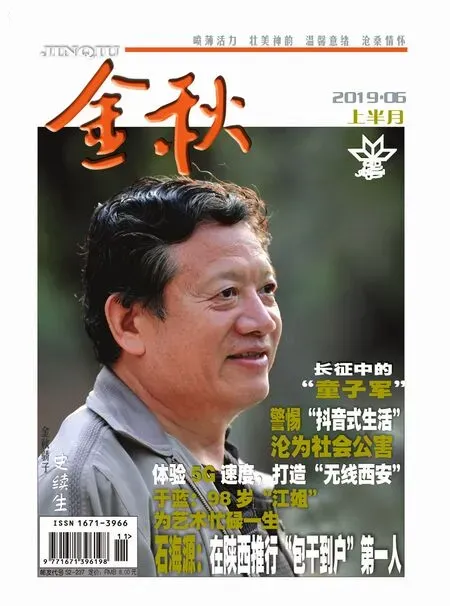大西北是我無悔的選擇
文/袁寶麟
主持人/純樸 記憶郵箱:yuminjie611@163.com
我原在上海一家大型商業(yè)銀行總行任職,捧著讓人羨慕的“金飯碗”,過著老適意(上海話,意為非常舒適)的日子。其間,我曾有過3次調往外地的機會:一次是杭州分行的一位上海籍同事想和我對調,“天堂”杭州離我老家紹興近在咫尺;一次是人事處征詢我是否愿意調往天津,條件是工資調高兩級;還有一次是南京舉辦華東物資交流大會,我去支援南京分行,分行挽留我在那里工作,應允給我一小院住房,還給我分一窩洋雞(當時南京人養(yǎng)洋雞成風)。我因留戀上海而回絕了他們,但在我27歲那一年卻選擇了貧瘠落后的大西北。
1952年初秋,潘漢年副市長代表上海市委向萬名銀行職工作動員報告,號召年富力強、有業(yè)務才能和工作經驗的銀行職工報名支援大西北。潘市長說,支援全國是中央交給上海的重大戰(zhàn)略任務,希望志在四方的好兒女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業(yè),他那充滿激情的講話打動了許多年輕人的心,也深深地打動了我。
我回家和妻子商量,她爽快地說:“這點覺悟我還是有的。嫁雞隨雞,有苦我們一起去吃。”當時,上海還沒有向全國成批輸送建設人才的先例,長輩們聽說我要去西北感到驚訝,說我“頭腦發(fā)熱”,“出風頭”,問我:“你原來連‘天堂’都不去,現在怎么愿去西北了?”我告訴他們:“原來我考慮的是個人利益,現在是國家需要”。“兩年來黨的教育使我懂得,人活著不能只為自己,人生價值的實現要與祖國富強、民族振興結合在一起。”他們見我鐵了心,都搖頭說:“你可想好了,世上沒有后悔藥。”我斬釘截鐵地回答:“大西北,是我無悔的選擇。請大家放心,我不會被困難嚇倒的,我也決不做逃兵”。
我報名被批準后,大家勸我暫時把住房、家具都留下,萬一西北苦得受不了,回來還有個窩,但我卻“破釜沉舟”:住房、家具讓給了朋友,還割了闌尾,因為我右下腹偶有隱痛,聽說西北醫(yī)療條件差,怕萬一到了那里闌尾發(fā)起炎來會要命的。出院沒過幾天,我就攜家?guī)Э诎菏妆鄙稀M械挠?059名志愿者及其家屬,分乘5趟專列,直駛西北。
專列到達西安后,按照人民銀行西北區(qū)行的安排,大家各奔東西,有的進了大漠深處,有的上了雪域高原,有的去了河西走廊……我幸運地被分配在西安,進了陜西省分行。
我們到了西北各地以后,當地銀行對我們的方方面面照顧得十分周到:盡量安排在城市里工作;給大家租好房子;與糧食部門商量特供部分大米;為了避免歧視和誤解,陜西省分行還專門發(fā)出通知,統(tǒng)一稱我們?yōu)椤吧虾=鹑跇I(yè)響應祖國號召參加大西北建設的干部”。
然而,我驚訝地發(fā)現,在號稱西北首府的西安,吃喝拉撒都是難題。我家三代人擠在兩間低矮潮濕的土坯房里,夜幕一降臨,頂棚上便成了老鼠的游樂場,下大雨時,屋里接水的盆盆罐罐便奏起了打擊樂。沒有廚房,只好在屋檐下搭塊油氈,放個爐子,湊合著炒菜煮飯。全院只有一個臭烘烘的土茅坑,上廁還得排隊等候。用水就更艱難了,得擔著水桶到外面去挑,開始是水井,后來換成自來水站,同來的曾大姐家的保姆就是因為吃不了挑水這個苦而回了上海。9個月后,工資按規(guī)定重新定了級,我定為月薪72萬元(舊人民幣,折合新幣72元,下同),在同來的人中算是比較高的,但與我在上海的工資相比只剩了個零頭。我的妻子由“教書匠”改行當銀行會計,因業(yè)務生疏,工資只定了42萬元(30年后我們的工資才上調到原來在上海時的水平,而物價已今非昔比了)。
但艱苦的生活條件并沒有動搖我們建設西北的初心,我和妻子不停地互相打氣:不就是因為西北貧困落后才需要我們來建設的嗎?隨著建設的發(fā)展,一切都會好起來的。西北人民祖祖輩輩都這樣生活,我們?yōu)槭裁床荒埽烤褪强恐@些樸素的認識和堅定的信念,我們終于闖過了“生活關”,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建設“第二故鄉(xiāng)”的洪流中去。
西北的工作條件比起上海來也艱苦很多,一年有1/3的時間是在基層和農村,下去還得自己背鋪蓋,一走就是好多里,甚至幾十里。有時蹲在農村幾個月,別說理發(fā)洗澡,就連洗腳都成了奢望。有時睡在騾馬店的大炕上,汗酸味、旱煙味、腳臭味常熏得我輾轉難眠。不過,艱苦的工作環(huán)境雖折磨人,也教育人。1953年暮春的寧陜之行,我的心靈受到了一次洗禮。寧陜地處秦嶺腹地,當時還沒公路,進山出山都靠兩條腿。那年全國銀行推行一系列新的信貸結算制度,支行的同志感到“老虎吃天”,就到省行來搬“救兵”。于是,我們3個文弱書生(兩個來自上海)腳蹬草鞋,從石泉縣進山,在人跡罕見的林海中輾轉走了兩天,才蹣跚地摸到那個巴掌大的縣城,3個人都幾乎散了架。但令人高興的是,我們一跨進支行大門,基層同志就忙著燒水讓我們燙腳,給我們蒸了熏肉和白米飯,還為我們準備了簇新的被褥。一連幾天,大家聚精會神地聽我們談政策規(guī)章、工作藝術,圍著我們不停地問這問那,我們也毫無保留地把肚里的“半瓶子醋”全倒了出來。一次次的走基層,我看到了基層同志的渴望和對我的認可,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價值。我深切地感到:大西北雖然比上海艱苦得多,卻比上海更需要我。
從1952年走進陜西,我一直鉚足了勁在這片熱土上連續(xù)耕耘了40年,還在學習探索中做了不少開創(chuàng)性的工作,如金融研究、外匯管理。雖然我只是為陜西建設增磚添瓦,但一磚一瓦上都凝聚著我的心血、鐫刻著我的忠誠。
在西北工作期間,我曾有過一次調往江南的機會。我在參加全國專業(yè)會議期間,結識了華東某分行的一位同行,兩人一見如故。有一年夏天,我在煙臺學術研討會上又遇見了他。分手前,他認真地對我說:“想回江南嗎?到我們那里去工作吧,我們正在廣招四方英才……”面對這個調回江南的難得機會,我動心了。但是,看到并肩戰(zhàn)斗的“老陜”們,充滿對美好未來的憧憬,堅守故土,發(fā)奮工作,我想,如果我違背當年扎根大西北的誓言,拍屁股走人,做了“逃兵”,不僅辜負了三秦父老的厚愛和期望,又有何面目見“江東父老”。思慮再三,最終我把飛向江南的心緊緊地拽了回來。
2018年5月,東方衛(wèi)視通過《上海支援全國》的編者,就當年上海金融業(yè)支援大西北的話題,對我追蹤采訪(《上海支援全國》是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2011年編的一本史料書,我應約撰寫了上海金融業(yè)支援大西北的回憶錄)。采訪結束時,這位年輕記者好奇地問了我一個曾經被人問過N次的問題:“放棄繁華的上海,支援落后的西北,你后悔嗎?”我毫不含糊地告訴她:“這是我自己的選擇,這一選擇是正確的,我無怨無悔。將美好年華獻給最需要我的大西北,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