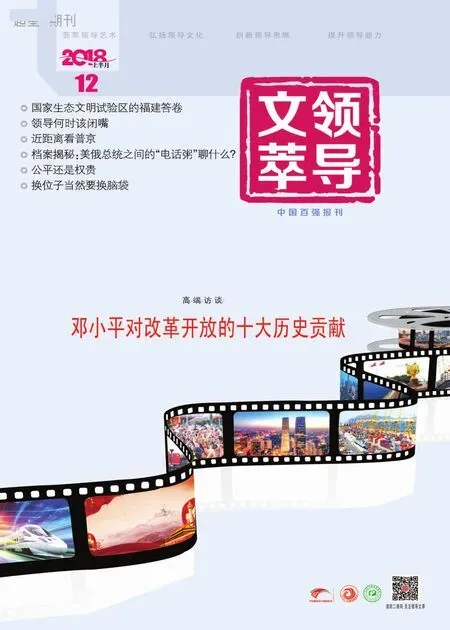這個官場“兩面人”, 為大唐盛轉衰埋下炸藥包
關山遠
01
唐朝,建國于公元618年,亡于907年,共歷二十一帝,享國289年,被公認為古代中國的巔峰。
何以言之?一個國家上上下下透露出來的氣質是:自信!政治經濟軍事硬實力,外交文化制度軟實力,均為當時之最強者,內百姓安居,外四夷臣服,唐朝皇帝被尊為天可汗。
狠狠給歷史心臟來上一椎的,是一個叫李林甫的人。
02
李林甫死后3年,“漁陽顰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安史之亂爆發。炸藥包是李林甫埋下的,只不過點燃導火索的,是著名美女楊貴妃的哥哥楊國忠。
歷史上,李林甫以“口蜜腹劍”著稱,嘴巴說話像抹了蜜,肚子里卻藏了一把劍,轉過身就把對方給捅了,“啖以甘言而陰陷之”。口里說的,跟心里想的、實際做的,完全是兩回事。這就是“兩面人”。
“兩面人”表現有各種各樣,但李林甫堪稱集大成者,如果要給“兩面人”畫像,李林甫是最稱職的模特。
其一,陰險,擅長給人挖坑下套。
“兩面人”都愛玩陰的,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當你的面熱烈鼓掌,轉身就是一記八卦掌。李林甫精于此道,他熱愛權力,當了玄宗朝宰相19年,憑什么能夠做到這一點?就是排除異己,把可能挑戰、影響自己的人一個個干掉。
其二,圓滑,是個好演員。
李林甫的仕途起點不高,但他擅長察言觀色,與宮中宦官、妃嬪交情深厚,對玄宗的舉動了如指掌,每逢奏對,都能符合玄宗的意旨,深得賞識,于是步步高升。
明明是為自己鋪路,偏偏要做成忠臣愛國的模樣。
后代學者許衡則這么評價李林甫:“奸邪之人,其心險,其術巧。惟險,故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惟巧,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御。其諂似恭,其訐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近。”精辟啊!
03
如果繼續給“兩面人”畫像,他們還有一個特點就是“自卑”。自身才學不足,便痛恨一切有才華之人,比的不是才能,是權謀。張九齡、嚴挺之等賢臣,都被李林甫趕出了朝廷。李適之、楊慎矜等政敵,都被他迫害致死。晚年的唐玄宗完全被李林甫蒙蔽,幾乎接觸不到任何有才華的大臣,也無法了解外界信息。
“自卑”的另一面,是“自大”,李林甫狂妄到了極致,他滿足玄宗的任何享樂需求,但只要玄宗想提拔一個可能對他相位造成威脅的人,他就能讓這個人出問題,被生病,被貪污,被謀反。
當然,“兩面人”最大的特征,是自私。他們是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一切都以自己為中心,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欲,他們能夠做足表面文章,無盡的謊言,滿滿的大戲。
李林甫給大唐埋下了安史之亂的炸藥包,在于他為了一己私利,居然把“出將入相”的國家體制當兒戲。
唐玄宗天寶年以前,鎮邊節度使數年就得輪換,從未有一人像安祿山這樣,可兼任二鎮節度使十數年的。節度使守邊立下汗馬功勞,可回到首都擔任重要京官,京官也常常下派到邊關,擔任節度使。這就是“出將入相”,出則為將,入則為相,邊境節度使與朝中宰相都有任期,經常輪換,也可防止做大謀反。
但是,李林甫拜相后,擔心朝中文臣到邊境擔任節度使后又回來拜相,就這么忽悠唐玄宗:“文臣為將,怯于戰陣,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驍勇善戰,而寒族在朝中沒有黨援。”如此破壞軍將輪換制度的餿主意,居然被唐玄宗采納了。
李林甫的得意算盤是:多以胡人為節度使,他們沒有文化,即使回朝來也威脅不到我。那些文化比我高的,我要死死摁住,一個也不放下去,免得功高回朝,分我權力。李林甫本人也被封為節度使,但他辭掉了,并不上任。
于是,朝廷重臣不再派下去任節度使,唐朝是一個進攻型的國家,軍隊基本上都分布在邊境,文臣下不去了,朝廷漸漸不再掌握軍權,軍權掌握在安祿山這樣的胡人手里。很難說安祿山一開始就有反骨,但他長期控制河北,專任一方,手下兵強馬壯,又見朝廷如此糜爛,有機可乘,怎會不生二心?
哈佛中國史《唐朝:世界性的帝國》一書如此評價:
“李林甫只任用非漢族人擔任節度使,他希望通過把軍隊交給和朝廷沒有瓜葛的人來消除任何通過軍功贏得政治權力的潛在競爭者。但這一政策意味著真正在外掌權的人變得逐漸和中央政府疏遠起來。有這樣一位將軍,安祿山,在東北地區起兵叛亂,終結了盛唐,并給予王朝破壞性的打擊。”
04
安史之亂后,唐朝大傷元氣,傷的是國運。
唐朝因為安史之亂,逐漸失去了西域,曾經商旅往來的陸上絲綢之路,中斷了;安祿山死了,但藩鎮割據、各自為政的格局卻進一步加重,中央王朝對地方的控制力越來越弱,因為控制與反控制,在之后的一百年間,中央與藩鎮戰爭不斷,藩鎮與藩鎮之間,為了爭奪地盤,也常大打出手。如此混亂,老百姓怎么活?于是,農民起義,遍地烽火。
唐朝的氣質也變了,不復開放與昂揚。從安史之亂到最終覆亡150年,唐朝始終掙扎在藩鎮割據、宦官專權、朋黨之爭3股風暴之中。這些,李林甫都脫不了干系。
亂世如麻中,飄浮著李林甫一張陰森森的自私的臉,“兩面人”的臉。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這么評價李林甫和唐朝另一位奸相盧杞:“謀國而貽天下之大患,斯為天下之罪人,而有差等焉。禍在一時之天下,則一時之罪人,盧杞是也;禍及一代,則一代之罪人,李林甫是也。”
從這個角度說,李林甫是歷史上最可怕的“兩面人”之一,老百姓對他恨之入骨,民間傳說中有諸多他后世輪回遭到報應的故事。
清代著名詩人查慎行(金庸的先祖)曾編過一本《因果輪回實錄》,繪聲繪色地集納了關于李林甫遭受天雷轟擊的事。
05
李林甫的真實下場,也跟傳說中被天雷轟擊差不多。
他臨終前,已經失寵。他死后,楊國忠與安祿山合謀,誣告李林甫與叛將阿布思約為父子,同謀造反。安祿山還派阿布思部落的降將入朝作證。唐玄宗命有司審理。李林甫的女婿楊齊宣擔心自己受到牽連,便附和楊國忠,出面證實。
當時,李林甫尚未下葬,被削去官爵,抄沒家產。諸子被除名流放嶺南、黔中,親黨中則有50余人被貶。唐玄宗還命人劈開李林甫的棺木,挖出口內含珠,剝下金紫朝服,改用小棺以庶人之禮安葬。
歷史就是這么吊詭:李林甫是著名的“兩面人”,楊國忠也是“兩面人”,李林甫當初提攜他時,以為這是個傻子,不會威脅自己的相位;安祿山更是“兩面人”,之前一直在他面前扮出一副唯唯諾諾的模樣。3個“兩面人”,湊在一起,加上一個昏聵的唐玄宗,領銜主演了唐朝滅亡的悲劇大片。
能夠把歷史興衰的秘密,歸結到一個人或幾個人的身上嗎?或許,更精確的,應該歸結于李林甫、楊國忠、安祿山還有唐玄宗,由他們的自私、貪欲和昏聵共同構成的混亂體制,這種混亂體制,不能識別“兩面人”,只會助長“兩面人”如毒蕈般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