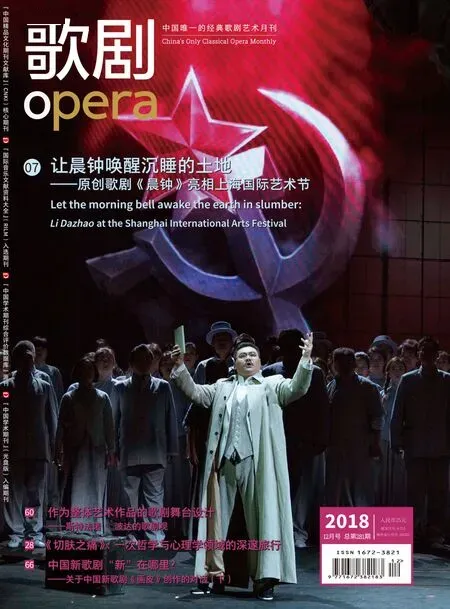穆理新歌劇《瑪妮》大都會首演
文:謝朝宗(本刊駐美特約記者)
瑪妮(Marnie)是個不斷變化身份的女子,她每工作一段時間,獲取到該公司的保險箱號碼后,就把存款偷走,然后改名換姓、改頭換面再去另一家公司上班,對新東家重施故伎。像這樣的人,有不同的“藝術分身”也是理所當然,瑪妮的故事先是被寫成一本小說,然后拍成電影,現在又變成一部歌劇。
歌劇《瑪妮》(Marnie
)由美國作曲家尼可·穆理(Nico Muhly)所作,是這位還不到40歲的作曲家在大都會歌劇院上演的第二部作品。他的上一部歌劇《兩個男孩》(Two Boys
)取材于一則當代英國的網絡犯罪新聞,《瑪妮》則是一個1960年代英國的辦公室詐騙故事——他似乎對發生在英國的犯罪故事特別感興趣。

穆理的音樂興趣十分廣泛,不過可能因為他從小就是教堂合唱團成員,所以復調音樂是他最鐘愛的音樂形式。《瑪妮》一開始在辦公室里的場景,就是以這種多聲部復調的方式呈現,許多細微的不協和音,正象征著一個忙碌的辦公室里亂中有序的景象。然而在這個很有現代感的開場后,第一幕逐漸失去戲劇張力,這個問題有很大一部分是來自劇本結構——不斷引出新的場面及角色,卻并沒有累積戲劇張力的效果,反而分散了觀眾最關心的故事:瑪妮行為的心理動機及后果。瑪妮遇見改變她命運的人物——由客戶變成她老板,最后又變成她丈夫的印刷廠老板馬克(Mark Rutland);瑪妮用偷來的錢讓母親搬到好一點的地方去住,但她們的會面很快演變成母親的抱怨;馬克的弟弟特里(Terry)硬要跟瑪妮約會;瑪妮在酒吧里遇見她以另一個身份存在時的舊識;馬克的母親抱怨馬克管理公司無方……這些場景與瑪妮故事的關系深淺不一,情節主要是在鋪陳,但在歌劇里它們都被處理得很相似:長度相當、中慢板的節奏、近宣敘調的旋律、沒有戲劇高低潮的起伏。穆理的音樂有著極簡音樂的細致和輕靈,他以不同的樂器來代表不同人物(如瑪妮是雙簧管、母親是中提琴),給了樂團許多表現的機會,但整體說來雖然悅耳但太平淡,以致不能抓住人心。
在第一幕結束前,馬克因抓住了瑪妮欺詐的把柄,以此要挾她嫁給他,在蜜月時更進一步要挾而強暴她,該幕結束在瑪妮割腕自殺生死未知的懸疑時刻。第二幕開始,我們知道她得救了,但她和馬克的婚姻也陷入僵局,表面和諧、私底下劍拔弩張。馬克在這一幕開場時的詠嘆調,是全劇最抒情的段落,他回溯在林子里撞見一頭小鹿,鹿的驚惶無措讓他想起了瑪妮。他和瑪妮談條件,如果瑪妮答應去看心理醫生,他就讓瑪妮去看她喜歡的賽馬。這引來全劇音樂性最豐富的兩個場景:一是瑪妮喜歡的馬在奔跑時被射傷最后不治,整個樂團將音樂推向最高潮后戛然而止,充分展現了以音樂創造戲劇性的效果;第二個場景是她去看心理醫生,瑪妮的幾個分身吐露出她對過去的悔恨和對未來的不安,樂團的伴奏則往往傳達出相反的情緒,顯示她內心的掙扎。穆理的音樂在第二幕起到了主導情緒的作用,比起之前一幕要有趣許多。
《瑪妮》的制作和演出團隊都是一流的。導演邁克爾·梅耶(Michael Mayer)和舞臺設計朱利安·克勞奇(Julian Crouch)以不斷變換位置的條幅投影轉換場景,達到迅速變場的目的,投影也以顏色和圖案呈現不同情緒。琳尼·佩吉(Lynne Page)設計的服裝給瑪妮鮮艷的色彩,在其他角色的灰黑中特別突出。凱文·亞當斯(Kevin Adams)的燈光,有效地制造出陰沉的感覺。
女主角伊莎貝爾·倫納德(Isabel Leonard)飾演的瑪妮是一個壓抑內斂的人物,觀眾感覺到她有著痛苦的過去,但卻始終不能真正了解其內心,就如她的丈夫一樣;飾演馬克的克里斯托弗·馬爾特曼(Christopher Maltman)也給予了這個角色豐富的性格;伊斯汀·戴維斯(Iestyn Davies)的假聲男高音給了特里一種邪惡的感覺;女中音德尼斯·格雷夫斯(Denyce Graves)則給了瑪妮的母親豐滿的聲音。指揮羅伯特·斯帕諾(Robert Spano)把不同層次的音樂線條都詮釋得清晰明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