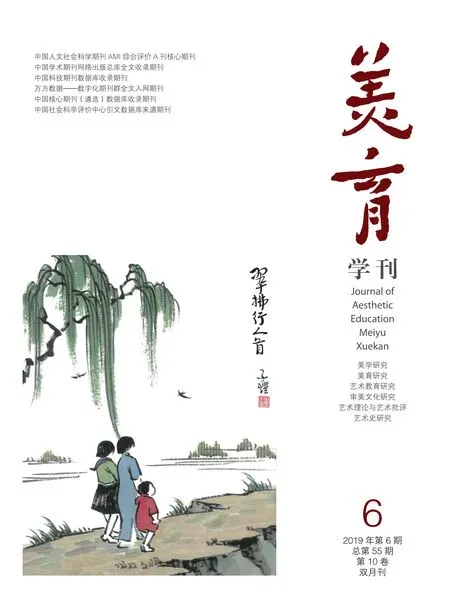敘事藝術(shù)的抒情倫理
徐 承
(杭州師范大學(xué) 藝術(shù)教育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1121)
一、問題的提出
海外華人中國抒情傳統(tǒng)學(xué)派之理論奠基人高友工認為,中國藝術(shù)及其美學(xué)的主流是抒情傳統(tǒng),中國古代不同門類的藝術(shù)多以抒情詩的形態(tài)為審美理想,而中國抒情詩這一美學(xué)典范的最高成就是在圓滿的形式結(jié)構(gòu)中蘊蓄(即象征)深厚的倫理價值從而造就抒情境界。(1)參見高友工:《美典:中國文學(xué)研究論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8年。尤其是《文學(xué)研究的美學(xué)問題》《中國文化史中的抒情傳統(tǒng)》《試論中國藝術(shù)精神》《律詩的美學(xué)》等篇。高友工的觀點遠有儒家“比興”闡釋學(xué)的支持,在海內(nèi)外應(yīng)和者甚眾。然而最近,浙江大學(xué)徐岱提出了一個與之截然相反的觀點:“與‘抒情傳統(tǒng)派’試圖占據(jù)‘道德制高點’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馳,由‘抒情主義’主導(dǎo)的藝術(shù)往往受限于自我利益的得失和功名利祿的計較,在倫理方面完全處于不堪一擊的境況。”[1]180徐岱的批評矛頭主要指向中國古典抒情詩。本文無意加入關(guān)于中國抒情文藝之倫理價值評判的爭論。但高、徐二位針鋒相對的論述帶給我們一個啟示:對抒情經(jīng)驗加以倫理考量是當代藝術(shù)學(xué)尤其是倫理美學(xué)研究中的重要課題。不過,盡管尼采早已指出:“美學(xué)必須首先解決這個問題:‘抒情詩人’怎么能夠是藝術(shù)家?”[2]17但就當今學(xué)界的研究熱度而言,“抒情倫理”研究相對于“敘事倫理”研究處于絕對的弱勢,后者業(yè)已成為以小說和電影為主要對象的文化研究的熱門話題。究其原因,或許在于抒情藝術(shù)往往以個體的情感轉(zhuǎn)圜作為作品的主體結(jié)構(gòu),格局較小、思想單純,不似敘事藝術(shù)能夠通過對人類社會行為的多維摹寫而展開宏闊的結(jié)構(gòu)、探討復(fù)雜的人倫問題,從而在倫理批評方面具有更大的可被挖掘的空間。恰如盧卡奇所聲稱:“在小說中,倫理學(xué)是一種純形式上的前提,這種前提由于其深度而有可能進入決定形式的本質(zhì),由于其廣度而使同樣決定形式的總體得以可能形成,并由于其包羅萬象而使構(gòu)成要素的平衡得以實現(xiàn)。”[3]敘事藝術(shù)庶幾如此。
當然,“抒情倫理”研究并不因此而應(yīng)當被忽略,畢竟“抒情”是一項重要的人類文化活動,甚至是產(chǎn)生藝術(shù)的原初推動力之一。徐岱曾提出大多數(shù)中國古典抒情詩“事實上可以看作是一種具有抒情色彩的‘微型小說’”[1]155,以此說明敘事在藝術(shù)世界中的普泛性。然而我們在承認抒情對敘事確實具有某種結(jié)構(gòu)上的依賴性的同時,也應(yīng)當注意到,抒情在敘事藝術(shù)中正是暫停(或暫緩)故事情節(jié)的鋪陳而表露人物甚至作者的感情與思想的部分,因而往往可以被視作作品的“倫理之眼”。就此而言,對敘事藝術(shù)展開抒情倫理研究便成為一個別開生面的課題,它似乎屬于“敘事倫理”研究的大范疇,但在微觀上卻借重“抒情倫理”的批評方式。本文嘗試在這方面作出一些初步探索,既是對“敘事倫理”研究的充實,也是為“抒情倫理”曲線正名。
二、起源場景
現(xiàn)代西方文藝理論往往把抒情詩、敘事文學(xué)(以史詩與小說為代表)、戲劇看成是三種不同的文類,三者間的差異主要通過內(nèi)容呈現(xiàn)的主客觀性或發(fā)聲的人稱來加以厘定,如黑格爾、韋勒克與沃倫、卡勒等都是這么做的。(2)參見黑格爾:《美學(xué)》第3卷上冊,朱光潛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79年,第20頁;韋勒克、沃倫:《文學(xué)理論》,劉象愚、邢培明、陳圣生、李哲明譯,北京:文化藝術(shù)出版社,2010年,第261頁;卡勒:《文學(xué)理論》,李平譯,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76-77頁。這樣的文類區(qū)分帶有相當程度的理想性和宏觀性,我們可以把某部具體的文學(xué)作品在總體上歸為三種文類中的一種,但就這部作品的微觀層面而言,則完全有可能同時混融了抒情、敘事和戲劇的成分。本文所論及的敘事藝術(shù),是在比文類更為廣泛的藝術(shù)體類的意義上,指稱一切以故事情節(jié)的展開為主體結(jié)構(gòu)的藝術(shù)形式。這樣的敘事藝術(shù)具有廣義上的敘事性,無論這種敘事是通過某一人稱的獨白還是多個角色的對白來實現(xiàn)的;同時因其敘事結(jié)構(gòu)必須在時間中展開而具有了借抒情來調(diào)節(jié)敘事節(jié)奏的可能性與必要性。本文所論及的抒情,則是指一種廣義的藝術(shù)功能,即抒發(fā)某一個體(角色、作者、隱含作者等)的內(nèi)在情感;所謂“抒發(fā)”,并非簡單的表現(xiàn),而是指以音樂性來對情感予以賦形(形式化)和延展(風格化)。
就此而言,敘事藝術(shù)的鼻祖荷馬史詩盡管情節(jié)跌宕、氣勢宏闊,卻從來不乏美妙的抒情聲音。《伊利亞特》開篇即唱:“女神啊,請歌唱佩琉斯之子阿基琉斯的致命的忿怒,那一怒給阿開奧斯人帶來無數(shù)的苦難,把戰(zhàn)士的許多健壯英魂送往冥府,使他們的尸體成為野狗和各種飛禽的肉食……”[4]這一聲朝向第二人稱“女神”的吟唱,以雄奇的場景拉開整部戰(zhàn)爭大戲的帷幕,為全詩定下悲壯、慘烈和英雄主義的基調(diào)。里爾琴伴奏下(3)關(guān)于荷馬史詩的演唱和伴奏方式,參見保羅·亨利·朗:《西方文明中的音樂》,顧連理等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4年,第7頁。的抒情唱詞,不僅在情緒營造方面把聽眾置入心情激蕩、悠然神往的境地,還在敘事上打開一扇窗口,把整部《伊利亞特》的情節(jié)起點錨定在阿基琉斯因與阿伽門農(nóng)爭執(zhí)而罷戰(zhàn)從而導(dǎo)致特洛伊戰(zhàn)局急轉(zhuǎn)而下這一戲劇性的轉(zhuǎn)捩點。抒情的內(nèi)容旋即使人思緒紛紛,產(chǎn)生倫理方面的疑問:既然戰(zhàn)局的逆轉(zhuǎn)、戰(zhàn)士的敗亡緣于將帥間的私人恩怨,那主人公的行為是否是道德的?作品即將描述雙方戰(zhàn)士的生命如芻狗般被命運拋棄,那作者的創(chuàng)作動機遵循的是怎樣的道德法則?由此反映出史詩時代的古希臘社會具有怎樣的道德狀況?類似這樣的問題,需聽取作品的長篇敘事方能尋找答案,但這些問題的提出,卻緣于這段抒情歌詞所激起的對戰(zhàn)爭中螻蟻般的生命的深深同情。換言之,同情使人發(fā)出道德追問,產(chǎn)生窮究敘事情節(jié)的興趣。
相對于通篇保持著緊張與激烈的《伊利亞特》,《奧德賽》以主人公戰(zhàn)后重返家園的漂泊、懷念、憂思為主題,整體風格更接近于一闋悠遠綿長的抒情詩。對于這部與《伊利亞特》風格迥異的《奧德賽》,人文主義批評家喬治·斯坦納有一段杰出的評論,點出了后者所蘊含的抒情倫理的奧妙:“我猜想,荷馬是在他青壯年時期完成了編撰《伊利亞特》的任務(wù)。《伊利亞特》有著年輕人的殘酷無情。隨著經(jīng)驗日豐,感情日沛,他在經(jīng)歷更為豐富、感知力更加細膩時,《伊利亞特》中的人生觀可能讓荷馬感到殘缺。……在他人生的后半段,這個游歷多方的詩人可能回顧了《伊利亞特》,將其中對于人類行為的態(tài)度和他自己的親身經(jīng)歷進行比較。在比較中,荷馬保持著微妙的平衡,對《伊利亞特》中的人生觀既尊重,又批判,結(jié)果就誕生了《奧德賽》。荷馬用驚人的敏銳感從特洛伊的傳奇中選出了一位最接近‘現(xiàn)代’精神的英雄人物做主人公。奧德修斯在《伊利亞特》中就已標志著從單純的英雄生涯向一種對信念更具懷疑、敏感、謹慎的精神生活的過渡。就像奧德修斯一樣,荷馬摒棄了阿基琉斯世界中那種直露粗糙的價值觀。在創(chuàng)作《奧德賽》時,他穿越靈魂的遙遠距離回望《伊利亞特》,既有緬懷之情,又含笑帶著懷疑。”[5]這里最后一句話文風雋永、內(nèi)涵豐贍,道出了《奧德賽》所以能世世代代傳唱不息的藝術(shù)精髓:對英雄生涯的伴有道德疑慮的懷想與抒情。
從我們對兩部荷馬史詩的分析來看,敘事藝術(shù)的抒情倫理批評大有可為。而《伊利亞特》與《奧德賽》的風格差異預(yù)示著敘事藝術(shù)的抒情至少可以有兩種不同的方式:一是保持敘事與抒情各自的界限,令二者各行其是,同時相互映照、相互推動;二是敘事與抒情混融,造就一種高度風格化的抒情性敘事的美學(xué)效果。后一種情況的最終發(fā)展結(jié)果就是抒情小說(或稱詩化小說)、抒情詩劇、詩化電影等在整體風格上接受抒情詩美學(xué)影響的敘事藝術(shù)。如北京大學(xué)吳曉東的《現(xiàn)代“詩化小說”探索》一文即對西方自象征派小說至意識流小說,以及中國從廢名、沈從文、何其芳到馮至、汪曾祺的詩化小說傳統(tǒng)予以清理,[6]相似主題的研究成果還有很多。筆者更感興趣的則是前一種情況,亦即在典型(敘事情節(jié)具有高度戲劇性)的敘事藝術(shù)中所出現(xiàn)的抒情。關(guān)注這類敘事藝術(shù)的抒情倫理,或許更能體現(xiàn)抒情倫理批評在敘事學(xué)研究中的重要性。
三、典范的樹立
眾所周知,中國古代《詩經(jīng)》中的詩作在其原始“表演”場景中是以“詩樂舞”一體的方式呈現(xiàn)的,音樂充當了聯(lián)結(jié)抒情詩與表演藝術(shù)的紐帶。無獨有偶,古希臘戲劇的誕生,也與音樂和抒情詩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關(guān)系。美國音樂文化史學(xué)家保羅·亨利·朗曾指出:“在感情表現(xiàn)到達極度亢奮時,戲劇會轉(zhuǎn)向音樂。這是最單純和最古老的戲劇形式的本質(zhì)要求,因為人的靈魂被深深震撼而只能胡言亂語般呼喊時,只有音樂才能繼續(xù)表達感情。……埃斯庫羅斯,一位音樂家,一位合唱抒情詩人,卻創(chuàng)造了因深刻的內(nèi)心激動而觸發(fā)的作品。……他所使用的手段具有音樂性—抒情性的特質(zhì)。在埃斯庫羅斯時代,音樂和抒情仍是不可分割的整體,言辭與音調(diào)、詩歌與旋律同時被創(chuàng)造出來。”[7]13簡言之,古希臘戲劇是與抒情詩和音樂同源的,歐洲戲劇的起源須追索至其與詩尤其是音樂性抒情詩之間的密切聯(lián)系。
當亞里士多德寫作文藝理論著作《詩學(xué)》的時候,他所謂的“詩”指的是包括史詩、悲劇、喜劇等在內(nèi)的所有當時以詩格寫作的文類。《詩學(xué)》首章將該書的寫作任務(wù)之一描述為對“應(yīng)如何組織情節(jié)才能寫出優(yōu)秀的詩作”[8]27予以探討,這就明示了他重點考察的“詩”乃是“組織情節(jié)”的敘事藝術(shù)。需要提請注意的是,這些敘事藝術(shù)既然通篇以格律詩體寫成,那不管是否配以音樂或譜以曲調(diào),都已因為格律的組織而使語言具有了一定的音樂性,因而也不可避免地在整體上帶有一定的抒情性。經(jīng)過對幾種不同詩類的比較,《詩學(xué)》最終將筆墨集中于悲劇,可見悲劇是亞氏心目中敘事藝術(shù)的最高代表。
古希臘悲劇一般都遵循“開場、進場歌、第一場、第一合唱歌、第二場、第二合唱歌、第三場、第三合唱歌、第四場、第四合唱歌……退場”這樣的結(jié)構(gòu),每一場劇情表演中間都插入一段歌隊合唱,用以發(fā)揮抒情的藝術(shù)功能。羅念生認為:“(古希臘)戲劇的合唱歌的風格取自抒情詩。所以,從繼承的關(guān)系來看,戲劇乃是史詩與抒情詩的結(jié)合。”[9]抒情合唱的插入使得戲劇情節(jié)的展開具有了規(guī)律性的停頓,從而為整體敘事帶來了行止交替的節(jié)奏感。不過,亞里士多德顯然對歌隊的抒情合唱不太重視,他認為:“情節(jié)是悲劇的根本,用形象的話來說,是悲劇的靈魂。……在剩下的成分里,唱段是最重要的‘裝飾’。”[8]65也就是說,亞里士多德只是把抒情唱段視作對敘事的錦上添花,他的關(guān)切集中于悲劇“對一個嚴肅、完整、有一定長度的行動的摹仿”[8]63,亦即純粹敘事情節(jié)的展開方式。亞里士多德的敘事倫理批評也僅僅著眼于敘事情節(jié),依據(jù)他的價值評判,優(yōu)秀的悲劇表現(xiàn)好人(具備智慧與德行的人)遭受不幸命運的情節(jié),從而激起觀眾憐憫與恐懼的情緒并使之得到凈化。
亞里士多德對悲劇抒情段落的輕忽是令人遺憾的,這導(dǎo)致后世的敘事藝術(shù)研究尤其是敘事倫理研究很少關(guān)注作品的抒情成分。但所幸,美學(xué)史上也有對古希臘悲劇之抒情合唱的美學(xué)功能予以高度評價者,尼采和席勒便是個中代表。尼采曾在他的名著《悲劇的誕生》中用他那種廣為人知的極端語調(diào)宣稱:“悲劇從悲劇歌隊中產(chǎn)生,一開始僅僅是歌隊,除了歌隊什么也不是。……用來銜接悲劇的合唱部分,在一定程度上是孕育全部所謂對白的母腹,也就是孕育全部舞臺世界和本來意義上的戲劇的母腹。……悲劇本來只是‘合唱’,而不是‘戲劇’。”[2]25-33這幾乎就是在說,是合唱的擴展構(gòu)成了古希臘悲劇,是抒情歌藝術(shù)孕育了戲劇藝術(shù)。如果有讀者嫌尼采的用語過于夸張的話,那么席勒對古希臘悲劇歌隊合唱部分的美學(xué)評價似應(yīng)得到更多的信服:“它摒棄了事件的狹小天地,將自身擴大到超越過去與未來、超越遙遠的時代與民族以及整個人類的程度,推斷出生命的重大歸結(jié),并宣告智慧的教訓(xùn)。除此之外,它還牽扯到想象的威力——牽扯到似乎以天神般的步伐攀登世界萬物的頂峰的一種大膽的抒情自由;而且它是同曲調(diào)和節(jié)奏的所有明顯的影響一道在語調(diào)和動作中產(chǎn)生了這種自由。”(4)席勒:《論悲劇中歌隊的作用》,轉(zhuǎn)引自喬治:《戲劇節(jié)奏》,張全全譯,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6年,第73頁。席勒的意思是,戲劇的劇情作為事件受限于其發(fā)生的特定時間與空間,而合唱則有一種特殊的美學(xué)功能,能將該事件所包含的生活智慧推廣至超越時空的普遍層面,并產(chǎn)生“抒情自由”的審美高峰體驗。在筆者看來,“抒情自由”的概念暗示抒情合唱中包含著重要的倫理維度。
通過文本分析不難發(fā)現(xiàn),歌隊的抒情合唱段落對于古希臘悲劇倫理內(nèi)涵的揭示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以埃斯庫羅斯的《普羅米修斯》和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為例。在《普羅米修斯》中,歌隊扮演了一組劇中人角色——提坦神俄刻阿諾斯和忒堤斯的十二個女兒。女神的抒情歌聲在與普羅米修斯對話的過程中唱出,不僅抒發(fā)了對英雄遭遇的深切同情,而且表達了鮮明的道德立場:
除了宙斯,哪一位神不氣憤,不對你的苦難表同情?
現(xiàn)在整個世界都為你大聲痛哭,那些住在西方的人悲嘆你的宗族曾經(jīng)享受的偉大而又古老的權(quán)力;那些住在神圣的亞細亞的人也對你的悲慘的苦難表同情。
那些住在科爾喀斯土地上的勇于作戰(zhàn)的女子和那些住在大地邊緣,邁俄提斯湖畔的斯庫提亞人也為你痛哭。
那駐在高加索附近山城上的敵軍,阿拉伯武士之花,在尖銳的戈矛的林中吶喊,也對你表示同情。
海潮下落,發(fā)出悲聲,海底在嗚咽,下界黑暗的地牢在號叫,澄清的河流也為你的不幸的苦難而悲嘆。[10]
這些抒情之辭對宙斯予以道德孤立,對普羅米修斯則表達了來自神界、人類各種族,乃至擬人化的山川湖海等自然界萬物的道義和情感支持,其內(nèi)含的倫理評判隨著抒情意象的一一展開而仿佛具有了充斥全宇宙的磅礴力量。誠如亞里士多德所言,要引發(fā)觀眾的憐憫與恐懼之情,須讓劇中的好人遭受不幸。然而如何證明并讓觀眾充分感受普羅米修斯的德性之“好”?單純依靠敘事性的念白恐怕有些蒼白無力,此段抒情合唱則以感人至深的藝術(shù)效果使觀眾對普羅米修斯產(chǎn)生強烈的道德情感,有力地保障了悲劇功能——引發(fā)憐憫與恐懼——的實現(xiàn)。
《俄狄浦斯王》的歌隊扮演的是十五名睿智的忒拜城長老,他們一共出場合唱五次。進場歌被安排在開場俄狄浦斯得報忒拜疫情之后,用以描述男女老少受災(zāi)的慘狀并向諸神發(fā)出禱告。這段抒情歌仿佛在急速推進的劇情中間插入了一幅相對靜止的畫面,通過對無辜平民受災(zāi)之苦的近景呈現(xiàn)來逼問引起災(zāi)異的罪魁禍首。之后又有四闕合唱歌,依次安插在剩余五場之間,其內(nèi)容主要是對道德律令與神的關(guān)系、神的權(quán)威和公義性,以及俄狄浦斯德行高尚卻遭受不幸命運的事實——上述幾項內(nèi)容相互之間顯然具有強烈的倫理張力——做出評論和感嘆。《俄狄浦斯王》的敘事情節(jié)具有步步緊逼、無可逆轉(zhuǎn)的緊張和絕望,抒情唱段的加入,尤其是對神義論和宿命論等人生哲理問題的風格化探討,則在一定程度上舒緩和消解了戲劇化敘事所帶來的緊張感和絕望感,有利于觀眾暫時跳出情節(jié)推進的急流作一些感受與反思,從而調(diào)整和平衡已被激起的極端情緒。套用亞里士多德的術(shù)語來說,情節(jié)的不斷“突轉(zhuǎn)”和“發(fā)現(xiàn)”造成了強烈的戲劇性,抒情成分則對由此引發(fā)的觀眾的“憐憫”與“恐懼”之情予以“凈化”。
相對于荷馬史詩,古希臘悲劇對抒情顯然具有了更加自覺的形式安排,同時分派給它更多、更集中的倫理批判的任務(wù)。敘事藝術(shù)家對抒情的形式上的運用和語義層面的利用已經(jīng)漸趨成熟。放眼更長的歷史,將能看到古希臘悲劇在抒情倫理的表現(xiàn)方面實在具有某種典范意義。
四、隱匿的傳統(tǒng)
美國戲劇學(xué)者威爾森和戈德法布指出:“歌隊是古希臘戲劇中的關(guān)鍵要素,也是最有特色的要素。自古希臘戲劇后,歌隊再沒有以同樣的方式出現(xiàn)過。”[11]不過在筆者看來,之后再沒有出現(xiàn)過的僅僅是悲劇歌隊的外在演出形式,而其內(nèi)在精義,亦即抒情段落內(nèi)嵌于敘事結(jié)構(gòu)中并體現(xiàn)特殊的倫理關(guān)懷這一美學(xué)特點,則在后世許多敘事藝術(shù)中得到了繼承和新的發(fā)展。
保羅·亨利·朗在談及古羅馬戲劇時指出:“在(古羅馬)戲劇領(lǐng)域中,我們重又遇到希臘戲劇,但拉丁變種與其希臘前身有很多細節(jié)上的不同:合唱被完全取消;羅馬人只有獨白或獨唱。”[7]41他在談及中世紀戲劇時又指出:“瑪麗亞·瑪格德琳(5)瑪麗亞·瑪格德琳即《圣經(jīng)·新約》中的圣徒抹大拉的馬利亞,為中世紀教會戲劇中的重要角色。的悲歌(‘悲傷詠嘆調(diào)’)應(yīng)被認為是(中古教會)音樂戲劇的中心。”[7]104把這兩句話聯(lián)系起來,可以看出一種發(fā)展趨勢:古羅馬和中世紀的戲劇逐漸以獨白和獨唱代替了古希臘悲劇中的合唱部分。按照浪漫主義詩論的觀點,獨白和音樂性是抒情詩的兩個核心要義。(6)參見艾布拉姆斯:《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tǒng)》,酈稚牛等譯,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5年版,第22-23、98-104頁。在這一美學(xué)視野下重識古羅馬與中世紀戲劇的上述發(fā)展趨勢,可以認為,在古希臘與文藝復(fù)興之間的漫長歲月里,歐洲戲劇逐步凝練和強化了其整體結(jié)構(gòu)中的抒情歌段落。
16世紀晚期的歐洲正處在文藝復(fù)興運動的高潮階段。莎士比亞是這一時期歐洲文化的代表人物,他的戲劇作品繼承了古代詩體戲劇的寫作傳統(tǒng),不僅以有格律的韻文寫成,(7)莎學(xué)專家孫大雨指出:“莎氏的戲劇作品,遠紹古希臘、羅馬戲劇詩人們的優(yōu)良傳統(tǒng)。莎劇是戲劇,同時又是詩,而且基本上是用有格律的韻文所組成,所以古時叫做戲劇詩,近今又叫詩劇,是戲劇和詩渾然一體的文藝作品。”孫大雨:《莎士比亞的戲劇是詩劇》,載《群言》,1986年第10期,第34頁。而且大量采用抒情詩和民間歌謠供劇中角色吟誦或演唱。如《羅密歐與朱麗葉》中出現(xiàn)了三首十四行詩,其中兩首分別是全劇的開場詩和第二幕的開場詩,以合唱(chorus)的方式提示情節(jié),并對劇中人的悲劇命運及其社會原因予以倫理點評,其作用近于古希臘悲劇的歌隊合唱;另一首則是著名的羅密歐與朱麗葉舞會邂逅時所吟誦的對白十四行詩,它以宗教比喻傳達羞澀而熱烈的愛情,是全劇最為膾炙人口的段落之一。《哈姆雷特》中出現(xiàn)了多個歌謠片段,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發(fā)瘋后的奧菲利婭所唱的幾段歌謠。且看一例:
姑娘,姑娘,他死了,一去不復(fù)來;頭上蓋著青青草,腳下石生苔。殮衾遮體白如雪,鮮花紅似雨;花上盈盈有淚滴,伴郎墳?zāi)谷ァ12]
這本是民間倩女哭情郎的抒情歌謠,癡情而凄美,在被逼瘋的奧菲利婭口中唱來,卻帶有一種冷峻的隱喻的意味,仿佛是從女性視角出發(fā)對宮廷斗爭予以審視和控訴,歌詞中的死亡意象則以神秘的氣息預(yù)示了《哈姆雷特》全劇的慘烈結(jié)局。
當莎士比亞在倫敦南郊的環(huán)球劇院大顯身手的時候,文藝復(fù)興的策源地意大利佛羅倫薩正在興起一種新的敘事藝術(shù)形式——歌劇。歌劇(opera)與一般戲劇(drama)的最大不同在于,它是從西方古典音樂的搖籃中成長起來的敘事藝術(shù)形式,其戲劇性——此處以亞里士多德所謂敘事情節(jié)的“突轉(zhuǎn)”與“發(fā)現(xiàn)”來定義這一概念——主要通過歌唱而非說白來呈現(xiàn)。(8)只有極少數(shù)歌劇和輕歌劇會用說白來推動情節(jié)。誠如美國歌劇學(xué)者科爾曼所言:“作為一種戲劇類型,它(歌劇)的本質(zhì)存在無論在細節(jié)上還是在整體上都是由音樂的表達所決定。”[13]正是在這樣的美學(xué)理念之下,歌劇發(fā)展出了主要以宣敘調(diào)和詠嘆調(diào)的交替演唱來完成全劇進程的藝術(shù)形式。宣敘調(diào)(recitative)的意大利語源意為“朗誦”,是一種接近于日常說話的演唱,其節(jié)奏自由而富于變化,不構(gòu)成有規(guī)律的節(jié)拍,樂句長短具有很大彈性,音調(diào)的旋律性不強,歌詞也不押韻。宣敘調(diào)多用于角色間的對唱,其實就相當于被譜以音樂的對白,承擔著推動敘事情節(jié)發(fā)展的功能。詠嘆調(diào)(aria)的意大利語源意為“歌”,是以旋律性見長的抒情歌曲,其節(jié)奏往往規(guī)律有致,歌詞也多采用押韻的詩體。除獨唱以外,各種重唱采用的也都是詠嘆調(diào)的形式,合唱也更接近抒情歌。于是,宣敘調(diào)和詠嘆調(diào)的交替演唱,在美學(xué)上就構(gòu)成了敘事與抒情的輪換。這種內(nèi)嵌于敘事的抒情方式,隱然呼應(yīng)了古希臘戲劇與莎士比亞戲劇中的抒情段落,無怪乎早期歌劇創(chuàng)作者都認為(實質(zhì)是想象)他們的工作是在恢復(fù)失傳已久的古希臘戲劇。事情正如保羅·亨利·朗所言:“他們(作為人文主義者的意大利歌劇先驅(qū))至少看出希臘戲劇的抒情性質(zhì)。他們猜測,不僅有歌隊合唱,還有真正的詠嘆調(diào)穿插在整部戲中,在感情高潮時,劇情變成抒情的夸張,因此需要音樂,猶如教堂的尖頂需要一口鐘。希臘戲劇的根本性質(zhì)的確是抒情藝術(shù),其抒情性只有現(xiàn)代意大利的戲劇堪與之比美。因此,它被視為opera是可以設(shè)想的,因為‘opera’就意味著opera in musica,就意味著音樂,而音樂是抒情的同義詞。”[7]344
詠嘆調(diào)之所以成為歌劇中最有代表性的、被傳唱最多的唱段,其原因就在于它是整部歌劇敘事結(jié)構(gòu)中專門用以抒情的段落,以優(yōu)美的旋律集中體現(xiàn)角色的情感、性格,并反映創(chuàng)作者(包括作曲家與臺本作者)的倫理意圖。限于篇幅,本文僅舉一例。
普契尼的《蝴蝶夫人》是歷史上演出率最高的意大利歌劇之一。它的劇情主要講述日本少女巧巧桑(昵稱“蝴蝶”)拋棄家族信仰嫁給了美國駐日海軍上尉平克爾頓,然而平克爾頓抱著玩弄的態(tài)度,很快就回國與一美國女子再次締結(jié)婚姻。蝴蝶在孤獨中產(chǎn)下平克爾頓的孩子,并終于盼來了平克爾頓返日,孰料平克爾頓只是和他的美國妻子一起來領(lǐng)走蝴蝶的孩子。悲憤的蝴蝶蒙住孩子的雙眼執(zhí)匕首自殺身亡,孩子則留給了被罪惡感包圍的平克爾頓。全劇的敘事雖不急迫卻充滿了戲劇張力,而劇中最享盛譽的一首詠嘆調(diào)《晴朗的一天》就出現(xiàn)在蝴蝶被平克爾頓離棄后在家門前的山坡上期盼和想象丈夫自海外歸來的段落:
當晴朗的一天,在那遙遠的海面,我們看見了一縷黑煙,有一只軍艦出現(xiàn),一只白色的軍艦平穩(wěn)開進了港灣,轟隆一聲禮炮。看吧!他已經(jīng)來到!我不愿跑去相見,我,不,我一人站在小山坡上邊,長久地只向海面張望,期待著和他幸福地相見。看遠處有一個人像小黑點,他急急忙忙奔跑,愈走愈近,奔向這邊。誰來了?誰來了?鈴木啊,你猜一猜,誰在叫,誰在叫?“我親愛的小蝴蝶,你到哪里去了?”我一句話也不講,就悄悄躲在一旁,我心在跳躍,滿腔熱情像火焰般地燃燒。他這樣快活不停在喊叫,在喊叫:“我最親愛的蝴蝶,快來我的懷抱。”這聲音還是像從前一樣美好,一切痛苦都忘掉。聽吧,我的鈴木!啊,我相信他一定來到,一定來到。[14]
歌詞展開了一幅蝴蝶幻想中的圖景,充滿與愛人重聚的甜蜜、矜持、激動,以及對幸福生活的熱切渴盼。然而承載著這些滿懷希望的歌詞的,卻是一支憂傷、痛苦、絕望的旋律,通過戲劇抒情女高音(spinto sopranos)柔腸寸斷的嗓音送入觀眾(聽眾)心田。歌詞與音樂之間的矛盾對比蘊含著巨大的倫理批判力量,歌詞內(nèi)容表明了蝴蝶的善良、忠于愛情和對愛人的無比信任,而沉郁悲愴的音樂卻分明在強調(diào)殘酷現(xiàn)實之不可逆轉(zhuǎn),并預(yù)示著蝴蝶終將為愛情獻出生命的悲劇結(jié)局。音樂與文學(xué)的兩相對照,映襯出蝴蝶高潔的人格形象,也間接對平克爾頓的所作所為予以道德譴責。歌劇的敘事內(nèi)涵也因著這曲詠嘆調(diào)的獨特的對比式抒情而更顯豐富、立體。
歌劇詠嘆調(diào)的抒情作用在現(xiàn)代音樂劇的唱段當中得到了更加通俗化的繼承與發(fā)揚。興起于19世紀的音樂劇(musical theatre)從藝術(shù)類型學(xué)來看與傳統(tǒng)歐洲歌劇有很大差異。誠如上述,歌劇一般在音樂范疇中被提及,主要通過歌唱來展開敘事、呈現(xiàn)戲劇性。而流行于紐約百老匯和倫敦西區(qū)的音樂劇則是從歌舞雜耍表演和滑稽歌舞雜劇中發(fā)展而來,同時接受了一部分輕歌劇的影響,最終定型為一種匯集了音樂、對白、表演與舞蹈的綜合性劇場藝術(shù),坊間常常稱之為秀(show)。簡言之,音樂劇往往因其演出形式的綜合性而被劃歸戲劇領(lǐng)域。與歌劇相比,音樂劇采用對白來過渡敘事情節(jié),其唱段則采用節(jié)拍相對穩(wěn)定、樂句相對勻稱、歌詞押韻的抒情歌曲。這就好比取消了歌劇的宣敘調(diào),而把詠嘆調(diào)予以保留和轉(zhuǎn)型——轉(zhuǎn)型主要是從古典音樂形式轉(zhuǎn)向更加朗朗上口的流行音樂形式。通過這些手段,音樂劇極大地強化了在敘事結(jié)構(gòu)中內(nèi)嵌抒情這一藝術(shù)表現(xiàn)形式,并把抒情的比重予以大幅增加。一部音樂劇中最具抒情風格的歌曲,往往也是劇中最能體現(xiàn)主角的人格形象、反映創(chuàng)作者的倫理評價的段落。如《歌劇魅影》中的《夜之樂章》、《貓》中的《回憶》、《艾薇塔》中的《阿根廷別為我哭泣》、《悲慘世界》中的《帶他回家》等,莫不如此。
藝術(shù)史經(jīng)過兩千多年的發(fā)展,終又在音樂劇身上重現(xiàn)了古希臘悲劇那種對白敘事與歌唱抒情相輪換的基本結(jié)構(gòu),所不同的是,音樂劇在整體保留了較強敘事性和戲劇性的同時,極大地增強了歌曲唱段的藝術(shù)自主性,使其能夠充分發(fā)揮多元的抒情風格、展示豐富的倫理內(nèi)涵,從而獲得觀眾對敘事結(jié)構(gòu)中的抒情段落的空前的審美專注。
五、小結(jié)
以上內(nèi)容嘗試對經(jīng)典敘事藝術(shù)中的抒情段落作出倫理批評,并著重展示了一些高度戲劇化的敘事藝術(shù)在抒情方式和倫理寄寓方式上的某種歷史性聯(lián)系和呼應(yīng),論證了抒情段落往往是敘事藝術(shù)的“倫理之眼”這一美學(xué)判斷。誠然,本文所涉及的內(nèi)容遠遠不能涵括歷史上各種敘事藝術(shù)及其抒情倫理表現(xiàn)的復(fù)雜面貌,尤其是本文對整體風格趨于抒情化的那一派敘事藝術(shù)的倫理表現(xiàn)狀況未予詳解,這也更加說明,敘事藝術(shù)的抒情倫理批評尚有極大的可挖掘空間。
在方法論層面,本文所倡導(dǎo)的敘事藝術(shù)的抒情倫理批評主要采取形式語義學(xué)的批評方法。這一批評方法的思想資源來自以盧卡奇為代表的中歐人文主義批評傳統(tǒng)。(9)“中歐人文主義”的提法出自喬治·斯坦納:《語言與沉默:論語言、文學(xué)與非人道》,李小均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尤其是《喬治·盧卡奇與他的魔鬼契約》《美學(xué)宣言》《走出中歐》等篇。盧卡奇曾在他的一篇談悲劇的論文中設(shè)專章討論“詩性倫理學(xué)”,并指出:“形式是生活的最高審判者。賦形的能力是一種審判性的力量,一種倫理性的東西,而價值判斷就包含在每一個有形式的存在中。”[15]根據(jù)這一批評原則,倫理內(nèi)涵的積淀有賴于特定藝術(shù)形式的定型與成熟,換言之,藝術(shù)形式的變遷為新的倫理價值的探討提供了可能。因此,敘事藝術(shù)的抒情形式每有新的發(fā)展,就為新的生活倫理的表達提供了契機,批評若能跟蹤敘事藝術(shù)的抒情形式發(fā)展并充分解析其美學(xué)特點,便能夠發(fā)掘出凝結(jié)于特定抒情形式中的特殊的倫理內(nèi)涵。這就是敘事藝術(shù)的抒情倫理批評所采用的形式語義學(xué)方法。
當然,對于抒情倫理批評而言,方法論只是其實現(xiàn)手段,價值論評判才是它的根本目的。宋代學(xué)者鄭樵曾批評漢儒以義論詩之失,指出“詩在于聲,不在于義”[16],肯定了音樂亦即抒情審美功能在詩歌藝術(shù)中的首要地位。然而鄭樵的詩歌美學(xué)主張需加上一段音樂美學(xué)的補充才能算是意義完整,這就是《禮記·樂記》中著名的對音樂藝術(shù)的抒情倫理論斷:“樂者,德之華也。……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外發(fā),唯樂不可以為偽。”[17]這段話說得再明確不過:音樂藝術(shù)是人心內(nèi)在德性的外在形式顯現(xiàn),只有感情深摯,才能真正生發(fā)音樂藝術(shù)之華美,所以音樂的創(chuàng)作與表演須正心誠意,不可以為偽。換言之,抒情之所以為抒情,在于藝術(shù)家情深意切,有真實的生活體驗,能誠懇而不加矯飾地進行藝術(shù)表現(xiàn),否則,抒情就淪為了“煽情”“矯情”“濫情”——后者正是抒情倫理批評應(yīng)在價值論層面予以重點批判的內(nèi)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