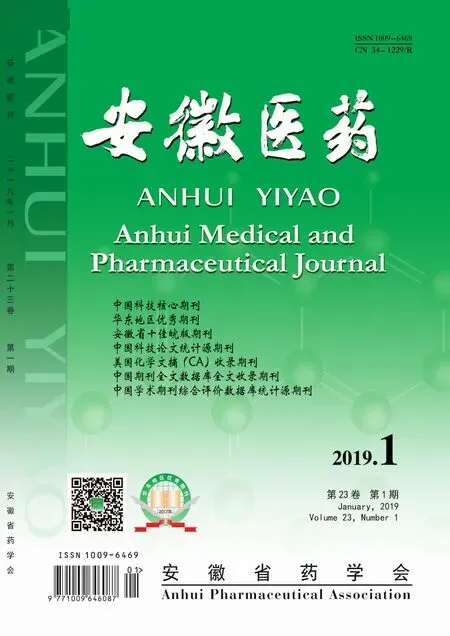系統性紅斑狼瘡并發抗磷脂綜合征臨床研究進展
張靜,林彤彤,蔡輝
抗磷脂綜合征(the antiphospholipid syndrome,APS)是以持續存在抗磷脂抗體(aPL)為特征,以動靜脈血栓形成和妊娠并發癥為主要特征的一種自身免疫性疾病。aPL包括狼瘡抗凝物(LA)、抗心磷脂抗體(aCL)或抗β2-GP1。APS可分為原發性APS和繼發性APS,后者多常見于系統紅斑狼瘡(SLE),也可繼發于其他自身免疫病、感染、吸煙和惡性腫瘤。災難性抗磷脂綜合征(catastrophic antiphospholipid syndrome,CAPS)是一種快速進展的閉塞性事件,發生于數天至數周。其他假定APS亞群包括微血管和血清陰性APS[1]。
近年來關于APS臨床和基礎方面的認知已顯著提高。單一血管受累或多血管閉塞可引起APS多種臨床癥狀。任何血管閉塞事件的組合均可發生于同一人,它們之間的時間間隔存在很大的差異,可從數周到數月甚至數年不等。本篇綜述重點概述了與SLE相關的APS最常見的臨床表現、分類標準及危險分層等研究進展。
1 臨床表現
1.1發病率及特點下肢靜脈血栓形成是本病最為嚴重的臨床表現。此外靜脈血栓可能影響其他部位,如表皮,盆腔,腎,肺,肝,門靜脈,下腔靜脈,鎖骨下動脈和眼靜脈,以及腦靜脈竇[2]。
相反的動脈血栓形成最常見的表現為腦血管意外,通常以中風或短暫性腦缺血發作形式出現,其次是心肌梗死。其他包括外周下肢動脈閉塞,手臂、鎖骨下動脈和頸、腎栓塞、主動脈弓綜合征、腹腔動脈及多種皮膚病變(pseudovasculitic病變、壞疽、皮膚壞死)[3]。
APS的另一特征為產科并發癥。最常見的胎兒表現包括早期、晚期胎兒丟失和早產兒[4]。妊娠合并APS也可見先兆子癇、子癇、HELLP綜合征、胎盤早剝[5-6]。
此外,還有些臨床表現較少出現在APS病人中,這些不常見的表現的流行及特點的大量數據主要來源于“歐洲-磷脂”項目。表1 APS主要臨床表現的數據統計來源于APS病人從疾病開始至納入研究的10年跟蹤隨訪。

表1 “歐洲-磷脂”組1 000例APS病人10年隨訪中主要的臨床表現/例(%)
1.2SLE相關的APS病人臨床表現休斯首次于1983年描述了一組SLE病人,其以LA陽性及復發性血栓形成為臨床特點[7]。隨著新世紀的開始,人們對該病的流行病學以及SLE的存在與否是否會改變APS臨床和血清學的表達產生極大的興趣。“歐洲-磷脂”組指出原發性APS約占53.1%,SLE相關的APS占36.2%,而5%為狼瘡樣綜合征相關的APS[3]。
約40%的SLE病人伴有APL陽性,但最終會出現血栓事件率低于40%[8-10]。20年隨訪中發現SLE合并aPL陽性的病人約50%~70%發展為APS[11]。僅極少數原發性APS發展為系統性紅斑狼瘡[12-13]。“歐洲-磷脂”組10年隨訪中發現,僅8名被診斷為原發性APS的病人出現抗dsDNA陽性,被重新分類為狼瘡樣綜合征,3名病人被重新分類為SLE-APS[14]。
SLE多見于女性病人,男女比例約9∶1,常好發于育齡期,約15~50歲之間,從而反映了激素在發病機制中的影響[15]。在“歐洲-磷脂”組中,女性APS病人中占主導地位(男女比例為1∶5)而SLE相關的APS(1∶7)女性所占比例比原發性APS(1∶3.5)大。此外在臨床表現方面,女性病人更容易出現關節炎、網狀青斑,而男性更容易出現心肌梗死、癲癇和下肢動脈血栓形成。兒童和老年發病也存在差異性(兒童發病更多的表現為舞蹈病和頸靜脈血栓,而老年發病則更多的傾向于男性病人,且常出現中風和心絞痛,但較少出現網狀青斑)[3]。因此激素或者是其他與年齡相關的因素可能與這些差異相關。
在臨床表現中,除了上述所提到的經典APS臨床表現外,SLE相關的APS病人也會出現其他臨床表現。“歐洲-磷脂”組中,SLE相關的APS在10年隨訪中發現,與原發性APS相比,更易出現關節痛、關節炎、白細胞減少、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貧血、網狀青斑、癲癇、腎小球血栓形成、心肌梗死。相反,原發APS病人更易出現血栓性淺靜脈炎,早產兒和胎兒宮內生長受限(表2)。對于自身抗體方面,與原發性APS相比,SLE相關的APS更易出現LA,抗核抗體(ANA)、抗dsDNA抗體、抗RO/SSA、抗La/SSB、抗RNP抗體、抗Sm抗體。
1.3死亡率Ruiz-Irastorza等[10]發現累積生存期15年的SLE病人出現APS比未出現APS概率低 (65%和90%,P=0.03)。回顧性分析顯示8年生存期的SLE病人約98%未合并APS。SLE相關的APS與高死亡率密切相關(P=0.006)。回歸分析數據顯示,疾病活動,動脈血栓形成,血小板減少癥、心臟瓣膜病、毛細血管炎、手指壞死和腎炎是死亡的獨立危險因素。
“歐洲-磷脂”組中,約6.8%的SLE-APS病人和7.1%的原發性APS病人死亡。“歐洲-磷脂”組與同樣為1 000名病人的“歐洲-狼瘡”組進行對比時,發現“歐洲-磷脂”組在10年觀察期內死亡率為9.3%,高于“歐洲-狼瘡”組(6.8%)。主要的死亡原因為嚴重血栓形成(卒中,心肌梗死、肺栓塞或災難性APS)。“歐洲-狼瘡”組中,所有死亡的病人均與SLE-APS的血栓相關,其與“歐洲-磷脂”組有類似的發病率。

表2 “歐洲-磷脂”組10年隨訪中SLE相關的APS和原發性APS主要血栓和產科表現/例(%)
2 分類標準
1999年專家研討會在日本札幌舉行,提出了初步分類標準[16]。2006年對此標準進行了修訂[8],包括增加了抗β2-GP1的檢測,延長實驗室血清檢查時間間隔,更準確的定義臨床表現和實驗室滴度閾值[17]。雖然沒有增加新的臨床標準,某些特定的特征達成共識,如APS相關的特征,包括心臟瓣膜受累、網狀青斑、血小板減少癥、APS腎病,非血栓性中樞神經系統表現(即認知功能障礙)。修訂后APS分類標準為強調危險分層的APS研究提供了更加統一的標準。
雖然已有SLE和APS的分類標準,依據臨床表現去區分SLE和原發性APS有一定難度,因為原發性APS可表現為蛋白尿,胸膜炎,癲癇、精神病、溶血性貧血和血小板減少,而這些臨床表現亦為美國風濕病學會(the American College of Rheumatology,ACR)SLE分類標準的一部分[18]。1993年Piette等人試圖利用原發性APS排除標準區別其他免疫疾病相關的APS和原發性APS。排除標準包括顴骨或盤狀皮疹、口腔或咽部潰瘍、關節炎,胸膜炎、心包炎、尿蛋白大于0.5 g/d,淋巴細胞減少小于1 000 mL,抗DNA、抗ENA抗體,ANA大于1∶320,藥物誘導aPL。這些排除標準并未被廣泛使用,而對原發性APS和SLE-APS的區別,大多是靠臨床醫師的專業知識鑒別。
3 危險分層
aPL可誘導血栓前狀態通過激活內皮細胞中的血栓和炎癥表型降低血栓形成閾值[19]。而最終的臨床表現是由其他幾種變量調控的,如制動、妊娠、內皮功能失調,這些被認為是APS病人中血栓事件必要的“二次打擊”。一些回顧性代表性和前瞻性隊列研究表明半數以上的APS病人的血管事件與其他可逆的血栓形成的危險因素有關[20]。
臨床表現和血栓形成風險由aPL外形、滴度、持久性和其他共存的血栓形成危險因素與潛在自身免疫性疾病如系統性紅斑狼瘡調控[21]。
合并aPL陽性與血栓風險增加相關[22-24],尤其是三者均為陽性時(LA,aCL 和抗β2-GP1)[9,25]。LA陽性已被證明與血栓癥關系最為密切[26],而孤立的抗β2-GP1陽性與血管事件弱相關[11,26]。在SLE病人中,孤立的持續中高滴度ACL陽性與血栓事件風險相關[9,27]。
對于風險的定義已達成國際共識。高風險的定義如下[28]:LA陽性可以作為APL相關臨床表現的最佳預測指標;相比于低滴度APL的IgM型,高滴度和ACL和抗β2-GP1的IgG亞型與aPL相關事件更特異;相比于兩種或單個標記物陽性,三聯陽性與臨床事件關系更為密切;持續存在是aPL特征之一,而短暫性的aPL陽性,也可存在于感染及其他非APS事件中。低風險的定義如下:孤立的,間歇性的ACL陽性;低或中滴度的抗β2-GP1。
SLE病人合并aPL陽性的血栓風險評估應考慮任何可能的附加風險因素,如老年人,傳統的心血管危險因素(如高血壓,糖尿病,高血脂、肥胖、早期更年期),后天性血栓形成(如吸煙、口服避孕藥,妊娠,制動,外科手術)和遺傳高凝狀態(S蛋白、C蛋白C缺失,因子V萊頓突變,凝血酶原20210基因突變)[29]。SLE本身也是血栓形成的危險因素之一。事實上,傳統的Framingham風險評分低估了SLE病人的心血管風險,特別是冠狀動脈疾病[30]。
因此SLE合并aPL陽性不僅存在血栓事件風險,同時也存在器官損害和和不良預后的風險[10]。
而近期出現的“風險評分”可作為協助醫生量化血栓形成風險的工具[31-32]。
4 結語
SLE是以不同的臨床表現和大量自身抗體為特征的一種復雜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在致病性自身抗體中aPL是至關重要的,因為該抗體常在SLE病人中發現(至少20%~30%),SLE-APS病人預后一般較差,可出現病情危重甚至危及生命。對于該病的治療長期抗凝是降低血栓事件的唯一治療手段,部分病人需要終生抗凝治療[33]。口服維生素K拮抗劑首選一線藥物,近年出現的新型抗凝藥物可逐漸被臨床運用。根據第14屆抗磷脂抗體國際研討會推薦的指南[34],口服小劑量阿司匹林可作為抗磷脂抗體陽性病人的一級預防用藥。SLE合并APS/aPL陽性病人的管理謹慎平衡個人風險因素之間的關系。初級預防和二級預防是必要的,在高血栓形成的情況下(手術、長期制動及產褥期),應使用低分子肝素預防血栓形成[21,35]。對于活動期SLE治療,建議最小化風險因素以及健康的生活方式。隨著對SLE-APS認識的不斷提高,亟須進行多中心、前瞻性、大規模臨床隊列研究,以探討其臨床特點及其發病機制,從而提高診治水平。